多巴胺王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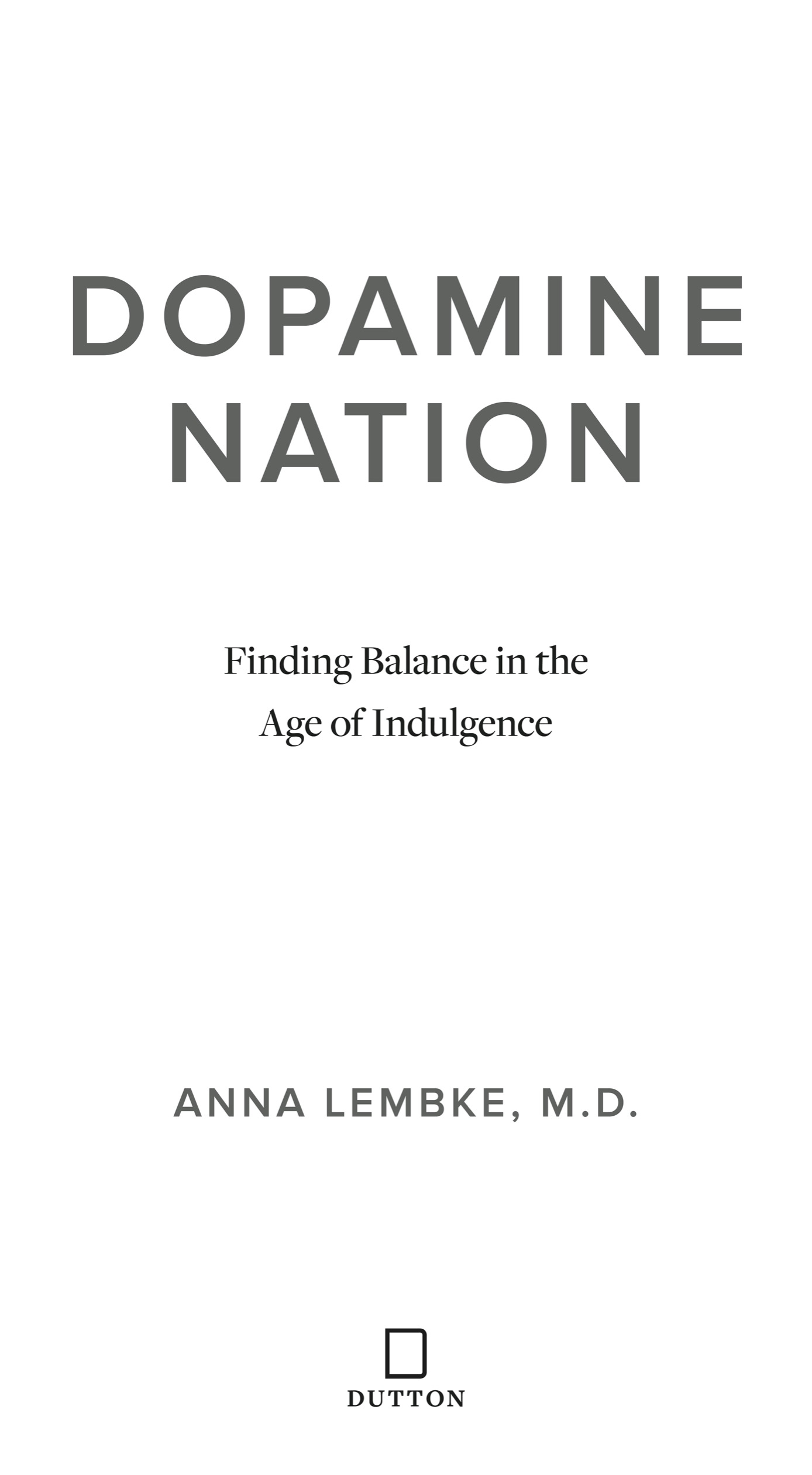

企鹅兰登书屋有限责任公司的一个印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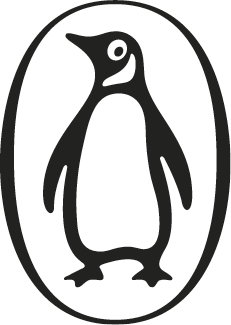
版权 © 2021年 安娜-莱姆克的作品
企鹅支持版权。版权助长创造力,鼓励不同的声音,促进言论自由,并创造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感谢你购买本书的授权版本,感谢你遵守版权法,未经许可,不以任何形式复制、扫描或分发本书的任何部分。你在支持作家,让企鹅公司继续为每个读者出版书籍。
DUTTON和Dcolophon是Penguin Random House LLC的注册商标。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出版数据
名字。Lembke, Anna, 1967- 作者。
标题。多巴胺之国 : 在放纵的时代寻找平衡 / 安娜-伦布克,医学博士。
描述。纽约 : Dutton, [2021] | 包括参考书目和索引。
识别器。LCCN 2020041077 (印刷品) | LCCN 2020041078 (电子书) | ISBN 9781524746728 (精装) | ISBN 9781524746735 (电子书)
课题。LCSH: 快感。| 疼痛。| 强迫性行为.| 互联网-社会方面.| 物质滥用.
分类。LCC BF515 .L46 2020(印刷品)| LCC BF515(电子书)| DDC 152.4/2-dc23
LC记录可在https://lccn.loc.gov/2020041077
LC电子书记录可在https://lccn.loc.gov/2020041078
书籍设计:Lorie Pagnozzi,改编为电子书:Estelle Malmed
虽然作者在出版时已尽力提供准确的电话号码、互联网地址和其他联系信息,但出版商和作者都不对错误或出版后发生的变化承担任何责任。此外,出版商对作者或第三方网站或其内容没有任何控制,也不承担任何责任。
出版商和作者都不从事向个人读者提供专业建议或服务。本书中包含的观点、程序和建议并不打算取代对医生的咨询。所有关于你的健康问题都需要医疗监督。作者和出版商都不对本书中的任何信息或建议所引起的任何损失或损害承担责任或义务。
pid_prh_5.7.1_c0_r0
为了玛丽、詹姆斯、伊丽莎白、彼得和小卢卡斯
目 录
简介
问题所在
感觉良好,感觉良好,世界上所有的钱都花在感觉良好上。
-LEVON HELM
这本书是关于快乐的。它也是关于痛苦的。最重要的是,它是关于快乐和痛苦之间的关系,以及对这种关系的理解如何成为美好生活的关键。
为什么?
因为我们已经把世界从一个稀缺的地方转变为一个压倒性的丰富的地方。毒品、食物、新闻、赌博、购物、游戏、发短信、发短讯、上Facebook、上Instagram、上YouTub、上推特……今天高回报刺激的数量、种类和效力的增加是惊人的。智能手机是现代的皮下注射针,为有线的一代人提供24/7的数字多巴胺。如果你还没有遇到你选择的药物,它很快就会来到你附近的网站。
科学家们依靠多巴胺作为一种通用货币来衡量任何经验的成瘾潜力。大脑奖励途径中的多巴胺越多,体验就越容易上瘾。
除了多巴胺的发现之外,上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神经科学发现之一是大脑在同一地方处理快乐和痛苦。此外,快乐和痛苦的作用就像天平的两端。
我们都经历过那种渴望吃第二块巧克力的时刻,或者希望一本好书、电影或电子游戏永远持续下去。那一刻的渴望是大脑的快乐天平向痛苦一方倾斜。
本书旨在解读奖励的神经科学,并以此使我们能够在快乐和痛苦之间找到一个更好、更健康的平衡。但仅有神经科学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人类的生活经验。有谁能比那些最容易受到强迫性过度消费影响的人更好地教导我们如何克服强迫性过度消费呢:成瘾者。
这本书是基于我的病人落入毒瘾并重新找到出路的真实故事。他们允许我讲述他们的故事,以便你可以像我一样从他们的智慧中受益。你可能会发现其中一些故事令人震惊,但对我来说,它们只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做到的事情的极端版本。正如哲学家和神学家肯特-邓宁顿(Kent Dunnington)写道:“有严重毒瘾的人是那些我们忽视的当代先知之一,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我们的真实身份。”
无论是糖还是购物,窥视还是吸食,社交媒体上的帖子还是*《* *华盛顿邮报》*,我们都在从事一些行为,我们希望我们没有,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后悔。本书为如何在一个消费已成为我们生活中无所不包的动机的世界中管理强迫性过度消费提供了实际解决方案。
从本质上讲,找到平衡的秘诀是将欲望的科学与恢复的智慧相结合。
第一部分
追求的快乐
第一章
我们的自慰机
我去候诊室迎接雅各布。第一印象?很亲切。他六十出头,中等身材,面容柔和但很英俊……老得很好。他穿着标准的硅谷制服:卡其裤和一件休闲的纽扣衬衫。他看起来不显眼。不像是有秘密的人。
当雅各布跟着我穿过短短的迷宫式走廊时,我能感觉到他的焦虑像波浪一样从我背上滚过。我记得我以前走在病人回办公室的路上时也会感到焦虑。我是不是走得太快了?我的臀部摆动了吗?我的屁股看起来好笑吗?
现在看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承认我是一个经历过战火洗礼的人,更加坚毅,可能更加冷漠。当我知道的少,感受的多时,我是一个更好的医生吗?
我们到了我的办公室,我在他身后关上了门。我轻轻地给他提供了两张相同的、等高的、相距两英尺的、有绿色坐垫的、有治疗许可的椅子中的一张。他坐了下来。他的眼睛打量着整个房间。
我的办公室是十乘十四英尺,有两扇窗户,一张装有电脑的桌子,一个摆满书的餐具柜,以及椅子之间的一张矮桌。办公桌、餐具柜和矮桌都是用相匹配的红棕色木材制成的。这张桌子是我以前的系主任递过来的。它的内侧从中间裂开,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是对我所做工作的一个恰当的比喻。
桌子上面有十堆独立的纸张,完美地排列着,像一个手风琴。我被告知这给人一种有组织的效率的感觉。
墙上的装饰品是一个大杂烩。必要的文凭,大多没有装裱。太懒了。我在邻居家的垃圾中发现了一幅猫的画,我把它拿去做画框,但为了这只猫而保留。一幅五颜六色的挂毯,上面画着孩子们在佛塔里和周围玩耍,这是我20多岁时在中国教英语时的遗物。挂毯上有咖啡渍,但只有在你知道自己在找什么的情况下才能看到,就像Rorschach。
展示的是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大部分是病人和学生的礼物。有书籍、诗歌、散文、艺术品、明信片、节日卡、信件、漫画。
一位有天赋的艺术家和音乐家的病人给了我一张他拍摄的金门大桥的照片,上面有他手绘的音符。他拍这张照片的时候已经没有自杀倾向了,但这是一张哀伤的照片,全是灰色和黑色。另一个病人,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因为只有她自己看到的皱纹而感到尴尬,无论用多少肉毒杆菌都无法抹去,她给了我一个泥水壶,大到可以容纳十个人。
在我的电脑左边,我保留了一张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梅伦科利亚1》*的小版画。 在这幅画中,梅伦科利亚化身为一个女人,弯腰坐在长椅上,周围是被忽视的工业和时间的工具:卡尺、天平、沙漏、锤子。她的饥饿的狗,肋骨从它凹陷的框架中突出来,耐心地等待着她唤醒自己,但却徒劳无功。
在我电脑的右边,一个五英寸的粘土天使,用铁丝锻打的翅膀向天空伸展着她的手臂。她的脚下刻着勇气这个词。她是一位正在清理办公室的同事送给我的礼物。一个剩余的天使。我要拿走它。
我很感激这个属于我自己的房间。在这里,我被悬挂在时间之外,存在于一个充满秘密和梦想的世界中。但这个空间也带有悲伤和渴望的色彩。当我的病人离开我的照顾时,职业的界限禁止我与他们联系。
尽管我们的关系在我的办公室里是真实的,但在这个空间之外,它们是不可能存在的。如果我在杂货店看到我的病人,我甚至会犹豫是否要打招呼,以免我宣布自己是一个有自己需求的人。什么,我吃饭?
多年前,当我在接受精神病学住院医师培训时,我第一次在办公室外看到我的心理治疗主管。他从一家商店出来,穿着风衣,戴着印第安纳-琼斯式的联邦帽。他看起来就像刚从J.Peterman目录的封面上走出来。这种经历让人感到震惊。
我与他分享了我生活中的许多私密细节,他像对待病人一样给我提供咨询。我没有想到他是一个戴帽子的人。对我来说,这表明他对个人外表的关注,与我对他的理想化。但最重要的是,这让我意识到我的病人在办公室外看到我可能会感到很不安。
我转向雅各布并开始。“我能帮你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演化出的其他开端包括。“告诉我你为什么在这里?““今天是什么让你进来的?“甚至是 “从头开始,无论你在哪里”。
雅各布看了看我。“我希望,“他用浓重的东欧口音说,“你会是个男人。”
我知道那时我们会谈论性。
“为什么?“我问道,佯装无知。
“因为对你这个女人来说,听到我的问题可能会很难受。”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几乎已经听到了所有可以听到的东西。”
“你看,“他跌跌撞撞,羞涩地看着我,“我有性瘾。”
我点了点头,坐到了椅子上。“继续吧……”
每个病人都是一个未打开的包裹,一本未读的小说,一片未开发的土地。一个病人曾经向我描述过攀岩的感觉。当他站在墙上时,什么都不存在,只有无限的岩壁与每个手指和脚趾下一步该放在哪里的有限决定并列。练习心理治疗与攀岩没有什么不同。我让自己沉浸在故事中,讲述和复述,其余的都消失了。
我听过许多关于人类苦难的故事,但雅各布的故事让我震惊。最让我不安的是,它暗示了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以及我们留给孩子的世界。
雅各布直接从童年的记忆开始说起。没有前言。弗洛伊德会感到自豪。
“我在两三岁的时候第一次手淫,“他说。这段记忆对他来说历历在目。我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到这一点。
“我在月球上,“他继续说,“但它不是真正的月球。那里有一个像神一样的人……而且我有性经验,我不认识……”
我认为月亮是指像深渊一样的东西,无处不在,同时又无处不在。但是上帝呢?我们不是都在渴望超越自己的东西吗?
作为一个年轻的小学生,雅各布是一个梦想家:纽扣不整齐,手上和袖子上有粉笔,上课时第一个看窗外,一天中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在他八岁的时候,他就经常手淫。有时独自一人,有时和他最好的朋友一起。他们还没有学会羞耻。
但在他第一次领圣餐后,他被唤醒了手淫是 “弥天大罪 “的想法。从那时起,他只单独手淫,而且每周五都去拜访他家当地教堂的天主教神父忏悔。
“我手淫,“他透过忏悔室的格子开口低声说。
“多少次?“牧师问。
“每一天。”
暂停一下。“不要再这样做了。”
雅各布停止说话,看着我。我们分享了一个理解的小微笑。如果这样直截了当的告诫能解决问题,我就会失去工作。
男孩雅各布决心服从,做个 “好人”,所以他握紧拳头,不碰自己的地方。但他的决心只持续了两三天。
“他说,“那是我双重生活的开始。
双重生活这个词对我来说就像ST段抬高对心脏病医生来说一样熟悉,第四阶段对肿瘤医生来说是,血红蛋白A1C对内分泌医生来说是。它指的是成瘾者秘密参与毒品、酒精或其他强迫性行为,不为人所知,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不为自己所知。
在整个十几岁的时候,雅各布从学校回来,来到阁楼,对着他从教科书上抄下来的希腊女神阿佛洛狄忒的画像手淫,并把它藏在木地板之间。他后来把他的这段生活看成是一段纯真的时光。
十八岁时,他搬到城里和他姐姐一起住,在那里的大学学习物理和工程。他的姐姐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长时间地独自生活。他很孤独。
“所以我决定做一台机器……”
“一台机器?“我问道,坐得更直了一点。
“一个手淫机器。”
我犹豫了一下。“我明白了。它是如何工作的?”
“我把一根金属棒连接到一个唱片机上。另一端我连接到一个开放的金属线圈,我用软布将其包裹起来。“他画了一张图给我看。
“我把布和线圈放在我的阴茎上,“他说,把阴茎的发音当作两个词:笔像书写工具,尼斯像尼斯湖水怪。
我有一种想笑的冲动,但经过片刻的思考,我意识到这种冲动是对其他事情的掩饰:我很害怕。害怕在邀请他向我展示自己之后,我将无法帮助他。
“他说:“当唱片机一圈又一圈地移动时,线圈就会上升和下降。我通过调整唱片机的速度来调整线圈的速度。我有三种不同的速度。通过这种方式,我把自己带到了边缘……很多次,都没有翻过去。我还了解到,同时抽一支烟能把我从边缘拉回来,所以我也用这一招”。
通过这种微观调整的方法,雅各布能够保持几个小时的预高潮状态。“这个,“他说,点点头,“非常容易上瘾。”
雅各布每天用他的机器自慰几个小时。对他来说,这种快乐是无与伦比的。他发誓说他会停止。他把机器藏在高处的壁橱里,或者把它完全拆开,扔掉零件。但一两天后,他又从柜子里或垃圾桶里把零件拉下来,只是为了重新组装,重新开始。
-
也许你对雅各布的自慰机感到厌恶,就像我第一次听说它时一样。也许你认为它是一种极端的变态行为,超出了日常经验,与你和你的生活几乎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你和我,我们就会错过一个机会,去欣赏我们现在生活方式的一些关键因素。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在与我们自己的手淫机器打交道。
大约40岁时,我对浪漫小说产生了不健康的依恋。暮光之城,一个关于青少年吸血鬼的超自然浪漫小说,是我的入门药物。我对阅读它感到很尴尬,更不愿意承认自己被它迷住了。
暮光之城》击中了爱情故事、惊悚片和幻想之间的甜蜜点,是我在中年转角处的完美逃避。我并不孤单。数以百万计的同龄女性都在阅读和追捧《暮光之城》。我沉浸在书中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寻常。我一生都是一个读者。不同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一些我无法根据过去的倾向性或生活环境来解释的事情。
当我读完*《暮光之城》*后,我撕掉了我能拿到的所有吸血鬼浪漫小说,然后转向狼人、仙女、女巫、死灵法师、时间旅行者、占卜师、读心者、喷火者、算命师、宝石工人……你懂的。在某些时候,温顺的爱情故事不再令人满意,所以我寻找越来越多的经典男孩与女孩的幻想的图形和色情的演绎。
我记得我对在附近图书馆的普通小说书架上很容易找到生动的性场景感到震惊。我担心我的孩子能接触到这些书。在中西部长大的我在当地图书馆看到的最种族主义的东西是《上帝,你在吗?这是我,玛格丽特。
事情升级了,在我的技术专家朋友的怂恿下,我买了一个Kindle。不再需要等待从另一个图书馆分馆送来的书,也不再需要把蒸汽书皮藏在医学杂志后面,尤其是当我丈夫和孩子在身边的时候。现在,只要轻扫两下,点击一下,我就能随时随地得到我想要的任何,包括在火车上、飞机上、等待理发的时候。我可以很容易地把凯伦-玛丽-莫宁(Karen Marie Moning)的《黑暗之火》(Darkfever)当作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简而言之,我成了公式化情色类型小说的连锁读者。一旦我读完一本电子书,我就继续读下一本:用阅读代替社交,用阅读代替烹饪,用阅读代替睡眠,用阅读代替对丈夫和孩子的关注。有一次,我很惭愧地承认,我把我的Kindle带去工作,在病人之间阅读。
我一直在寻找越来越便宜的选择,一直到免费。亚马逊就像任何好的毒贩一样,知道免费样品的价值。偶尔我发现一本真正优质的书,但恰好很便宜;但大多数时候,它们真的很糟糕,依靠破旧的情节装置和毫无生气的人物,充满了错别字和语法错误。但我还是读了它们,因为我越来越多地在寻找一种非常具体的体验。我如何到达那里越来越不重要了。
我想沉浸在那种不断上升的性紧张气氛中,最后在男女主人公勾搭在一起时得到解决。我不再关心句法、风格、场景或人物。我只想得到我的满足,而这些按照公式写成的书,就是为了吸引我。
每一章都在悬念中结束,而各章本身也在向高潮发展。我开始匆匆读完这本书的前半部分,直到进入高潮,读完后也懒得再读其他部分。我现在悲哀地知道,如果你打开任何浪漫小说到大约四分之三的时候,你就可以直接进入主题。
在我开始迷恋爱情的一年左右,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周末的凌晨2点起床,阅读*《五十*度灰》。我理智地认为这是现代版的*《傲慢与偏见*》,直到我读到 “屁股塞 “那一页时,我突然意识到在凌晨时分阅读虐恋性玩具并不是我想要度过的时间。
广义的成瘾是指尽管某种物质或行为(赌博、游戏、性)对自己和/或他人造成伤害,但仍然持续和强迫性地消费。
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与那些有过量毒瘾的人的生活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它说明了我们今天都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强迫性过度消费问题,即使我们的生活很好。我有一个和蔼可亲的丈夫,伟大的孩子,有意义的工作,自由、自主和相对富裕–没有创伤、社会混乱、贫穷、失业或其他成瘾的风险因素。然而,我却强迫性地越来越多地退缩到一个幻想的世界里。
资本主义的黑暗面
在23岁时,雅各布遇到了他的妻子并结婚。他们一起搬进了她与父母共享的三室一厅的公寓,他把他的机器留在了身后–他希望永远如此。他和他的妻子注册了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公寓,但被告知需要等待25年。在他们居住的东欧国家,这在20世纪80年代是很典型的。
他们没有让自己与她的父母生活几十年,而是决定在外面赚取额外的钱,以便早日买下自己的房子。他们开始做电脑生意,从台湾进口机器,加入不断增长的地下经济。
他们的生意兴隆,按照当地的标准,他们很快变得富有。他们获得了一栋房子和一块土地。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当雅各布得到一份在德国当科学家的工作时,他们的上升轨迹似乎得到了保证。他们抓住这个机会向西移动,进一步发展他的事业,并为他们的孩子提供西欧可能提供的所有机会。这次搬迁提供了各种机会,但并非都是好事。
“一旦我们搬到德国,我就发现了色情制品、色情网站、现场表演。我居住的这个城市以这些而闻名,我无法抵制。但我还是忍住了。我管理了10年。我作为一个科学家工作,努力工作,但在1995年,一切都变了。”
“什么变化?“我问,已经猜到了答案。
“互联网。我今年四十二岁,过得还不错,但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我的生活开始崩溃了。1999年有一次,我在同一个酒店房间里,我以前可能住过50次。我有一个重要的会议,第二天有重要的谈话。但我整晚都在看A片,而不是准备我的演讲。我在会议上出现,,没有睡觉,没有发言。我做了一个演讲,非常糟糕。我几乎失去了我的工作。“他低头摇了摇头,回忆道。
“在那之后,我开始一个新的仪式,“他说。“每次我进入酒店房间,我都会在浴室镜子、电视、遥控器上贴满便条,上面写着’不要这样做'。我甚至坚持不了一天。”
我感到震惊的是,酒店房间就像后世的斯金纳箱:一张床、一台电视和一个迷你酒吧。什么都不用做,只需按下毒品的杠杆。
他再次低下头,沉默绵延。我给了他时间。
“那是我第一次想到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想世界不会想念我,也许没有我更好。我走到阳台上,往下看。四层楼……那就够了。”
-
对任何药物成瘾的最大风险因素之一是容易获得该药物。当我们更容易得到一种药物时,我们就更有可能去尝试它。在尝试过程中,我们更有可能对它上瘾。
目前,美国阿片类药物的流行是这一事实的一个悲惨和令人信服的例子。1999年至2012年期间,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处方(OxyContin、Vicodin、Duragesic fentanyl)翻了两番,再加上这些阿片类药物广泛分布在美国的每个角落,导致阿片类药物成瘾率和相关死亡人数不断上升。
2019年11月1日,公共卫生学校和项目协会(ASPPH)任命的一个特别工作组发布了一份报告,结论是:",强力(高效力以及长效)处方阿片类药物供应的巨大扩张,导致处方阿片类药物依赖性的规模化增长,以及许多人过渡到非法阿片类药物,包括芬太尼及其类似物,随后推动超剂量的指数增长。“该报告还指出,阿片类药物使用障碍 “是由反复接触阿片类药物造成的”。
同样,减少成瘾物质的供应也会减少成瘾和相关伤害的暴露和风险。上个世纪测试和证明这一假设的一个自然实验是禁酒令,从1920年到1933年,美国在全国范围内对酒精饮料的生产、进口、运输和销售实行宪法禁令。
禁酒令导致消费和沉迷于酒精的美国人数量锐减。在这一时期,由于缺乏治疗酒瘾的新药,公众醉酒和与酒精有关的肝病的比率下降了一半。
当然,也有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创造了一个由犯罪团伙经营的大型黑市。但是,禁酒令对酒精消费和相关发病率的积极影响普遍没有得到充分认识。
禁酒令带来的饮酒减少效应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在随后的30年里,随着酒精再次变得更容易获得,消费量稳步上升。
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人饮酒的比例增加了近50%,而高风险饮酒增加了15%。2002年至2013年期间,,可诊断的酒瘾在老年人(六十五岁以上)中增加了50%,在妇女中增加了84%,这两个人口群体以前对这个问题相对免疫。
可以肯定的是,增加接触机会并不是唯一的成瘾风险。如果我们的亲生父母或祖父母有毒瘾,即使我们在毒瘾家庭之外长大,风险也会增加。精神疾病是一个风险因素,尽管两者之间的关系还不清楚:精神疾病是否导致吸毒,吸毒是否导致或掩盖精神疾病,还是介于两者之间?
创伤、社会动荡和贫困导致成瘾风险,因为毒品成为一种应对手段,并导致表观遗传变化–对遗传碱基对以外的DNA链的遗传变化–影响个人和他们的后代的基因表达。
尽管有这些风险因素,获得成瘾物质的机会增加可能是现代人面临的最重要的风险因素。供应创造了需求,因为我们都陷入了强迫性过度使用的漩涡。
我们的多巴胺经济,或历史学家大卫-考特怀特(David Courtwright)所称的 “limbic capitalism”,正在推动这一变化,在转型技术的帮助下,不仅增加了药物的获取,还增加了药物的数量、种类和效力。
例如,1880年发明的卷烟机,使人们有可能从每分钟卷四支香烟到惊人的20,000支。今天,全世界每年销售6.5万亿支香烟,相当于每天消费大约180亿支香烟,估计造成全世界600万人死亡。
1805年,德国人弗里德里希-塞蒂尔纳(Friedrich Sertürner)在当药剂师学徒时发现了止痛药吗啡–一种比其前体鸦片效力高十倍的阿片类生物碱。1853年,苏格兰医生亚历山大-伍德发明了皮下注射器。这两项发明促成了19世纪末医学杂志上数百份关于根治性(医生发起的)吗啡成瘾病例的报告。
为了寻找一种成瘾性较低的阿片类止痛药来替代吗啡,化学家们想出了一种全新的化合物,他们将其命名为 “海洛因”,意为 “英雄",即德语中 “勇敢 “的意思。海洛因的药效是吗啡的两到五倍,并导致了20世纪初的麻醉狂。
今天,羟考酮、氢可酮和氢吗啡酮等强效医药级阿片类药物以各种可以想象的形式出现:药片、注射、贴片、鼻腔喷雾。2014年,一位中年患者走进我的办公室,吮吸着一根鲜红色的芬太尼棒棒糖。芬太尼是一种合成的阿片类药物,比吗啡的效力高50到100倍。
除了阿片类药物,今天许多其他药物也比过去更有效力。电子香烟–时尚、谨慎、无味、可充电的尼古丁输送系统–在较短的时间内,,导致血液中的尼古丁水平比传统香烟更高。它们也有多种口味,旨在吸引青少年。
今天的大麻比20世纪60年代的大麻效力高五到十倍,可用于饼干、蛋糕、布朗尼蛋糕、小熊软糖、蓝莓、“大麻馅饼”、润喉糖、精油、芳香剂、酊剂、茶……不胜枚举。
世界各地的技术人员都在操纵着食物。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薯片和油炸食品生产线的自动化导致了袋装薯片的诞生。2014年,美国人每人消费了112.1磅马铃薯,其中33.5磅是新鲜马铃薯,其余78.5磅是加工的。我们吃的许多食物中都添加了大量的糖、盐和脂肪,以及数以千计的人工香料,以满足我们现代人的胃口,如法国吐司冰淇淋和泰式番茄椰子浓汤。
随着药物的获取和药效的增加,多药联用–即同时或近距离使用多种药物–已经成为常态。我的病人马克斯发现,画出他使用药物的时间线比向我解释更容易。
正如你在他的插图中所看到的,他在17岁时开始酗酒、抽烟和吸食大麻(“玛丽珍”)。到18岁时,他开始吸食可卡因。十九岁时,他转而使用奥施康定和赞安诺。二十多岁时,他使用了Percocet、芬太尼、氯胺酮、LSD、PCP、DXM和MXE,最终使用了Opana,一种医药级阿片类药物,使他转向海洛因,在那里他一直呆到三十岁时来见我。在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总共经历了十四种不同的毒品。
现在的世界提供了完整的数字毒品,这些毒品以前并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它们现在也存在于数字平台上,其效力和可得性成倍增加。这包括在线色情、赌博和电子游戏,仅举几例。
用药时间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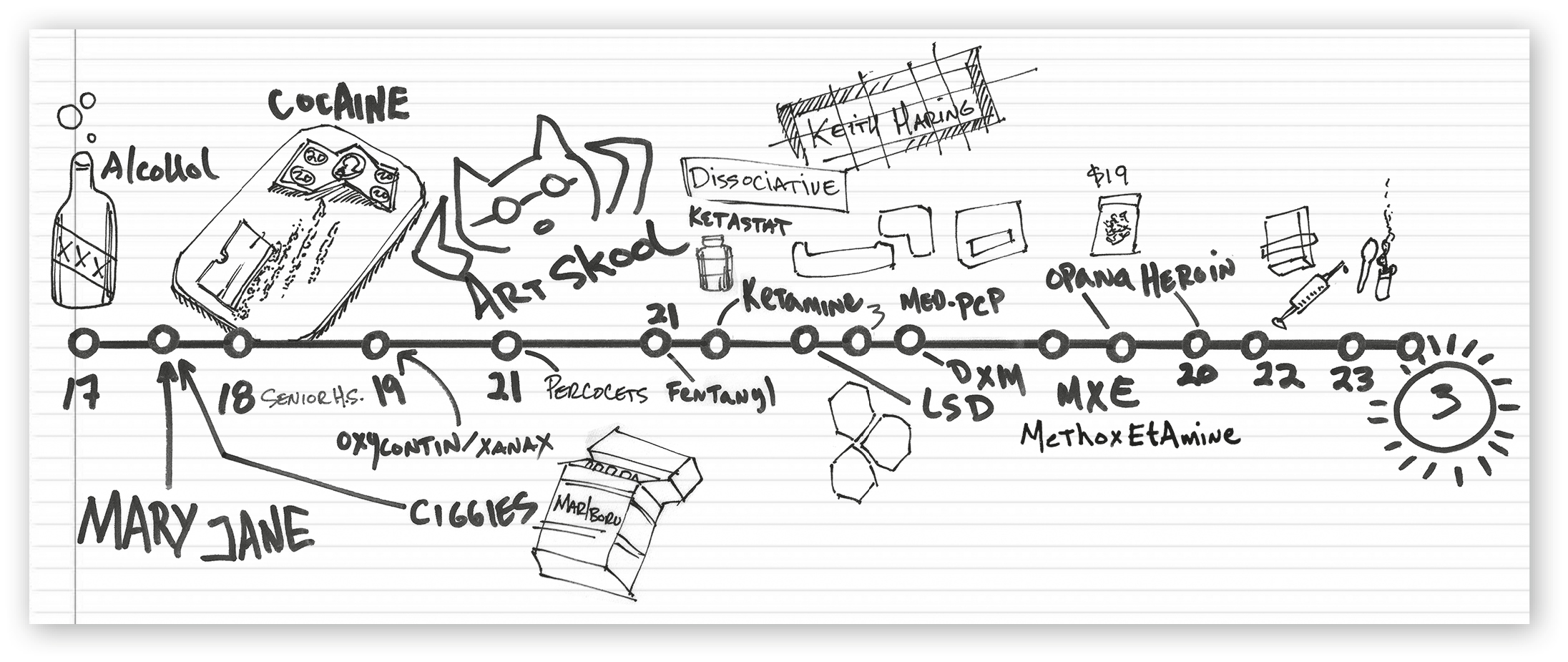
此外,这项技术本身也让人上瘾,它有闪烁的灯光、音乐声、无底的碗,以及随着不断的参与,承诺会有越来越大的回报。
我自己从相对温顺的吸血鬼爱情小说发展到相当于社会认可的女性色情作品,可以追溯到电子阅读器的出现。
消费行为本身已经成为一种毒品。我的病人Chi是一名越南移民,他迷上了在网上搜索和购买产品的循环。对他来说,高潮是从决定买什么开始的,一直到期待送货上门,并在他打开包裹的那一刻达到高潮。
不幸的是,在他撕掉亚马逊的磁带并看到里面的东西时,这种兴奋并没有持续多少时间。他的房间里堆满了廉价的消费品,并欠下了数万美元的债务。即使如此,他还是无法停止。为了保持这种循环,他不得不订购越来越便宜的商品–钥匙链、杯子、塑料太阳镜,并在到达后立即退回。
互联网和社会传染病
雅各布决定那天不在酒店里结束自己的生命。就在第二周,他的妻子被诊断出患有脑癌。他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接下来的三年里他一直在照顾她,直到她去世。
2001年,在49岁时,他与高中时的女友重新联系并结婚。
“在我们结婚前我就告诉她我的问题。但也许我在告诉她的时候,会尽量减少。”
雅各布和他的新妻子一起在西雅图买了一套房子。雅各布通勤到硅谷担任科学家的工作。他在硅谷和远离妻子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是回到色情和强迫性手淫的旧模式。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从来不做色情活动。但当我在硅谷或旅行时,如果她不在我身边,那么我就会做。”
雅各布停顿了一下。接下来的事情对他来说显然是难以启齿的。
“有时候,当我玩电的时候,在我的工作中,我可以,在我的手中感觉到一些东西。我很好奇。我开始想,用电流触摸我的阴茎会是什么感觉。于是我开始在网上研究,我发现有一整个使用电刺激的群体。
“我把电极和电线连接到我的立体声系统。我利用立体声系统的电压尝试交流电流。然后,我不使用简单的电线,而是在盐水中安装由棉花制成的电极。音响的音量越大,电流就越大。在低音量时,我没有感觉。在高音量时,它是痛苦的。在这两者之间,我可以从这种感觉中达到高潮。”
我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我忍不住了。
“但这非常危险,“他继续说。“我意识到,如果停电,这可能会导致电涌,然后我就会受伤。人们这样做已经死了。在网上我了解到我可以买一个医疗包,比如……你们怎么称呼它们,那些治疗疼痛的机器……”
“一个TENS装置?”
“是的,一个TENS装置,六百美元,或者我可以花二十美元自己做。我决定自己做。我买了材料。我做了这台机器。它很有效。它工作得很好。“他停顿了一下。“但后来真正的发现是。我可以给它编程。我可以创建自定义的程序,使音乐与感觉同步。”
“什么类型的常规?”
“手淫,口交。你的名字。然后我发现不仅仅是我的套路。我上网下载其他人的程序,并分享我的程序。有些人编写程序,与色情视频同步,这样你就能感受到你正在看的东西……就像虚拟现实。快感,当然来自于感觉,但也来自于建造机器,,期待着它会做什么,实验着改进它的方法,并与他人分享。”
他微笑着,回忆着,就在他的脸落下之前,期待着接下来的事情。仔细观察我,我可以看出他在衡量我是否能接受。我支撑着自己,点头让他继续说下去。
“情况变得更糟。有一些聊天室,你可以在那里观看人们的自慰,现场直播。观看是免费的,但可以选择购买代币。我为好的表现提供代币。我把自己拍下来,放在网上。只有我的私人部位。没有我的其他部分。一开始很兴奋,让陌生人看我。但我也感到内疚,因为观看会给其他人带来想法,他们可能会上瘾。”
-
2018年,我在一名男子的案件中担任医学专家证人,该男子用卡车冲撞两名青少年,导致两人死亡。他是在毒品的影响下驾驶的。作为该诉讼的一部分,我花时间与文斯-杜托(Vince Dutto)侦探交谈,他是加利福尼亚州普雷塞尔县的首席犯罪调查员,该案的审判就发生在那里。
我对他的工作感到好奇,问他在过去20年里看到的任何模式变化。他告诉我一个悲惨的案例,一个六岁的男孩鸡奸了他四岁的弟弟。
“通常情况下,当我们接到这些电话时,“他说,“这是因为孩子接触的某个成年人对他进行了性虐待,然后孩子在另一个孩子身上重演,比如他的小弟弟。但我们做了彻底的调查,没有证据表明这个哥哥受到了虐待。他的父母离异,经常工作,所以孩子们都是自己抚养自己,但没有发生主动的性虐待。
“在这个案件中,最终出现的情况是,哥哥一直在互联网上看动画片,偶然发现了一些日本动漫动画片,其中有各种性行为。这孩子有自己的iPad,没有人监督他的行为,在看了一堆这些动画片后,他决定在他的弟弟身上试试。现在,这种事情,在二十多年的警察工作中,我以前从未见过。”
互联网促进了强迫性的过度消费,不仅提供了更多接触新旧毒品的机会,而且还暗示了我们可能从未想过的行为。视频不只是 “病毒式传播”。它们实际上是有传染性的,因此出现了 “备忘录”。
人类是社会动物。当我们在网上看到别人以某种方式行事时,这些行为似乎是 “正常的”,因为其他人也在这么做。“推特 “是专家学者和总统们都喜欢的社交媒体信息平台的一个恰当的名字。我们就像成群的鸟。我们中的一个人刚举起翅膀飞行,整个鸟群就已经升到空中。
-
雅各布低头看着自己的手。他无法与我对视。
“然后我在这个聊天室里遇到一位女士。她喜欢支配男人。我把她引入电的东西,然后我给她远程控制电的能力:频率、音量、脉冲的结构。她喜欢把我带到边缘,然后让我不要过去。她这样做了十次,其他的人看着,并发表评论。我们发展了友谊,这位女士和我,她从不愿意露面。但我有一次意外地看到了她,她的相机掉了一下。”
“她多大了?“我问道。
“四十多岁的时候,我想……”
我想问她长什么样子,但感觉到我自己的好奇心在这里起作用,而不是他的治疗需要,所以我没有问。
雅各布说:“我妻子发现这一切,她说她要离开我。我答应停止。我在网上告诉我的女性朋友我不干了。我的女性朋友非常生气。我的妻子非常生气。那时我恨我自己。我停了一阵子。也许一个月。但后来我又开始了。只有我和我的机器,没有聊天室。我对我妻子撒谎,但最终她发现了。她的治疗师告诉她要离开我。于是我妻子离开了我。她搬到了我们在西雅图的房子里,现在我是一个人。”
他摇摇头,说:“它从来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好。现实总是更少。我告诉自己再也不要了,然后我毁掉了机器,把它扔掉。但在第二天凌晨四点,我又从垃圾桶里把它拿出来,再次建造它。”
雅各布用恳求的目光看着我。“我想停下来。我想。我不想作为一个瘾君子死去。”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想象他通过互联网把自己的生殖器连接到一个充满陌生人的房间。我感到恐怖、同情和一种模糊的、令人不安的感觉,那可能是我。
-
与雅各布不同的是,我们都有可能把自己挑逗得欲仙欲死。
世界全球死亡人数的70%归因于可改变的行为风险因素,如吸烟、身体不活动和饮食。,全球领先的死亡风险是高血压(13%)、烟草使用(9%)、高血糖(6%)、缺乏体育活动(6%)和肥胖(5%)。2013年,估计有21亿成年人超重,而1980年有8.57亿。现在,除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外,全世界肥胖的人比体重不足的人多。
全世界的成瘾率都在上升。全球因酒精和非法药物成瘾造成的疾病负担为1.5%,在美国超过5%。这些数据不包括烟草消费。选择的药物因国家而异。美国以非法药物为主,俄罗斯和东欧以酒精成瘾为主。
1990年至2017年期间,全球所有年龄组因吸毒成瘾而死亡的人数都在增加,其中一半以上的死亡发生在50岁以下的人身上。
穷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特别是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最容易受到强迫性过度消费问题的影响。他们很容易获得高回报、高效力、高创新的药物,与此同时,他们缺乏,无法获得有意义的工作、安全的住房、高质量的教育、负担得起的医疗保健,以及法律面前的种族和阶级平等。这创造了一个危险的成瘾风险关系。
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的研究表明,没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中年白人比他们的父母、祖父母和曾祖父母死得更早。这个群体的前三大死因是药物过量、与酒精有关的肝病和自杀。凯斯和迪顿将这种现象恰当地称为 “绝望的死亡”。
我们强迫性的过度消费不仅有可能使我们灭亡,也有可能使我们的星球灭亡。,世界的自然资源正在迅速减少。经济学家估计,到2040年,世界的自然资本(土地、森林、渔业、燃料)在高收入国家将比现在减少21%,在较贫穷国家将减少17%。同时,高收入国家的碳排放将增长7%,世界其他地区将增长44%。
我们正在吞噬自己。
第二章
逃避痛苦
我在2018年遇到了大卫。他在身体上并不显眼:白人,中等身材,棕色头发。他身上有一种不确定性,使他看起来比医疗记录中记载的三十五岁要年轻。我发现自己在想,他不会持久。 他将会回到诊所一两次,然后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了。
但我已经知道我的预言能力是不可靠的。我曾有过这样的病人,我相信我可以帮助他们,但事实证明他们是难缠的,还有一些我认为没有希望的病人,却出人意料地有韧性。因此,现在看到新的病人时,我试着让怀疑的声音安静下来,记住每个人都有康复的机会。
“告诉我什么让你进来,“我说。
大卫的问题始于大学,但更准确地说,是在他走进学生心理健康服务机构的那天。他是纽约州北部的一名20岁的大二学生,在焦虑和学习成绩不佳方面寻求帮助。
他的焦虑在与陌生人或他不熟悉的人交流时被触发。他的脸会发红,他的胸部和背部会发潮,他的思想会变得混乱不堪。他回避必须在别人面前发言的课程。他曾两次从必修的演讲和交流研讨会上退学,最终通过在社区大学学习同等课程来满足要求。
“你在害怕什么?“我问道。
“我害怕失败。我害怕被人知道我不懂。我害怕寻求帮助”。
经过45分钟的预约和不到5分钟的纸笔测试,他被诊断出患有注意力缺陷障碍(ADD)和广泛性焦虑症(GAD)。进行测试的心理学家建议他去看精神科医生,给他开一种抗焦虑的药物,而且,大卫说,“给我的注意力缺陷障碍开一种兴奋剂”。他没有得到心理治疗或其他非药物的行为矫正。
大卫去看精神科医生,医生给他开了Paxil(一种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用于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和Adderall(一种兴奋剂,用于治疗注意力缺陷症)。
“那么,你的情况如何–我是说药物,"。
“起初,Paxil对焦虑有一点帮助。它减轻了一些最严重的出汗情况,但它并不能治愈。我最后把我的专业从计算机工程改为计算机科学,认为那会有帮助。这需要较少的互动。
“但是,由于我不能够说出我不知道,所以我没有通过考试。然后我又没有通过下一次考试。然后,我放弃了,一个学期后,我的平均成绩没有受到影响。最后,我完全转出了工程学院,这真的很悲哀,因为这是我所喜欢和真正想做的。我成了历史专业。班级比较小,只有20个人,我可以不与人交流。我可以把蓝皮书带回家,自己工作。”
“那Adderall呢?“我问道。
“我每天早上上课前都会先吃十毫克。它帮助我获得深度专注。但回过头来看,我认为我只是有不良的学习习惯。Adderall帮助我弥补了这一点,但它也帮助我拖延了时间。如果有考试而我没有学习,我就会昼夜不停地服用阿德拉,从白天到晚上,为考试做准备。后来,我没有它就无法学习。然后我开始需要更多。”
我想知道他要获得更多的药片有多难。“获得更多的东西很困难吗?”
“并非如此,“他说。“我总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补药了。我在几天前就给精神病医生打电话。不是很多天,只是一两天,这样他们就不会怀疑了。实际上,我在十天前就用完了,但如果我在几天前打电话,他们就会马上补上。我还了解到,最好是和P.A.,也就是医生的助手谈。他们更有可能在不问太多问题的情况下加药。有时我会编造借口,比如说邮购药店出了问题。但大多数时候,我没有必要这样做。
“听起来那些药丸并没有真正的帮助。”
大卫停顿了一下。“最后,它归结为安慰。吃药比感受痛苦更容易。”
-
2016年,我为斯坦福大学学生心理健康诊所的教职员工做了一次关于毒品和酒精问题的演讲。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去过校园的那个地方了。我提前到达,当我在前厅等待与我的联系人见面时,我的注意力被墙上的宣传册吸引了。
一共有四本小册子,每本小册子的标题中都有幸福这个词的一些变化。幸福的习惯》、《睡在幸福的路上》、《幸福触手可及》、《*7天让你更幸福》。*每本小册子里面都有实现幸福的处方。“列出50件使你快乐的事情,““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并]在你的日记中列出你喜欢自己的事情,“以及 “产生积极的情绪流”。
也许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优化幸福策略的时机和种类。对时间和频率要有预见性。对于善意的行为。自我实验,以确定在一天内做许多好事还是每天做一件事对你来说最有效”。
这些小册子说明了对个人幸福的追求如何成为现代格言,排挤了对 “美好生活 “的其他定义。即使是对他人的善意行为也被视为个人幸福的一种策略。利他主义不再仅仅是一种善的本身,而是成为我们自己 “幸福 “的载体。
二十世纪中期的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在*《治疗的胜利*》中预见到了这种趋势*。弗洛伊德之后信仰的使用*。“宗教的人生来就是为了被拯救;心理的人生来就是为了被取悦。”
劝告我们追求幸福的信息并不限于心理学领域。现代宗教也提倡自我意识、自我表达和自我实现的神学,认为这是最高的善。
作家和宗教学者罗斯-杜塔特(Ross Douthat)在他的《坏宗教》(Bad Religion)一书中,将我们的新时代 “内在的上帝 “神学描述为 “一种既是世界性的又是安慰性的信仰,承诺提供异国情调的所有乐趣……而没有任何痛苦。…没有任何痛苦…一种神秘的泛神论,在这种信仰中,上帝是一种经验而不是一个人。令人吃惊的是,在 “内在之神 “的文献中,很少有道德方面的劝诫。书中经常呼吁 “同情 “和 “仁慈”,但对面临实际困境的人几乎没有指导。所提供的指导往往是 “如果感觉好,就去做”。”
我的病人凯文,19岁,在2018年被他的父母带去见我。他们的顾虑有以下几点。他不愿意去学校,不能保持工作,也不愿意遵守任何家庭规则。
他的父母和我们其他人一样不完美,但他们在努力帮助他。没有虐待或忽视的证据。问题是他们似乎无法对他施加任何限制。他们担心,如果提出要求,就会 “给他带来压力 “或 “使他受到创伤”。
将儿童视为心理脆弱的人是一个典型的现代概念。在古代,儿童被认为是微型的成年人,从出生起就完全成型。在大多数西方文明中,儿童被认为是天生的邪恶。父母和照顾者的工作是执行极端的纪律,以使他们社会化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使用体罚和恐惧战术来使孩子听话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现在不是了。
今天,我看到的许多父母都害怕做或说一些会给他们的孩子留下情感伤痕的事情,从而使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遭受情感上的痛苦,甚至是精神疾病。
这种观念可以追溯到弗洛伊德,他在精神分析方面的开创性贡献是,早期的童年经历,即使是那些早已被遗忘或不被意识到的经历,也会造成持久的心理伤害。不幸的是,弗洛伊德关于早期儿童创伤可以影响成人心理病理学的见解已经演变成一种信念,即任何和每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经历都为我们提供了心理治疗的准备。
我们为使孩子免受不良心理体验的影响所做的努力不仅体现在家庭中,也体现在学校中。在小学阶段,每个孩子都会得到一些类似于 “每周之星 “的奖项–不是因为任何特定的成就,而是按字母顺序排列。每个孩子都被教导要警惕欺凌者,以免他们成为旁观者,而不是挺身而出者。在大学层面上,教师和学生都在谈论触发器和安全空间。
育儿和教育是以发展心理学和同理心为基础的,这是一种积极的演变。我们应该承认每个人的价值与成就无关,停止学校操场上的身体和情感暴行,以及其他地方,并创造安全的空间来思考、学习和讨论。
但我担心,我们既把童年过度消毒,又把童年过度病理化,把我们的孩子养在相当于软垫牢房的地方,没有办法让他们自己受伤,但也没有办法让他们为世界做好准备。
通过保护我们的孩子远离逆境,我们是否让他们对逆境产生了致命的恐惧?通过用虚假的赞美和缺乏现实世界的后果来增强他们的自尊,我们是否让他们变得更不宽容,更有权利,并且对自己的性格缺陷一无所知?通过屈服于他们的每个欲望,我们是否鼓励了一个新的享乐主义时代?
凯文在我们的一次会议上与我分享了他的人生哲学。我必须承认,我被吓坏了。
“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我想。如果我想呆在我的床上,我就呆在我的床上。如果我想玩视频游戏,我就玩视频游戏。如果我想吸食可卡因,我就给毒贩子发短信,他把毒品送来,然后我就吸食可卡因。如果我想做爱,我就上网找人,和他们见面并做爱。”
“你的工作怎么样了,凯文?“我问道。
“不是很好。“有那么一瞬间,他显得很羞愧。
在过去三十年里,我看到越来越多像大卫和凯文这样的病人,他们似乎拥有生活中的一切优势–支持性的家庭、高质量的教育、经济稳定、健康状况良好–但却出现了令人虚弱的焦虑、抑郁和身体疼痛。他们不仅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潜力,而且早上几乎无法起床。
-
医学的实践也同样因我们对无痛世界的努力而发生了变化。
在20世纪之前,医生认为某种程度的疼痛是健康的。19世纪的主要外科医生不愿意在手术中采用全身麻醉,因为他们认为疼痛能促进免疫和心血管反应,加快愈合。尽管据我所知,没有证据显示疼痛事实上会加速组织修复,但有新的证据表明,在手术期间服用阿片类药物会减慢修复速度。
十七世纪的著名医生托马斯-西登纳姆对疼痛是这样说的。“我认为每一个……努力都是为了完全制服极端危险的疼痛和炎症……。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四肢的适度疼痛和炎症是大自然为最明智的目的所使用的。”
相比之下,今天的医生被期望消除所有的疼痛,以免他们不能胜任同情心强的治疗者的角色。任何形式的疼痛都被认为是危险的,不仅因为它伤害了人,而且还因为它被认为通过留下永远不会愈合的神经系统伤口来点燃大脑未来的疼痛。
围绕疼痛的范式转变已经转化为,大量开出感觉良好的药片。今天,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和超过二十分之一的美国儿童每天都在服用一种精神药物。
,像Paxil、Prozac和Celexa这样的抗抑郁药的使用在世界各国都在上升,其中美国名列榜首。超过十分之一的美国人(每1000人中有110人)服用抗抑郁药,其次是冰岛(106/1000)、澳大利亚(89/1000)、加拿大(86/1000)、丹麦(85/1000)、瑞典(79/1000)和葡萄牙(78/1000)。在25个国家中,韩国排在最后(13/1,000)。
在德国,抗抑郁药的使用在短短四年内增加了46%,同期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增加了20%。虽然没有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的数据,但我们可以通过观察销售趋势来推断抗抑郁药的使用量在增长。在中国,2011年抗抑郁药的销售额达到26.1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19.5%。
2006年至2016年,美国的兴奋剂(Adderall,Ritalin)处方增加了一倍,包括5岁以下的儿童。2011年,三分之二被诊断为注意力缺失症的美国儿童被开了兴奋剂。
苯二氮卓类药物(Xanax、Klonopin、Valium)等镇静药物的处方也会成瘾,正在上升,也许是为了弥补我们服用的那些兴奋剂。1996年至2013年期间,在美国,开出苯二氮卓类药物处方的成年人数量增加了67%,从810万人增加到1350万人。
2012年,阿片类药物的处方量足以让每个美国人拥有一瓶药片,而阿片类药物过量导致的美国人死亡人数超过枪支或车祸。
那么,大卫认为他应该用药片来麻痹自己,这有什么奇怪吗?
-
除了逃避痛苦的极端例子,我们已经失去了容忍甚至是轻微形式的不适的能力。我们不断地寻求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让自己远离当下,接受娱乐。
正如奥尔德斯-赫胥黎在《重新审视美丽新世界》中所说*,*“一个庞大的大众传播业的发展,主要关注的既不是真实的也不是虚假的,而是不真实的,或多或少完全不相关的……没有考虑到人类对分心的几乎”。
沿着类似的思路,20世纪80年代经典作品《把自己逗死》的作者尼尔-波兹曼写道:“美国人不再相互交谈,而是相互娱乐。他们不交流思想,而是交流图像。他们不是用命题来争论,而是用漂亮的外表、名人和广告来争论”。
我的病人苏菲是来自韩国的斯坦福大学本科生,她来寻求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帮助。在我们谈论的许多事情中,她告诉我,她醒着的大部分时间都插在某种设备上。拍照片、看视频、听播客和播放列表。
在与她的会谈中,我建议她试着走到教室,不听任何东西,只是让自己的想法浮现出来。
她既难以置信又害怕地看着我。
“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她张口问道。
“嗯,“我大胆地说,“这是一种熟悉自己的方式。让你的经历展开而不试图控制它或逃避它。所有这些让自己分心的设备可能是导致你抑郁和焦虑的原因。一直躲避自己是很累的。我想知道,以不同的方式体验自己是否可以让你获得新的想法和感受,并帮助你感觉到与自己、与他人和与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
她想了一会儿。“但这太无聊了,“她说。
“是的,那是真的,“我说。“无聊不只是无聊。它也可能是令人恐惧的。它迫使我们面对更大的意义和目的问题。但无聊也是一个发现和发明的机会。它为新思想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空间,没有它,我们就会无休止地对周围的刺激作出反应,而不是让自己置身于我们的生活经验之中。”
第二周,苏菲尝试不插电步行去上课。
“开始时很难,“她说。“但后来我习惯了它,甚至有点喜欢它。我开始注意到这些树。”
缺乏自理能力还是有精神疾病?
回到大卫身上,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在 “全天候服用阿德拉”。2005年大学毕业后,他搬回父母家住。他想过要上法学院,参加了LSAT考试,甚至考得还不错,但当要申请时,他觉得不喜欢了。
“我主要是坐在沙发上,积累了大量的愤怒和怨恨:对自己,对世界。”
“你在为什么生气?”
“我觉得我浪费了我的本科教育。我没有研究我真正想研究的东西。我的女朋友还在学校……做得很好,获得了硕士学位。我却在家里沉湎于无所事事。”
大卫的女友毕业后,在帕洛阿尔托找到了一份工作。他跟着她去了那里,在2008年他们结婚了。大卫在一家技术创业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他与年轻、聪明的工程师交流,他们对自己的时间都很慷慨。
他重新投入到编码工作中,并学习了所有他在大学里想学习的东西,但在满是学生的房间里却不敢追求。他被提升为软件开发人员,每天工作15个小时,在业余时间每周跑30英里。
“但为了实现这一切,“他说,“我正在服用更多的Adderall,不仅仅是在早上,而是在整个白天。我在早上醒来,服用Adderall。回到家,吃晚饭,服用更多Adderall。吃药成了我的新常态。我还喝了大量的咖啡因。然后我到了晚上,我需要睡觉,我就想,*好吧,我现在该怎么做?*于是我又去找心理医生,说服她给我开安眠药。我假装不知道安眠药是什么,但我妈妈已经服用安眠药很长时间了,还有几个叔叔也服用过。我还说服她在演讲前给我开了有限的安眠药,用于治疗焦虑症。从2008年到2018年,我每天服用多达30毫克的阿德拉,每天服用50毫克的安眠药,每天服用3到6毫克的阿替凡。我想,我有焦虑症和多动症,我需要这些来发挥作用。”
大卫将疲劳和注意力不集中归因于精神疾病,而不是睡眠不足和过度刺激,他用这种逻辑来证明继续使用药片的合理性。多年来,我在许多病人身上看到了类似的悖论。他们使用药物,不管是处方药还是其他药物,来弥补基本的自我保健的不足,然后把费用归结为精神疾病,从而有必要使用更多的药物。因此,毒药变成了维生素。
“你在服用你的A类维生素。阿德拉、安眠药和安定剂,“我开玩笑说。
他笑了笑。“我想你可以这么说。”
“你的妻子或其他人知道你发生了什么事吗?”
“不,没有人知道。我的妻子也不知道。有时,当我的安眠药用完时,我会喝酒,或者当我服用过多的阿德拉时,我会生气并对她大吼。但除此之外,我隐藏得很好。”
“那么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已经厌倦了它。厌倦了日日夜夜服用兴奋剂和镇静剂。我开始考虑结束我的生命。我想我可以过得更好,其他人也可以过得更好。但是我的妻子怀孕了,所以我知道我需要做出改变。我告诉她我需要帮助。我让她带我去医院。”
“她有什么反应?”
“她把我带到急诊室,当一切都出来时,她很震惊。”
“是什么让她感到震惊?”
“那些药丸。我所服用的所有药丸。我的大量藏品。还有我藏了多少。”
David被送入精神病住院病房,并被诊断为兴奋剂和镇静剂成瘾。他一直呆在医院里,直到他完成对Adderall、Ambien和Ativan的戒断,并直到他不再有自杀倾向。这花了两个星期。他出院后回到了他怀孕的妻子身边。
-
我们都在逃避痛苦。我们中的一些人吃药。我们中的一些人在沙发上冲浪,同时狂热地观看Netflix。我们中的一些人阅读浪漫小说。我们几乎会做任何事情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然而,所有这些试图使自己与疼痛绝缘的做法似乎只是使我们的疼痛变得更糟。
根据《世界幸福报告》,该报告根据156个国家的公民认为自己的幸福程度进行排名,生活在美国的人报告说,2018年的幸福感不如2008年的时候。其他在财富、社会支持和预期寿命方面有类似衡量标准的国家,其自我报告的幸福指数也有类似的下降,包括比利时、加拿大、丹麦、法国、日本、新西兰和意大利。
研究人员采访了26个国家的近15万人,以确定普遍性焦虑症的发病率,该症被定义为过度和无法控制的担忧,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不利影响。他们发现,较富裕国家的焦虑症发病率高于贫穷国家。作者写道:“这种障碍在高收入国家的流行程度和损害程度明显高于中低收入国家”。
1990年至2017年期间,全世界抑郁症的新病例数量增加了50%。新病例增加最多的是社会人口指数(收入)最高的地区,特别是北美洲。
身体疼痛也在增加。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看到了更多的病人,包括原本健康的年轻人,尽管没有任何可识别的疾病或组织损伤,却出现了全身疼痛。无法解释的身体疼痛综合征的数量和类型也在增加:复杂区域疼痛综合征、纤维肌痛、间质性膀胱炎、肌筋膜疼痛综合征、盆腔疼痛综合征,等等。
当研究人员向全世界30个国家的人提出以下问题时–“在过去的四个星期里,你多久会有身体上的疼痛或痛苦?从未;很少;有时;经常;或非常经常?“他们发现,美国人报告的疼痛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多。
34%的美国人说他们 “经常 “或 “非常经常 “感到疼痛,而生活在中国的人有19%,生活在日本的人有18%,生活在瑞士的人有13%,而生活在南非的人有11%。
问题是:为什么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财富、自由、技术进步和医学发展的时代,我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快乐,更痛苦?
我们都如此悲惨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们如此努力地工作以避免悲惨。
第三章
快乐与痛苦的平衡
在过去的五十到一百年里,神经科学的进步,包括生物化学的进步、新的成像技术和计算生物学的出现,揭示了基本奖励过程。通过更好地了解支配疼痛和快乐的机制,我们可以获得新的见解,了解为什么和如何过多的快乐会导致疼痛。
多巴胺
大脑的主要功能细胞被称为神经元。它们通过电信号和神经递质在突触处相互交流。
神经递质就像棒球。投手是突触前的神经元。捕手是突触后的神经元。投手和捕手之间的空间是突触裂隙。就像在投手和捕手之间投球一样,神经递质在神经元之间架起了桥梁:化学信使调节着大脑中的电信号。有许多重要的神经递质,但让我们把重点放在多巴胺上。
神经递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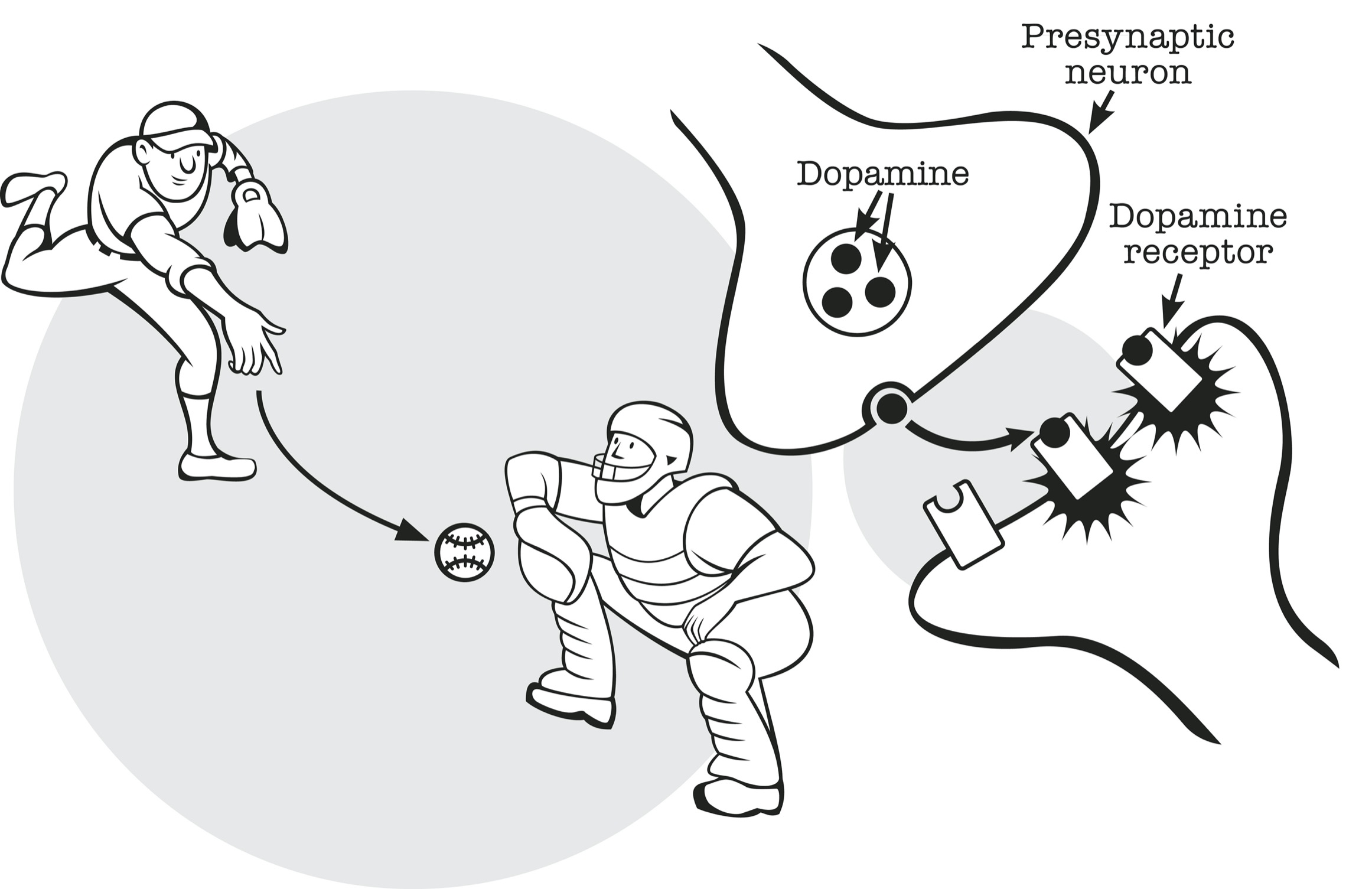
1957年,两位独立工作的科学家首次发现多巴胺是人脑中的一种神经递质。阿维德-卡尔松和他在瑞典隆德的团队,以及位于伦敦郊外的Kathleen Montagu。卡尔松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多巴胺并不是参与奖励处理的唯一神经递质,但大多数神经科学家都认为它是最重要的神经递质之一。多巴胺在获得奖赏的动机中发挥的作用可能比奖赏的快乐本身更大。渴望多于喜欢。无法制造多巴胺的基因工程小鼠不会寻找食物,即使食物放在离它们嘴边几英寸的地方也会饿死。然而,如果食物被直接放进它们的嘴里,它们会咀嚼并吃下食物,而且似乎很享受。
尽管有关于动机和快乐之间差异的争论,多巴胺被用来衡量任何行为或药物的成瘾潜力。一种药物在大脑奖励通路(连接腹侧被盖区、阿肯色核和前额叶皮层的脑回路)中释放的多巴胺越多,释放多巴胺的速度越快,这种药物就越容易上瘾。
大脑中的多巴胺奖励途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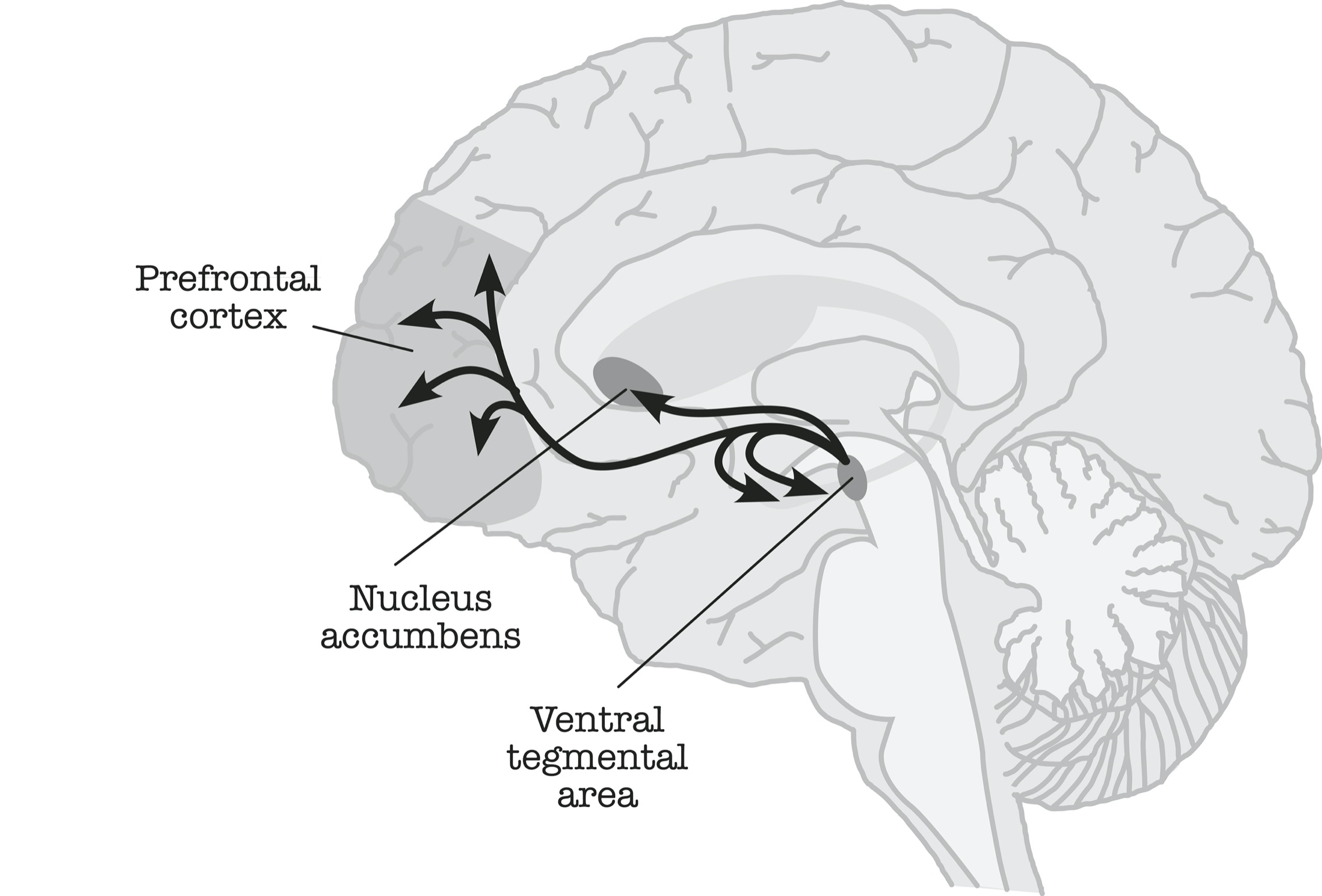
这并不是说高多巴胺物质真的含有多巴胺。相反,它们会在我们大脑的奖励途径中触发多巴胺的释放。
对于盒子里的老鼠来说,巧克力会使大脑中多巴胺的基础输出量增加55%,性行为增加100%,尼古丁增加150%,而可卡因增加225%。安非他明是街头毒品 “speed”、“ice “和 “shabu “的活性成分,也是用于治疗注意力缺失症的药物如Adderall的活性成分,它能使多巴胺的释放增加1000%。据此计算,吸食一次冰毒相当于十次高潮。
奖励和多巴胺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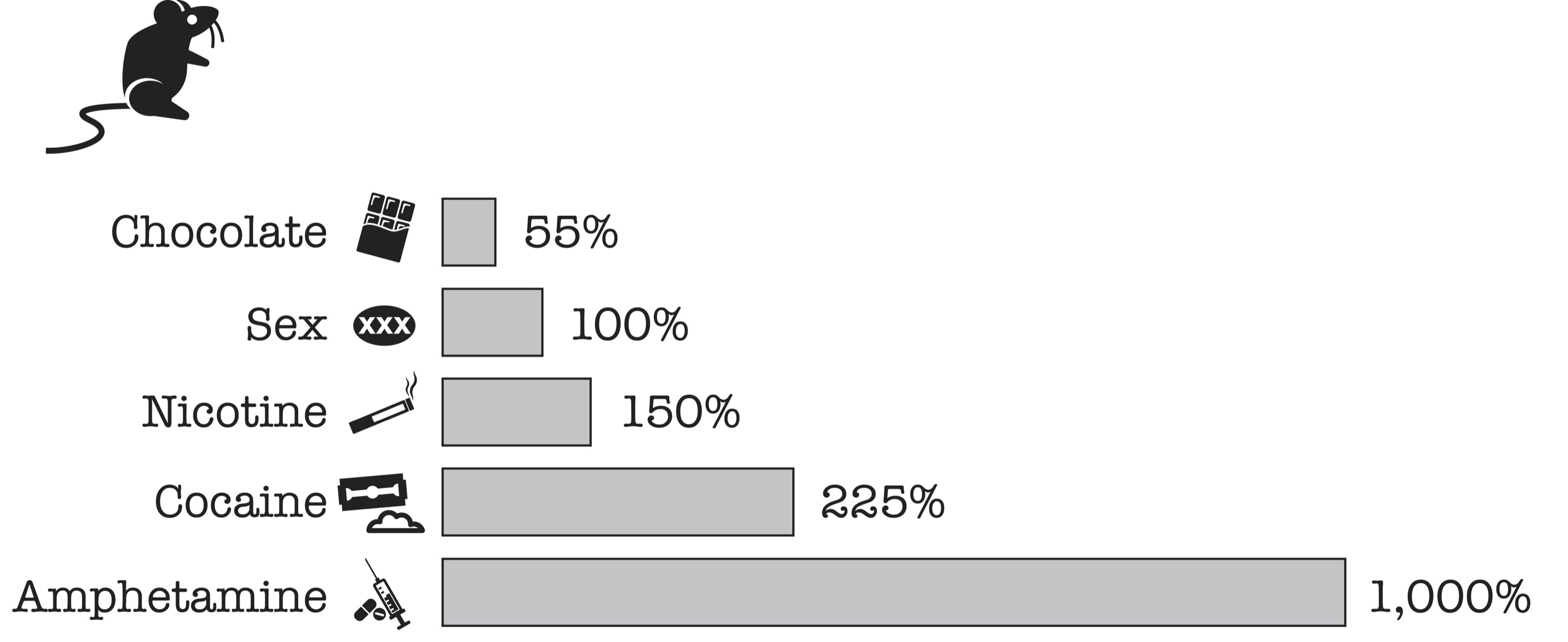
快乐和痛苦是共存的
除了发现多巴胺之外,神经科学家还确定,快乐和疼痛在重叠的脑区中被处理,并通过一个对手处理机制发挥作用。另一种说法是,快乐和痛苦的工作方式就像一种平衡。
想象一下,我们的大脑包含一个天平–在中心有一个支点的天平。当天平上没有任何东西的时候,它与地面是平的。当我们体验到快乐时,多巴胺就会在我们的奖励途径中释放,天平就会向快乐的一方倾斜。我们的天平倾斜得越多,倾斜得越快,我们感到的快乐就越多。

但这里是关于平衡的重要事情。它希望保持水平,也就是说,处于平衡状态。它不希望长时间向某一方倾斜,也不希望长时间向另一方倾斜。因此,每当天平向快乐倾斜时,强大的自我调节机制就会启动,使其再次保持水平。这些自我调节机制不需要有意识的思考或意志的行动。它们只是发生了,就像一个反射。
我倾向于把这种自我调节系统想象成小精灵,在天平的痛苦一侧跳动,以抵消快乐一侧的重量。小精灵代表了平衡的工作:任何生物系统都有保持生理平衡的趋势。

一旦平衡被拉平,它就会一直走下去,向痛苦的一方倾斜等量和相反的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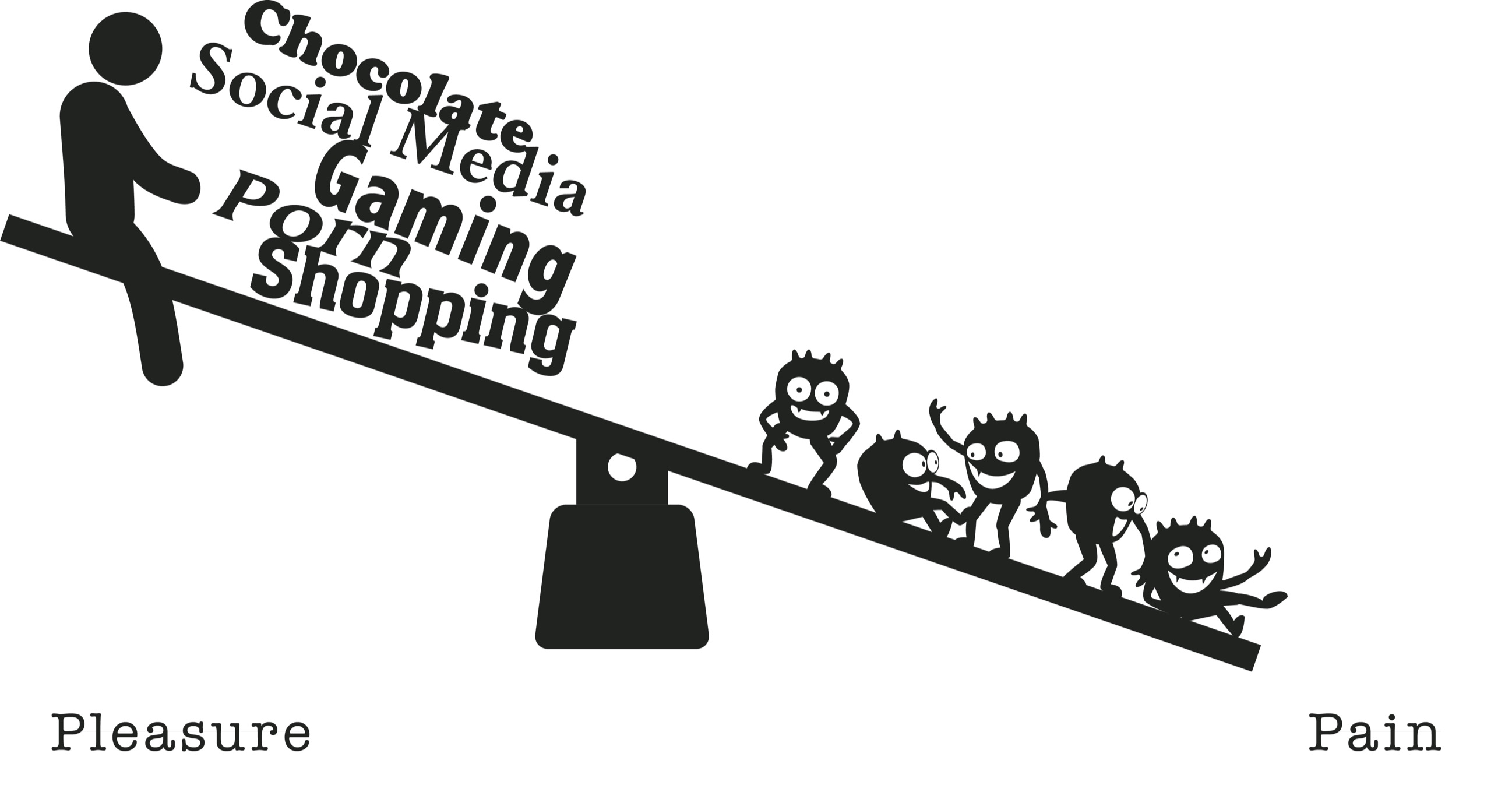
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科学家理查德-所罗门和约翰-科比把快乐和痛苦之间的这种相互关系称为对手过程理论:“任何长期或反复,偏离享乐或情感的中立性……都有代价”。这种代价是一种 “事后反应”,与刺激物的价值相反。或者正如老话所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事实证明,人体的许多生理过程都受类似的自我调节系统的支配。例如,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埃瓦尔德-赫林和其他人已经证明了颜色感知是如何被一个对手过程系统所支配的。持续地仔细观察一种颜色,会自发地在观察者的眼中产生一种 “对立 “颜色的图像。盯着白色背景下的绿色图像看一段时间,然后把目光移到空白的白纸上,你就会看到你的大脑是如何产生一个红色的残影。对绿色的感知相继让位于对红色的感知。当绿色被打开时,红色就不能被打开,反之亦然。
耐受性(神经适应性)
我们都经历过在快乐之后的渴望。无论是伸手去拿第二块土豆片,还是点击链接去玩另一轮电子游戏,我们都很自然地想要重新创造那些美好的感觉,或者试图不让它们消逝。简单的解决办法是继续吃,或玩,或看,或读。但这有一个问题。
随着反复接触相同或类似的快乐刺激,最初对快乐一方的偏离会越来越弱,越来越短,而对痛苦一方的事后反应会越来越强,越来越长,这个过程科学家称之为神经适应。也就是说,随着重复,我们的小精灵变得更大、更快、更多,我们需要更多我们选择的药物来获得同样的效果。
需要更多的物质来感受快感,或者在一定剂量下体验到更少的快感,这被称为耐受性。耐受性是成瘾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我来说,第二次阅读《暮光之城》传奇是很愉快的,但没有第一次那么愉快。当我第四次读它时(是的,我读了整部传奇四次),我的乐趣明显减少了。重读的时候,从来没有达到第一轮的效果。此外,每一次阅读,我都对它的后果有更深的不满意感,并有更强烈的愿望来恢复我第一次阅读时的感觉。随着我对*《暮光之城》*的 “宽容”,我被迫去寻找同一种药物的更新、更有力的形式,以试图重新获得早期的感觉。
随着长期、大量地使用毒品,快乐-痛苦的平衡最终会偏向痛苦一方。我们的享乐(快乐)设定点改变了,因为我们体验快乐的能力下降了,而我们对痛苦的脆弱性上升了。你可以把这看作是小精灵们在天平的疼痛一侧安营扎寨,拖着充气床垫和便携式烧烤架。

我在21世纪初开始敏锐地意识到高多巴胺成瘾物质对大脑奖赏通路的这种影响,当时我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病人因慢性疼痛来诊所接受大剂量、长期的阿片类药物治疗(想想奥施康定、维柯丁、吗啡、芬太尼)。尽管他们长期服用大剂量阿片类药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疼痛只会越来越严重。为什么?因为接触阿片类药物导致他们的大脑将其快乐-痛苦的平衡重置到痛苦的一边。现在他们原来的疼痛更严重了,而且他们身体的某些部位出现了新的疼痛,而这些部位以前是没有疼痛的。
这种现象被广泛观察到并被动物研究所验证,被称为阿片类药物诱导的痛觉减退症。痛觉,来自希腊语algesis,意思是对疼痛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当这些病人逐渐停止使用阿片类药物时,他们中的许多人经历了疼痛的改善。
神经科学家诺拉-沃尔科(Nora Volkow)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大量、长期消费高多巴胺物质最终会导致多巴胺缺乏的状态。
沃尔科研究了健康对照组与对各种药物成瘾的人在停止使用两周后大脑中的多巴胺传输情况。大脑图像令人震惊。在健康对照组的大脑图片中,大脑中与奖励和动机有关的肾豆形区域亮起了鲜红色的灯光,表明多巴胺神经递质的活动水平很高。在两周前停止使用的成瘾者的图片中,大脑中同样的肾豆形区域几乎没有红色,表明很少或没有多巴胺传输。
正如沃尔科博士和她的同事写道:“药物滥用者中DAD2 受体的减少,再加上DA释放的减少,将导致奖励电路对自然奖励刺激的敏感性下降”。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没有什么感觉是好的了。
换句话说,多巴胺团队的球员带着他们的球和他们的手套回家了。
成瘾对多巴胺受体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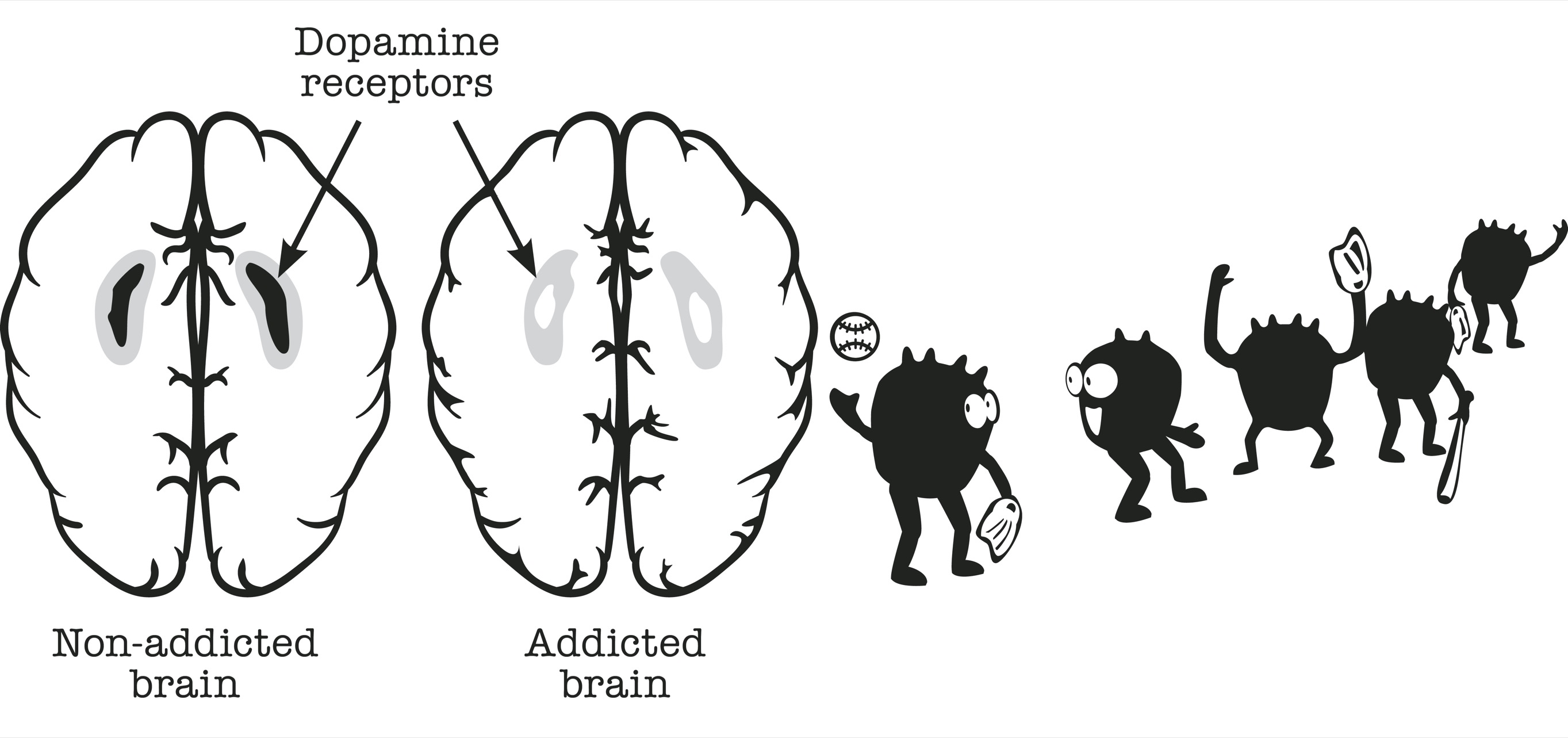
在我强迫性地阅读爱情小说的大约两年时间里,我最终到达了一个地方,我找不到一本我喜欢的书。仿佛我已经烧毁了我的小说阅读快乐中心,没有一本书能使它恢复。
矛盾的是,享乐主义,即为了追求快乐而追求快乐,会导致失语症,也就是无法享受任何形式的快乐。阅读一直是我快乐和逃避的主要来源,所以当它停止工作时,我感到震惊和悲痛。即便如此,也很难放弃。
我的成瘾病人描述了他们如何到达一个点,即他们的药物不再对他们起作用。他们不再有任何兴奋感。然而,如果他们不服药,他们就会感到很痛苦。戒断任何成瘾物质的普遍症状是焦虑、易怒、失眠和精神障碍。
快乐与痛苦的平衡向痛苦的一方倾斜是促使人们在持续戒断后复发的原因。当我们的天平向痛苦一方倾斜时,我们就会渴望得到药物,以感觉到正常(平衡)。
神经科学家乔治-库伯(George Koob)将这种现象称为 “dysphoria driven relapse”,在这种情况下,重新使用毒品的动机不是为了寻求快乐,而是为了减轻长期戒断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痛苦。
这里有一个好消息。如果我们等待的时间足够长,我们的大脑(通常)会重新适应没有药物的情况,我们会重新建立我们的基线平衡:一个水平平衡。一旦我们的平衡达到水平,我们就能再次在日常的、简单的奖励中获得快乐。去散步。看着太阳升起。与朋友一起享受美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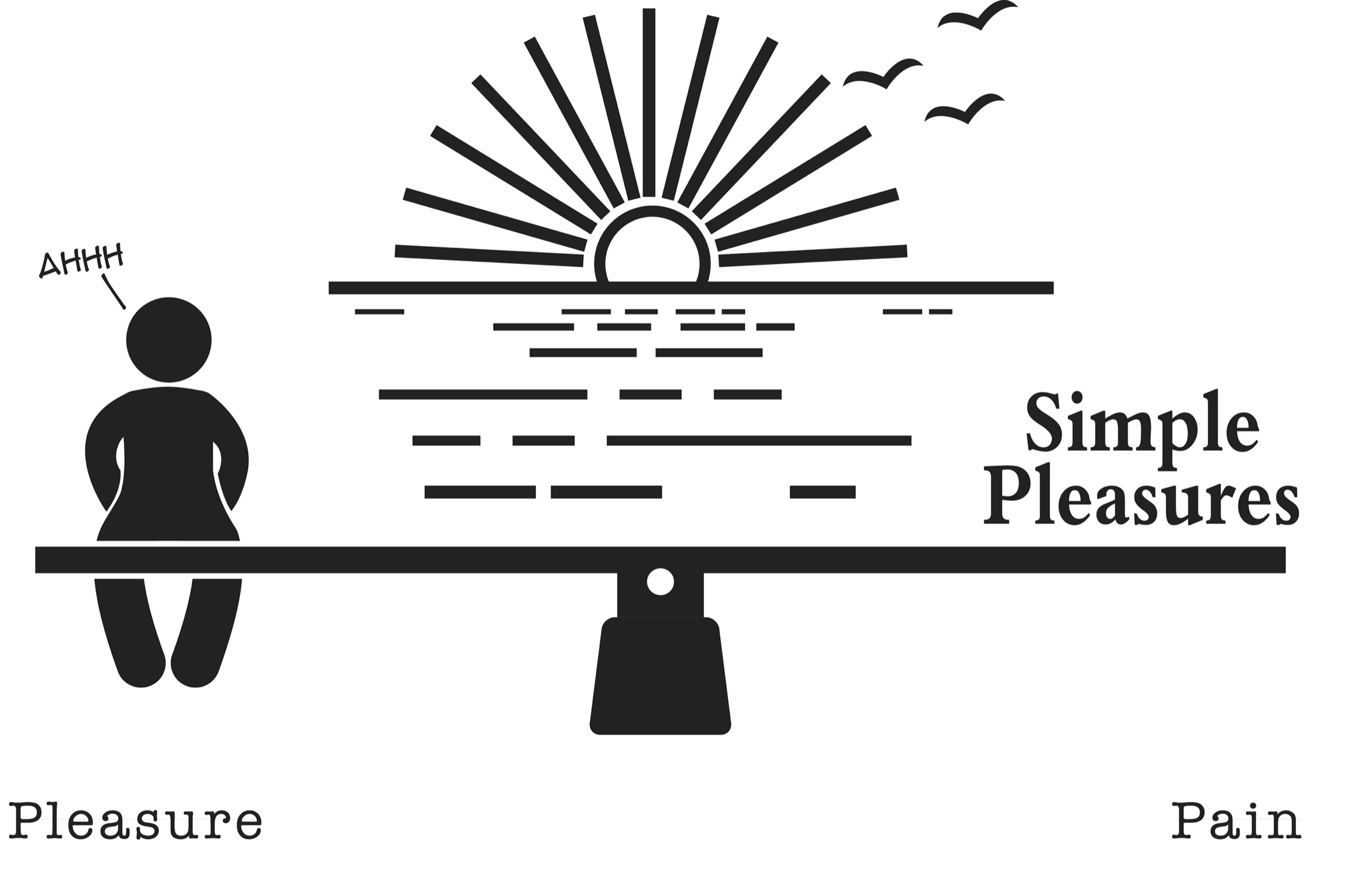
人、地、物
快乐与痛苦的平衡不仅由重新接触毒品本身引发,而且由接触与使用毒品有关的线索引发。在匿名酗酒者协会中,描述这种现象的口头禅是人、地方和事物。在神经科学的世界里,这被称为线索依赖性学习,也被称为古典(巴甫洛夫)条件。
1904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伊万-巴甫洛夫(Ivan Pavlov)证明,当狗看到一块肉时,会反射性地流口水。当肉的呈现一直与蜂鸣器的声音相匹配时,狗听到蜂鸣器就会流口水,即使没有肉立即出现。解释是,狗,学会了将肉块(一种自然奖励)与蜂鸣器(一种条件提示)联系起来。大脑中发生了什么?
通过将检测探针插入大鼠的大脑,神经科学家可以证明,在奖励本身被摄入(如注射可卡因)之前,多巴胺就已经在大脑中对条件线索(如蜂鸣器、节拍器、灯光)做出反应而释放。奖励前对条件线索的多巴胺刺激解释了当我们知道好东西即将到来时,我们所经历的预期快乐。
多巴胺水平。预期和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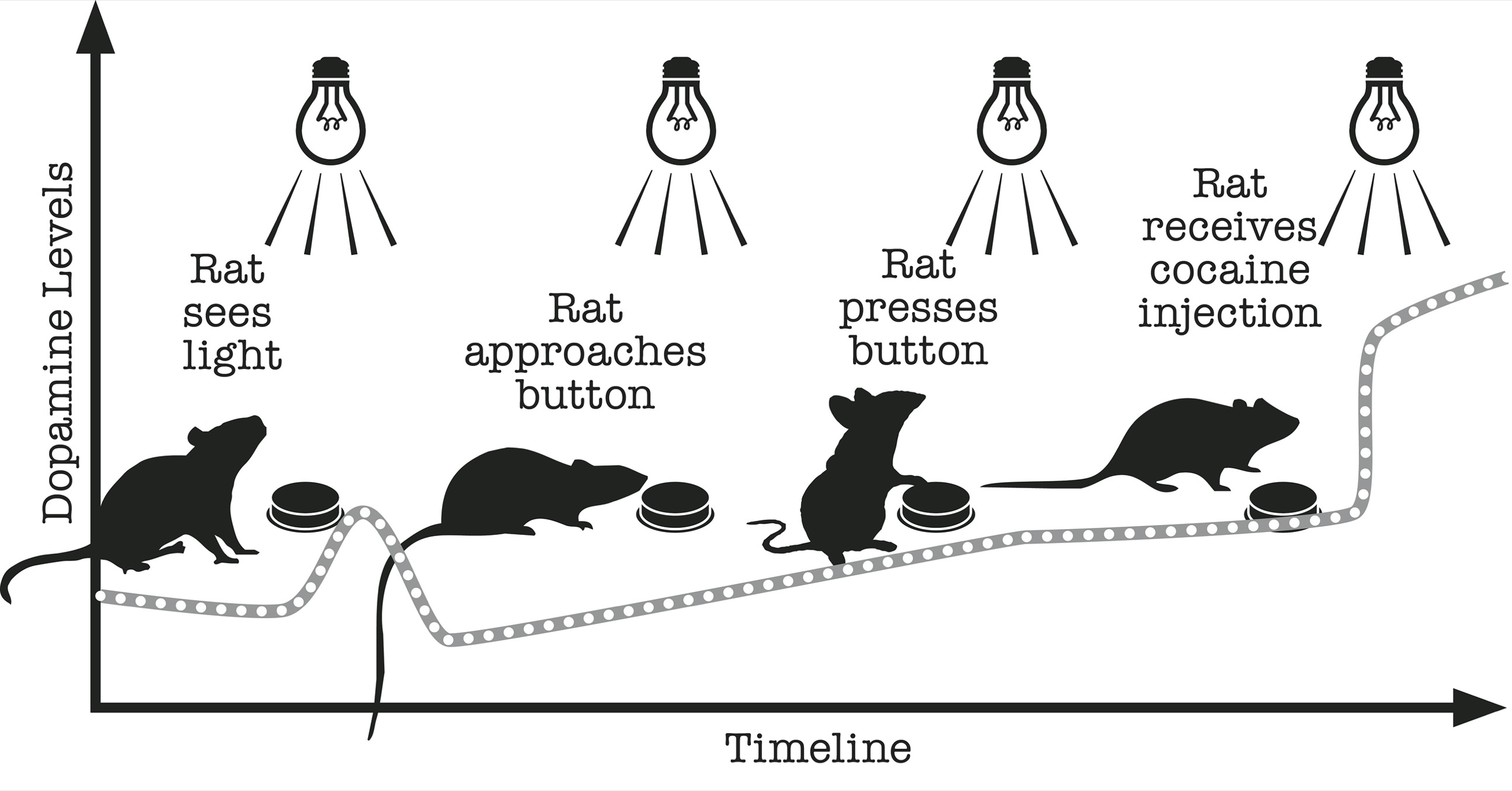
在条件提示之后,大脑中的多巴胺发射不仅下降到基线水平(即使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大脑也有一个多巴胺发射的强直水平),而且低于基线水平。这种短暂的多巴胺小缺失状态是促使我们寻找奖励的原因。多巴胺水平,低于基线水平,驱动渴望。渴望转化为有目的的活动以获得药物。
我的同事罗伯-马伦卡(Rob Malenka),一位受人尊敬的神经科学家,曾经对我说:“衡量一个实验室动物的成瘾程度,要看这个动物为了获得药物愿意付出多大的努力–按下杠杆,穿越迷宫,爬上滑道。“我发现人类的情况也是如此。更不用说预期和渴望的整个周期可能发生在有意识的门槛之外。
一旦我们得到预期的奖励,大脑中的多巴胺发射就会增加,远远超过调和基线。但如果我们预期的奖励没有实现,多巴胺水平就会下降到远低于基线。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得到了预期的奖励,我们会得到一个更大的峰值。如果我们没有得到预期的奖励,我们就会经历一个更大的暴跌。
多巴胺水平。预期和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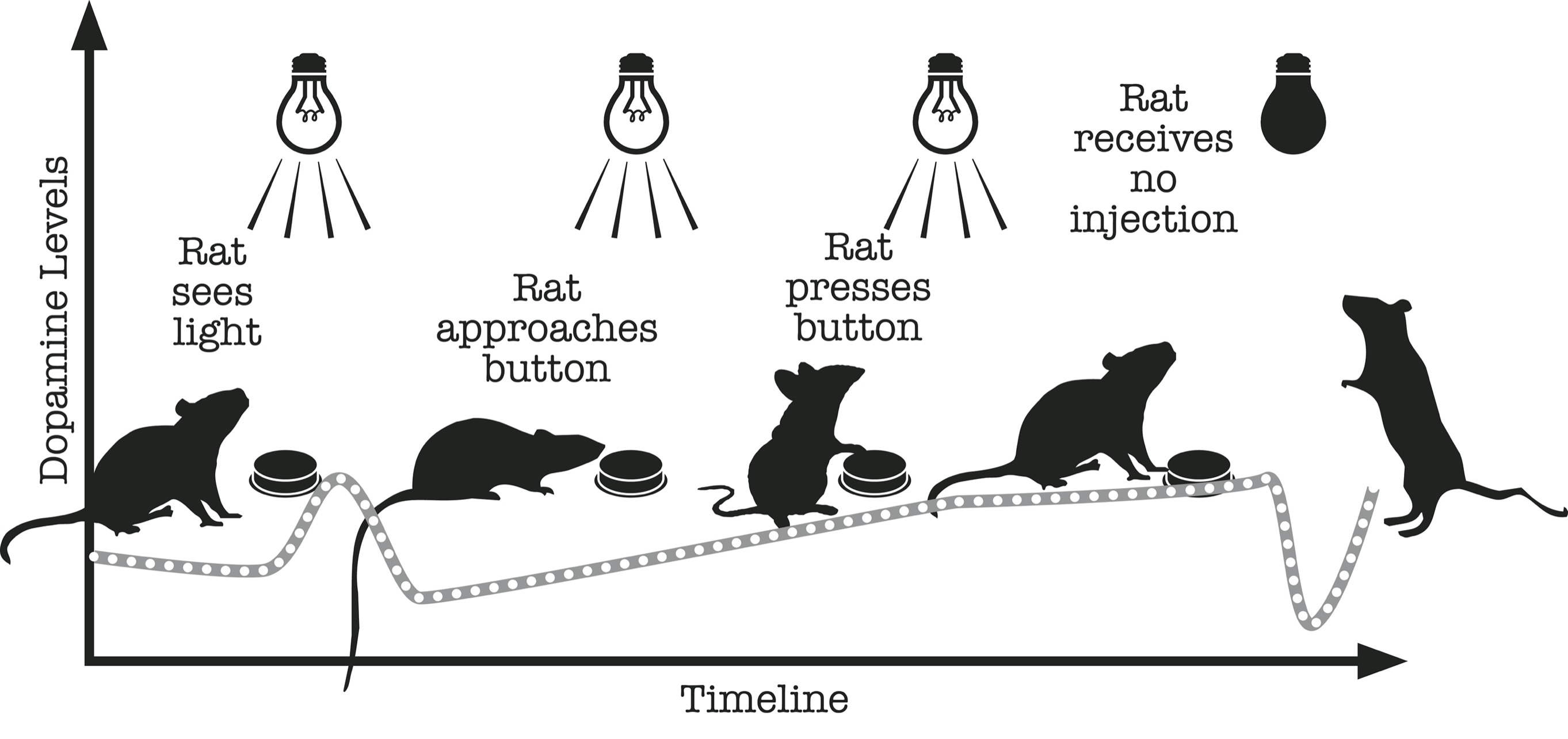
我们都经历过期望落空的情况。未能实现的预期奖励比一开始就没有预期的奖励更糟糕。
提示引起的渴望如何转化为我们的快乐-痛苦平衡?在对未来奖赏的预期中,天平向快乐一方倾斜(多巴胺小高峰),紧接着在提示之后向痛苦一方倾斜(多巴胺小缺失)。多巴胺缺失是对毒品的渴望,并推动了寻求毒品的行为。
在过去的十年中,人们在了解病态赌博的生物学原因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导致《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的赌博障碍被重新归类为成瘾性疾病。
研究表明,赌博导致的多巴胺释放与奖励传递的不可预测性有关,也与最终(通常是金钱)奖励本身有关。赌博的动机主要是基于无法预测奖励的发生,而不是基于经济收益。
在2010年的一项研究中,Jakob Linnet和他的同事测量了沉迷于赌博的人和健康对照组在赢钱和输钱时的多巴胺释放。两组人在赢钱时没有明显差异;然而,与对照组相比,病态赌徒在输钱时显示出多巴胺水平的明显增加。当输钱和赢钱的概率几乎相同(50%)时,奖励途径中的多巴胺释放量最高–代表最大的不确定性。
赌博障碍突出了奖励预期(奖励前的多巴胺释放)和奖励反应(奖励后或奖励期间的多巴胺释放)之间的微妙区别。我的赌博成瘾的病人告诉我,在玩的时候,他们的一部分想输。他们输得越多,继续赌博的冲动就越强烈,而当他们赢的时候就越兴奋–这种现象被描述为 “追寻损失”。
我怀疑社交媒体应用程序也有类似的情况,其他人的反应是如此反复无常和不可预测,以至于获得 “喜欢 “或一些类似的东西的不确定性与 “喜欢 “本身一样具有强化作用。
-
大脑通过改变产生多巴胺的神经元的形状和大小来编码对奖励及其相关线索的长期记忆。例如,树突,即神经元的分支,在回应高多巴胺奖励时变得更长、更多。这一过程被称为经验依赖的可塑性。这些大脑变化可以持续一生,并在药物不再使用后长期存在。
研究人员通过在一周内连续几天给大鼠注射相同数量的可卡因,并测量它们在每次注射后的奔跑程度,来探索可卡因暴露对大鼠的影响。注射了可卡因的大鼠会跑过笼子,而不是像正常大鼠那样保持在外围。通过使用投射在笼子上的光束,可以测量跑动的数量。大鼠打破光束的次数越多,它的跑动就越多。
科学家们发现,随着可卡因接触的每一天,大鼠从第一天的活泼慢跑,到最后一天的彻底狂奔,显示出对可卡因影响的累积性敏感。
一旦研究人员停止注射可卡因,大鼠就不再奔跑。一年后–这对老鼠来说是名副其实的一生–科学家们给老鼠重新注射了一次可卡因,老鼠们立即像在最初实验的最后一天那样跑了起来。
当科学家们检查大鼠的大脑时,他们看到可卡因在大鼠的奖励途径中引起的变化与持续的可卡因敏感化一致。这些发现表明,像可卡因这样的药物可以永远改变大脑。其他成瘾物质也有类似的发现,从酒精到阿片类药物到大麻。
在我的临床工作中,我看到那些与严重成瘾作斗争的人,即使在戒断多年后,只要接触一次,就会马上滑回到强迫性使用中。这可能是由于对所选择的药物持续敏感,以及早期使用药物的遥远回声而发生的。
-
学习也会增加大脑中多巴胺的发射。与饲养在标准实验室笼子里的老鼠相比,在多样化、新奇和刺激性环境中饲养了三个月的雌性老鼠显示出大脑奖励途径中富含多巴胺的突触的扩散。在刺激和新奇环境下发生的大脑变化与高多巴胺(成瘾性)药物的变化相似。
但如果同样的大鼠在进入强化环境之前用兴奋剂,如甲基苯丙胺(一种高度成瘾的药物)进行预处理,它们就不能显示出之前在强化环境中看到的突触变化。这些发现表明,甲基苯丙胺限制了大鼠的学习能力。
这里有一些好消息。我的同事伊迪-沙利文(Edie Sullivan)是研究酒精对大脑影响的世界专家,她研究了从成瘾中恢复的过程,发现尽管一些因成瘾导致的大脑变化是不可逆的,但有可能通过创建新的神经网络绕过这些受损区域。这意味着,虽然大脑的变化是永久性的,但我们可以找到新的突触途径来创造健康行为。
同时,未来有诱人的可能性,即扭转成瘾的伤痕。文森特-帕斯科利和他的同事给大鼠注射可卡因,大鼠表现出预期的行为变化(狂奔),然后使用光遗传学–一种涉及使用光来控制神经元的生物技术–逆转可卡因造成的大脑突触变化。也许有一天,光遗传学在人类大脑上将成为可能。
平衡只是一个比喻
在现实生活中,快乐和痛苦比天平的工作原理更复杂。
对一个人来说是快乐的东西,对另一个人来说可能不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首选药物”。
快乐和痛苦可以同时发生。例如,我们在吃辛辣食物时可以同时体验到快乐和痛苦。
不是每个人在开始时都有一个平衡点。那些患有抑郁症、焦虑症和慢性疼痛的人,开始时的天平倾向于疼痛一边,这可能解释了为什么患有精神障碍的人更容易上瘾。
我们对疼痛(和快乐)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们赋予它的意义的影响。
亨利-诺尔斯-比彻(1904-1976)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意大利和法国担任军医。他观察并报告了225名在战区受重伤的士兵。
比彻对他的研究纳入标准很严格,只调查了那些 “有五种具有代表性的重伤之一的人;广泛的周边软组织损伤、长骨复合骨折、头部被穿透、胸部被穿透或腹部被穿透……精神上很清醒,……在接受询问时没有休克”。
比彻有一个了不起的发现。这些受重伤的士兵中有四分之三报告说,尽管有生命危险,但他们在受伤后立即,几乎没有疼痛。
他的结论是,他们的身体痛苦被逃离 “极其危险的环境,一个充满疲劳、不适、焦虑、恐惧和真正死亡危险的环境 “的情绪缓解。他们的痛苦,比如说,给了他们 “,一张通往医院安全的门票”。
相比之下,《*英国医学杂志》*1995年发表的一份病例报告详细介绍了一名29岁的建筑工人的情况,他在,脚先落在一根15厘米长的钉子上,钉子从他的建筑靴顶部伸出来,已经穿透了皮革、肉和骨头,走进了急诊室。“钉子的最小移动都很痛苦,[而且]他被芬太尼和咪达唑仑镇住了,“强大的阿片类药物和镇静剂。
但是,当钉子从下面被拔出来,靴子被脱掉时,很明显,“钉子已经穿透了脚趾之间:脚完全没有受伤”。
-
科学告诉我们,每一种快乐都是有代价的,随之而来的痛苦比引起快乐的快乐更持久、更强烈。
随着长期和反复接触愉悦的刺激,我们容忍疼痛的能力会下降,而我们体验快乐的阈值会增加。
通过印上即时和永久的记忆,我们即使想忘记快乐和痛苦的教训,也无法忘记:海马体的纹身将持续一生。
在整个进化过程中,处理快乐和痛苦的系统性超古代神经机制在不同的物种中基本保持完好。它完美地适应了一个匮乏的世界。没有快乐,我们就不会吃喝拉撒,也不会繁衍后代。没有痛苦,我们就不能保护自己免受伤害和死亡。通过用反复的快乐提高我们的神经设定点,我们成为无止境的奋斗者,永远不会满足于我们所拥有的,总是在寻找更多。
但问题就出在这里。人类是终极追求者,对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的挑战反应太好。结果,我们把世界从一个匮乏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压倒性的丰富的地方。
我们的大脑不是为这个丰富的世界而进化的。正如在长期久坐的情况下研究糖尿病的汤姆-菲纽肯博士所说,“我们是雨林中的仙人掌”。而且就像适应干旱气候的仙人掌一样,我们正淹没在多巴胺中。
净效应是,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奖励来感受快乐,而更少的伤害来感受痛苦。这种重新调整不仅发生在个人层面,也发生在国家层面。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这个新的生态系统中生存和发展?我们如何培养我们的孩子?作为21世纪的居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新思维和行动方式?
有谁能比那些最容易受其影响的人更能教我们如何避免强迫性过度消费:那些与成瘾作斗争的人。几千年来,在不同的文化中,吸毒者被当作异类、寄生虫、贱民和道德败坏的传播者而被抛弃,但他们已经进化出一种智慧,完全适合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
以下是为一个对奖励感到厌倦的世界提供的恢复教训。
第二部分
自装订
第四章
多巴胺禁食
我在这里是因为我的父母让我来的。“大利拉用美国青少年的特点–闷闷不乐的声音说道。
“好的,“我说。“你的父母为什么要你见我?”
“他们认为我抽了太多的大麻,但我的问题是焦虑。我抽烟是因为我很焦虑,如果你能在这方面做些什么,那么我就不需要大麻了。”
我顿时被一种压倒性的悲伤所笼罩。不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推荐什么,而是因为我担心她不会接受我的建议。
“好吧,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我说。“告诉我你的焦虑症。”
长腿和优雅,她把双腿折叠在身下。
“她说:“这是从初中开始的,这些年来情况越来越糟。焦虑就像是我早上醒来时的第一感觉。打蜡笔是唯一能让我下床的事情。”
“你的蜡笔?”
“是的,我现在吸食毒品。我过去一直使用烟枪和烟斗,白天使用Sativa,睡觉前使用Indica。但现在我喜欢浓缩物……蜡、油、芽、碎片、剪刀、灰尘、QWISO。我大部分时间用的是Vape笔,但有时也用Volcano。我不喜欢吃的东西,但我会在两者之间或在不能吸烟的紧急情况下使用它们”。
D代表数据
通过促使她说出更多关于她的 “蜡笔”,我邀请大利拉深入了解她日常使用蜡笔的具体细节。我与她的谈话是以我多年来开发的框架为指导,与病人讨论强迫性过度消费的问题。
这个框架很容易被人记住,缩写为DOPAMINE,它不仅适用于酒精和尼古丁等传统毒品,也适用于任何我们长期摄入过多的高多巴胺物质或行为,或者只是希望我们与之有一个稍微不那么折磨的关系。虽然最初是为我的专业实践开发的,但我也把它应用于我自己和我自己的不良消费习惯。
-
DOPAMINE中的d代表数据。我从收集消费的简单事实开始。在大利拉的案例中,我探讨了她在使用什么,有多少,以及多长时间。
说到大麻,德利拉所描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产品和给药机制是我的病人如今的标准做法。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来找我的时候,已经有了相当于大麻博士的学历。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当娱乐性的周末使用是常态时,我的病人从早上醒来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吸烟,并持续一整天,直到他们再次入睡。这在很多方面都令人担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每天使用与成瘾有关。
就我自己而言,当阅读言情小说开始占用每天和几天的时间时,我开始怀疑自己正在向危险区摇摆。
O代表着目标
“吸烟对你有什么好处?“我问黛利拉。“它有什么帮助?”
“这是唯一对我的焦虑起作用的东西,“她说。“如果没有它,我就会失去功能……。我的意思是比我现在更不正常”。
-
在要求黛利拉告诉我大麻对她的帮助时,我是在验证大麻在做一些积极的事情,否则她就不会使用它。
DOPAMINE中的O代表使用的目标。即使是看似非理性的行为也是源于一些个人逻辑。人们出于各种原因使用高多巴胺物质和行为:为了好玩,为了适应,为了解闷,为了控制恐惧、愤怒、焦虑、失眠、抑郁、注意力不集中、疼痛、社交恐惧症……不胜枚举。
我利用浪漫来逃避对我来说是从养育幼儿到养育青少年的痛苦过渡,我觉得自己对这项工作不太熟练。我也在安抚我的悲痛,因为我从未再有过孩子,这是我想要的,而我丈夫却没有,这在我们的婚姻和性生活中造成了一种以前不存在的紧张。
P代表问题
“吸烟有什么坏处吗?意想不到的后果?“我问道。
“吸烟的唯一坏处,“德利拉说,“是我的父母总是在我的背后。如果他们能放过我,就不会有任何坏处了。”
我停顿了一下,注意到阳光在她的头发上闪闪发光。尽管她每天摄入超过一克的大麻,但她仍然是健康的形象。我想,年轻可以补偿很多东西。
-
DOPAMINE中的p代表与使用有关的问题**。
高多巴胺药物总是导致问题。健康问题。关系问题。道德问题。如果不是马上,那就是最终。德利拉看不到坏处–除了她和父母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是,是青少年的典型特征……而且不仅仅是青少年。这种脱节的发生有很多原因。
首先,我们大多数人在仍在使用毒品时,无法看到我们使用毒品的全部后果。高多巴胺物质和行为蒙蔽了我们准确评估因果关系的能力。
正如研究红收割机蚂蚁觅食行为的神经科学家丹尼尔-弗里德曼(Daniel Friedman)曾经对我说的那样,“这个世界感官丰富,因果关系贫乏。“这就是说,我们知道当下的甜甜圈味道不错,但我们不太清楚,连续一个月每天吃一个甜甜圈会使我们的腰围增加五磅。
第二,年轻人,甚至是重度使用者,对使用的负面后果更有免疫力。正如一位高中教师对我说的那样,“我最好的一些学生每天都在吸食大麻”。
然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长期使用的非预期后果成倍增加。我的大多数自愿前来接受治疗的病人都是中年人。他们来找我是因为他们已经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他们使用毒品的坏处超过了好处。正如他们在戒酒会上所说的,“我已经厌倦了生病和疲惫”。相比之下,我的青少年患者既没有病也没有累。
即便如此,当青少年仍在使用时,让他们看到他们使用毒品的一些负面后果,即使只是其他人不喜欢,也可以成为让他们停止使用的杠杆。而停止,即使只是一段时间,对于让他们看到真正的因果关系也是至关重要的。
A代表禁欲
“我确实有一个可能帮助你的想法,“我对大利拉说,“但这需要你做一些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是什么?”
“我想让你尝试一个实验。”
“一个实验?“她把头歪向一边。
“我希望你在一个月内停止使用大麻。”
她的脸无动于衷。
“让我解释一下。首先,在你抽那么多大麻的时候,治疗焦虑症的方法不太可能起作用。第二,更重要的是,有一种明显的可能性,如果你停止吸烟整整一个月,你的焦虑会自己好起来。当然,一开始你会因为戒断而感觉更糟。但如果你能度过头两个星期,很有可能在后两个星期你会开始感觉更好”。
她保持沉默,于是我继续说。我向她解释说,任何像大麻那样刺激我们的奖励途径的药物都有可能改变我们大脑的焦虑基线。感觉上像是大麻在治疗焦虑,实际上可能是大麻在缓解我们最后一剂药的戒断。大麻成为我们焦虑的原因,而不是治疗。唯一能确定的方法是停用一个月。
“我可以停一个星期吗?“她问。“我以前也这么做过。”
“一个星期就好了,但根据我的经验,一个月通常是重置大脑奖励途径所需的最少时间。如果你在戒烟四周后没有感觉更好,这也是有用的数据。这意味着大麻并不是驱动因素,我们需要思考还有什么是驱动因素。那么你是怎么想的?你认为你是否能够并愿意停止大麻一个月?”
“嗯。 . . .我认为我现在还没有准备好尝试戒烟,但也许以后会。可以肯定的是,我不会永远像这样抽烟。”
“十年后你还想这样使用大麻吗?”
“不,不可能。绝对不行。“她用力地摇了摇头。
“五年后怎么样?”
“不,五年内也不会。”
“从现在起一年内如何?”
暂停一下。嗤之以鼻。“我想你说到我了,医生。如果我不想在一年内像这样使用,我还不如现在就尝试停止。”
她看着我,笑了笑。“好吧,我们来做这个。”
在要求大利拉根据未来的自己考虑她目前的行为时,我希望戒烟会有新的紧迫性。这似乎已经起了作用。
-
DOPAMINE中的a代表禁欲。
禁欲对于恢复平衡是必要的,而且我们有能力从不太有力的奖励中获得快乐,以及看到我们的物质使用和我们的感觉之间的真正因果关系。从快乐-痛苦平衡的角度来说,禁食多巴胺允许有足够的时间让小精灵跳出平衡,让平衡回到水平位置。
问题是:人们需要戒烟多久才能体验到戒烟带来的大脑益处?
回想一下神经科学家诺拉-沃尔科(Nora Volkow)的成像研究,显示,在戒掉毒品两周后,多巴胺的传输仍然低于正常水平。她的研究与我的临床经验一致,即两周的戒断是不够的。两周后,病人通常仍在经历戒断。他们仍然处于多巴胺缺失状态。
另一方面,四个星期通常就足够了。马克-舒吉特和他的同事研究了一组每天大量饮酒的男子,他们也符合临床抑郁症的标准,或被称为主要抑郁症。
舒基特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实验心理学教授,他最有名的是证明了 “酗酒者 “的亲生儿子与没有这种遗传负担的人相比,患酒精使用障碍的遗传风险更大。在21世纪初的一系列关于成瘾的会议上,我有幸向马克这位有天赋的老师学习。
舒克特研究中的抑郁症患者在医院住了四个星期,在此期间,除了戒酒之外,他们没有接受任何抑郁症的治疗。在不喝酒的一个月后,80%的人不再符合临床抑郁症的标准。
这一发现意味着,对大多数人来说,临床抑郁症,是大量饮酒的结果,而不是同时存在的抑郁症。当然,对这些结果还有其他解释:医院环境的治疗环境、自发缓解、抑郁症的发作性,它可以不受外部因素影响而出现和消失。但鉴于抑郁症的标准治疗方法,无论是药物还是心理治疗,都有50%的反应率,这些有力的发现是非常了不起的。
自然,我见过的病人需要不到四周的时间来重置他们的奖赏途径,而其他人则需要更长的时间。那些长期大量使用烈性药物的人通常需要更多时间。年轻人重新调整的速度比老年人快,他们的大脑可塑性更强。此外,身体上的戒断因毒品而异。对于某些药物,如电子游戏,它可能是轻微的,但对于其他药物,如酒精和苯二氮卓类药物,它可能威胁到生命。
这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重要的警告:我从不建议那些如果突然戒断可能会有生命危险的人使用多巴胺禁食,如严重的酒精、苯并二氮卓(Xanax、Valium或Klonopin)或阿片类药物依赖和戒断的情况。对于这些病人来说,有必要在医学监测下进行减量。
有时,病人问他们是否可以用一种药物换另一种药物:用大麻换尼古丁,用电子游戏换色情。这很少是一个有效的长期策略。
任何奖励如果足够有力,能够克服小精灵,使天平向快乐倾斜,那么它本身就会成瘾,从而导致以一种瘾换另一种瘾(交叉成瘾)。任何不够有力的奖励都不会有奖励的感觉,这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消费高多巴胺奖励时,我们会失去在普通快乐中获得快乐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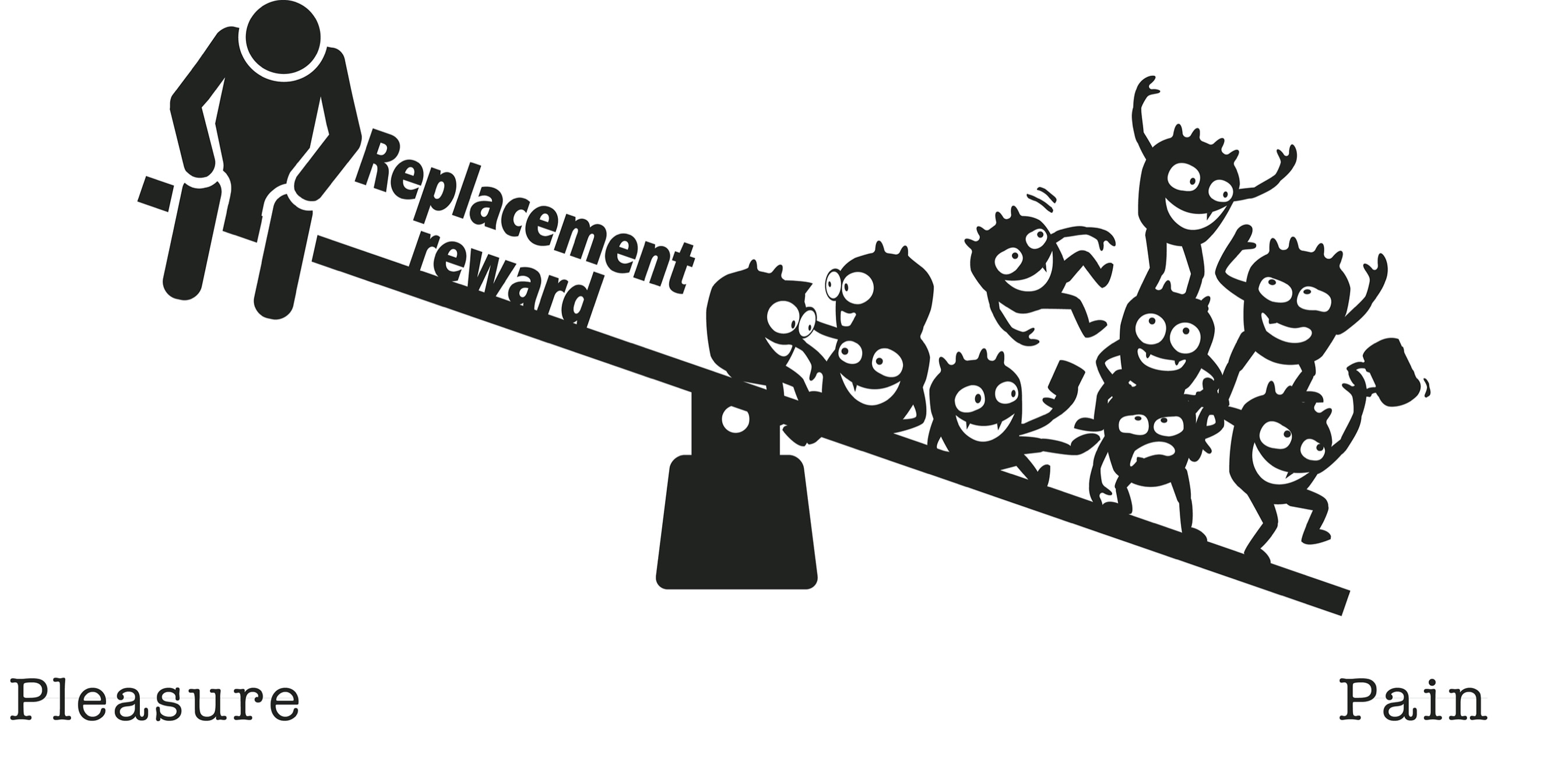
少数病人(大约20%)在快速服用多巴胺后没有感觉好转。这也是很重要的数据,因为它告诉我,药物并不是精神症状的主要驱动力,而且病人很可能有一种共存的精神障碍,需要自己的治疗。
即使多巴胺禁食是有益的,也应该同时治疗共存的精神障碍。在处理成瘾问题时,如果不同时处理其他精神障碍,通常会导致两者的不良结果。
尽管如此,为了体会物质使用和精神症状之间的关系,我需要观察,让病人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脱离高多巴胺的奖励。
M代表正念
“我想让你做好准备,“我对德利拉说,“在你感觉好转之前会感觉更糟。我的意思是,当你第一次停止使用大麻时,你的焦虑会变得更糟。但请记住,这不是你离开大麻后必须忍受的焦虑。这是戒断介导的焦虑。你不使用大麻的时间越长,你就会越快到达那个你感觉更好的地方。通常情况下,病人报告说在两周左右出现转折点。”
“好吧。在这期间我应该做什么呢?你有什么药丸可以给我吗?”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带走痛苦,而且还不会上瘾。既然我们不想用一种成瘾性换取另一种成瘾性,那么我要求你做的就是容忍这种痛苦。”
咽口水。
“是的,我知道。很难。但这也是一个机会。一个让你观察自己与你的思想、情绪和感觉,包括疼痛分开的机会。这种做法有时被称为正念。”
-
DOPAMINE的m代表心态。
正念这个词现在经常被抛来抛去,它已经失去了一些意义。它从佛教冥想的精神传统中演变而来,已被西方采纳并改编为许多不同学科的健康实践。它已经完全渗透到西方人的意识中,以至于现在美国的小学都在例行地教授它。但实际上什么是正念?
正念只是一种能力,在我们的大脑在做什么的时候观察它,而不做判断。这比它听起来要棘手。我们用来观察大脑的器官就是大脑本身。很奇怪,对吗?
当我看着夜空中的银河系时,我总是为我们能成为看起来如此遥远和独立的事物的一部分而感到震惊。练习正念就像观察银河一样:它要求我们把我们的思想和情绪看作是与我们分离的,但同时又是我们的一部分。
另外,大脑可以做一些非常奇怪的事情,其中一些是令人尴尬的,因此需要不做判断。保留判断力对正念的练习很重要,因为一旦我们开始谴责我们的大脑在做什么–Ewww!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我是个失败者。我是个怪人–我们就不再能够观察。保持观察者的位置对于以一种新的方式了解我们的大脑和我们自己是至关重要的。
我记得2001年,我抱着刚出生的婴儿站在厨房里,经历了一个侵入性的画面,就是把她的头砸向冰箱或厨房柜台,看着它像一个软瓜一样内爆。这个画面转瞬即逝,但很生动,如果我不是经常练习正念的人,我一定会尽力忽略它。
起初,我很惊恐。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我曾经治疗过一些母亲,她们由于患有精神疾病,认为她们必须杀死自己的孩子来拯救世界。其中一位母亲真的这么做了,我至今回忆起这个结果都感到悲伤和遗憾。因此,当我经历了一个伤害自己孩子的画面时,我想知道我是否加入了她们的行列。
但我记得要不加判断地观察,我跟着图像和感觉走,发现我并不想打碎我孩子的头;相反,我对这样做有很大恐惧。这种恐惧已经表现为图像。
我没有谴责自己,而是对自己产生了怜悯。我正在努力解决我作为一个新母亲的巨大责任,以及照顾这样一个无助的生物意味着什么,它完全依赖我保护她。
正念练习在戒酒的早期尤其重要。我们中的许多人使用高多巴胺物质和行为来转移我们自己的思想。当我们第一次停止使用多巴胺来逃避时,那些痛苦的想法、情绪和感觉会向我们袭来。
诀窍是停止逃避痛苦的情绪,而是允许自己容忍它们。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时,我们的经验就会呈现出一种新的、意想不到的丰富质地。痛苦仍然存在,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转变,似乎包含了一个巨大的共同痛苦的景观,而不是完全属于我们自己。
当我放弃阅读习惯时,在最初的几个星期里,我被一种存在主义的恐怖所笼罩。晚上我躺在沙发上,,这个时候我通常会伸手去拿一本书或其他一些分散注意力的方法,我双手抱着肚子,试图放松,但却感到充满了恐惧。我很震惊,在我的日常生活中,这样一个看似微小的变化会让我充满如此多的焦虑。
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继续练习,我体验到我的心理界限逐渐放松,意识逐渐开放。我开始看到,我不需要不断地分散自己对当下的注意力。我可以生活在其中,容忍它,甚至可能是更多的东西。
I代表着洞察力
黛利拉同意禁欲一个月。当她回来时,她的皮肤焕发了光彩,驼背的肩膀不见了,她闷闷不乐的神态被灿烂的笑容所取代。她大步走进我的办公室,找了张椅子坐下。
“嗯,我做到了!"。你不会相信的,医生,但我的焦虑已经消失了。消失了!”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最初的几天很糟糕。我觉得很无趣。第二天我就呕吐了。太疯狂了!我从未吐过。我有这种非常恶心的感觉。这时我才意识到我在戒断,这促使我继续戒断。”
“为什么那会激励你?”
“因为这是我拥有的第一个证据,证明我真的上瘾了。”
“那么之后的情况如何?你现在感觉如何?”
“伙计。好多了。哇。焦虑减少了。绝对的。焦虑这个词甚至没有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它曾经统治了我的一天。头脑清晰。我不必担心我的父母闻到它而生气。我在学校也不再焦虑了。妄想症和疑病症……都消失了。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和精神去组织我的下一次高考,匆匆忙忙地去做。不用再这样做了,真是一种解脱。我在省钱。我发现我更喜欢清醒时的活动……比如家庭活动。
“医生,我跟你说实话,我没有看到大麻是个问题。我真的没有看到它。但现在我已经戒烟了,我意识到吸烟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焦虑,而不是治疗焦虑。我已经抽了五年的烟,没有休息过,我没有看到它对我的影响。说实话,我有点震惊”。
-
DOPAMINE的i代表着洞察力。
在临床护理和我自己的生活中,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到,戒除我们所选择的药物至少四个星期的简单练习如何使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有清晰的认识。当我们继续使用时,这种洞察力是根本不可能的。
N代表接下来的步骤
当我对黛利拉的访问即将结束时,我问她下个月的目标。
“那么你怎么看?“我说。“你想在下个月继续弃权,还是想重新使用?”
“清醒的时候,“大利拉说,“我是最好的我。”
我享受着这一时刻。
“但是,“她说,“我仍然非常喜欢大麻,我怀念它给我带来的创造性感觉,以及逃避的感觉。我不想停止使用。我想回去使用,但不是我以前使用的方式”。
-
DOPAMINE的n代表了下一步。
这时我就会问我的病人,他们在戒断一个月后想做什么。在我的病人中,绝大多数能够戒断一个月并体验到戒断的好处的人,仍然想回到使用他们的药物。但他们想用与以前不同的方式使用。最重要的主题是,他们想少用。
成瘾医学领域的一个持续争议是,一直以成瘾方式使用毒品的人是否可以恢复到适度的、非危险的使用。几十年来,匿名酗酒者协会的智慧决定了戒断是成瘾者的唯一选择。
但新出现的证据表明,一些过去符合成瘾标准的人,特别是那些成瘾程度较轻的人,可以通过有控制的方式使用他们选择的药物,回到。根据我的临床经验,情况确实如此。
E代表实验
DOPAMINE的e和最后一个字母代表了实验。
在这里,病人带着新的多巴胺设定点(快乐与痛苦的平衡水平)和一个如何维持它的计划回到世界上。无论目标是继续禁欲还是节制,就像德利拉那样,我们一起制定如何实现目标的战略。通过一个渐进的试验和错误过程,我们找出哪些方法可行,哪些方法不可行。
如果我不指出,节制的目标,特别是对有严重成瘾的人来说,可能会适得其反,导致在戒断一段时间后使用量急剧上升,有时被称为戒断违反效应。
表现出成瘾遗传倾向的大鼠在戒酒两到四周后,一旦再次接触到酒精,,并在此后继续大量使用酒精,就像他们从未戒酒过一样。在接触和迷恋高热量食物的大鼠中也观察到类似的现象。这种影响在遗传上不太倾向于强迫性消费的大鼠和小鼠身上有所减弱。
在动物研究中不清楚的是,这种戒断后的暴饮暴食现象是否是像食物和酒精等有热量的药物所特有的,而在可卡因等无热量的药物中没有看到;或者真正的驱动力是大鼠本身的遗传倾向。
即使在可以实现节制的情况下,我的许多病人,报告说这太累了,无法继续下去,他们最终选择了长期禁欲。
但是对食物上瘾的病人呢?或智能手机?不能完全停止的药物?
如何节制的问题在现代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因为高多巴胺的商品无处不在,使我们都更容易受到强迫性过度消费的影响,即使没有达到临床上的成瘾标准。
此外,由于像智能手机这样的数字毒品已经深入到我们生活的许多方面,为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弄清楚如何节制其消费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为此,我现在介绍一个自我约束策略的分类法。
但在我们谈论自我束缚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多巴胺禁食的步骤,其最终目标是恢复水平平衡(平衡)并更新我们以多种不同形式体验快乐的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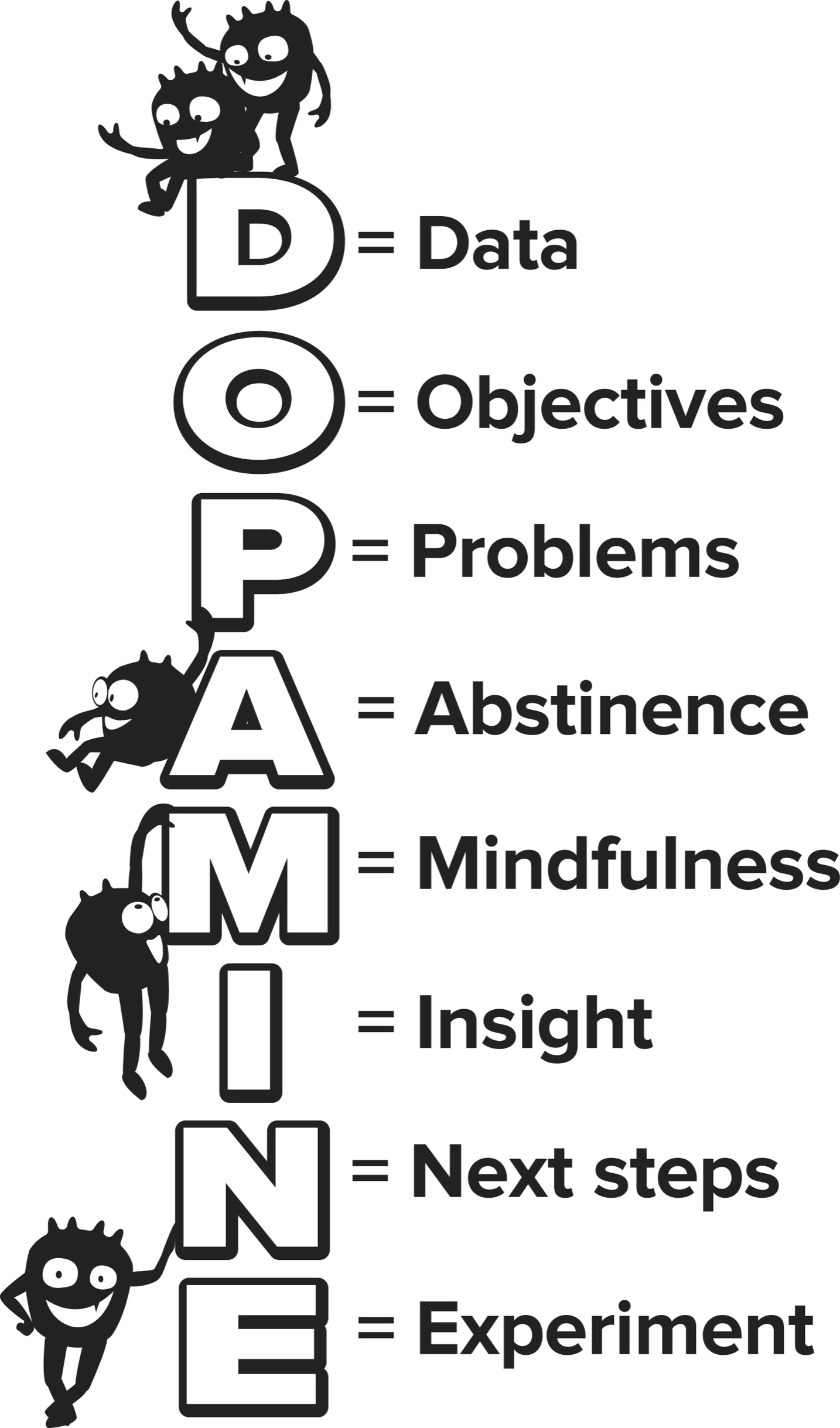
第五章
空间、时间和意义
2017年秋天,在戒除强迫性行为一年后,雅各布复发了。他当时已经六十五岁了。
触发因素是去东欧看望他的家人,由于他的现任妻子和他第一次婚姻的孩子相处不融洽而变得复杂–钱的问题和谁得到什么,这是一个老生常谈。
在他为期三周的旅行中,他的孩子们很生气,因为他没有给他们所要求的钱。他的妻子很生气,因为他甚至在考虑给他们钱。他害怕让任何人失望,因此威胁说要让他们都失望。
他从海外给我发电子邮件,让我知道他在挣扎。他还没有复发,但已接近复发。我做了一些电话辅导,并告诉他一回到家就来找我。他回国一周后来到办公室,但那时已经太晚了。
“是酒店房间里的电视让我又开始渴望,“他对我说。“我想看美国公开赛。我躺在那里翻阅频道,感觉很沮丧,想着我的家人和我的妻子,以及每个人都在对我生气。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裸体女人。在我看电视之前,我是很好的。我没有得到冲动。最大的错误是当我打开电视时,我开始想回到我的旧习惯,而且我无法阻止这些想法。”
“然后发生了什么?”
“在星期二,我回家。我不去工作。我呆在家里看YouTube。我看到人体彩绘……人们在彼此的裸体上作画。我想,这是一种艺术。星期三,我再也忍不住了。我出去买零件,再次制作我的机器。”
“你的电刺激机?”
“是的,“他悲伤地说,只是勉强与我的眼睛对视。“问题是当你开始的时候,你可以在狂喜中待很长时间。这就像处于一种恍惚状态。而这是一种解脱。我不去想别的事情。我不间断地进行20个小时。周三我做了一整天,一直到晚上。周四早上,我把机器零件扔进垃圾桶,然后回去工作。星期五早上,我又把它们从垃圾桶里拿出来修理,用了一整天。周五晚上,我给我的赞助人打电话,周六去参加匿名性行为者会议。星期天,我把零件从垃圾桶里拿出来,再次使用。周一又是如此。我想停止,但我做不到。我应该怎么做呢?”
“把机器和任何备件打包,“我告诉他,“全部扔进垃圾箱。然后把垃圾带到垃圾场或其他你不可能找回的地方。“他点头表示理解。“然后无论何时你有了使用的想法或冲动或渴望,就跪下来祈祷。只是祈祷。请求上帝帮助你,但要从你的膝盖上做起。这很重要。”
我把世俗的和形而上学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太低或太高的。当然,告诉他祈祷是违反不成文的规定的。医生们不谈论上帝。但我相信信仰,而且我的直觉告诉我,这对从小就信奉罗马天主教的雅各布来说会产生共鸣。
告诉他跪下来也是一种方法,可以插入一些肉体的东西,任何东西都可以打破迫使他使用的精神强制力。或者说,我认识到他有一些更深层次的需要,要表现出他的服从。
“在你祈祷之后,“我说,“然后起身给你的担保人打电话。“他又点了点头。
“哦,原谅你自己,雅各布。你不是一个坏男人。你有问题,就像我们其他人一样。”
-
自我束缚是用来描述雅各布扔掉他的机器的行为的术语。它是我们有意和自愿地在我们自己和我们选择的药物之间建立障碍,以减轻强迫性的过度消费。自我约束主要不是一个意志的问题,尽管个人机构发挥了一些作用。相反,自我约束公开承认了意志的局限性。
创造有效的自我约束的关键是,首先要承认我们在强大的强制力的魔法下所经历的自愿性的丧失,并在我们仍然拥有自愿选择能力的时候约束自己。
如果我们等到感到不得不使用时,寻求快乐和/或避免痛苦的反射性拉力几乎是不可能抗拒的。在欲望的悸动中,没有决定权。
但是,通过在我们自己和我们所选择的药物之间制造有形的障碍,我们在欲望和行动之间按下了暂停键。
此外,自我约束已经成为现代的必需品。外部规则和制裁,如对香烟征税,对酒精的年龄限制,以及禁止拥有可卡因的法律,尽管是必要的,但在一个几乎可以无限地获得各种高多巴胺商品的世界上,永远是不够的。
多年来,我的病人一直在告诉我他们的自我约束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我开始把它们写下来。我重新利用我从病人那里学到的策略来建议其他病人,就像我对雅各布所做的那样,我告诉他把他的机器丢在一个偏远的垃圾箱里,这样他以后就不能再取回它了。
我问我的病人:“你可以设置什么样的障碍,使你更难轻易获得你选择的药物?“我甚至在自己的生活中使用自我束缚来处理强迫性过度消费的问题。
自我约束可以分为三大类:物理策略(空间)、时间策略(时间)和分类策略(意义)。
正如你在下面的内容中所看到的,自我约束并不是万无一失的,特别是对那些有严重成瘾的人来说。它也可能成为自欺欺人、恶意和错误科学的牺牲品。
但这是一个良好和必要的起点。
物理自缚
在荷马的奥德修斯从特洛伊战争回家的旅途中,等待他的是许多危险,第一个危险是塞壬,那些半女半鸟的生物,她们迷人的歌声引诱水手在附近岛屿的岩石悬崖上死亡。
水手要想安然无恙地通过塞壬,唯一的办法就是不听她们唱歌。奥德修斯命令他的船员把蜂蜡塞进耳朵里,把他绑在帆船的桅杆上,如果他乞求解开或试图挣脱,就把他绑得更紧。
正如这个著名的希腊神话所说明的那样,自我束缚的一种形式是在我们和我们选择的药物之间建立文字上的物理障碍和/或地理距离。下面是我的病人告诉我的一些例子。“我拔掉了电视插头,把它放在我的衣柜里。““我把我的游戏机放逐到车库里。““我不使用信用卡。只有现金。““我事先给酒店打电话,要求他们撤掉迷你吧。““我事先给酒店打电话,要求他们把迷你吧和电视搬走。““我把我的iPad放在美国银行的保险箱里。”
我的病人奥斯卡是一个年过七旬的胖子,他有一颗,声音洪亮,喜欢说独白,以至于他把集体治疗搞得一团糟,不得不退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在书房里工作、在车库里捣鼓、在花园里摆弄时,喝得酩酊大醉。
通过试验和错误,他了解到,为了防止这种行为,他必须将所有的酒精从家里拿走。任何带入家中的酒精都需要锁在一个只有他妻子才有钥匙的文件柜中。使用这种方法,奥斯卡能够成功地戒酒多年。
但我警告过你,自我束缚并不是保证。有时,障碍本身成为一种挑战的邀请。解决如何获得我们选择的药物的难题成为其吸引力的一部分。
有一天,奥斯卡的妻子在出城的路上,把一瓶昂贵的酒锁在了文件柜里,并带走了钥匙。她离开的第一个晚上,奥斯卡开始思考那瓶酒,他知道它在那里。这个想法像一个物理存在一样闯入了他的意识。它并不痛苦,只是很烦人。如果我去看一眼,确保它都被锁起来了,我就不会再想它了,他告诉自己。
他走到他妻子的书房,拉开抽屉。令他惊讶的是,抽屉打开了半英寸,他可以看到瓶子直立在文件之间。虽然不足以把它拿出来,但足以看到瓶塞,诱人地伸手不见五指。
他站在黑暗的抽屉里凝视了整整一分钟,思索着这瓶酒。他的一部分人想关上抽屉。他的另一部分则无法停止盯着它看。然后,他脑子里的某些东西一闪而过,他决定了–或者说他不再试图不做决定。他开始行动起来。
他急忙去车库拿他的工具箱。他开始工作,使用各种工具试图拆开锁,打开抽屉。他以激光聚焦和决心工作。但他无法打开抽屉。他尝试的每一种工具都未能穿透锁。
然后,答案就像一个结突然在他的手指下松开一样,在他的脑海中闪现。当然了。为什么我以前没有想到呢?这是很明显的。
他坐了起来。现在不需要着急。他的目标就在眼前。他悄悄地收拾了他的工具,除了一把长柄钳。他用长柄钳打开瓶塞,把瓶塞和钳子轻轻放在桌子上,然后去厨房拿他唯一需要的剩余工具:一根长的塑料吸管。
在奥斯卡的文件柜失败的地方,像kSafe厨房保险箱这样的新设备可能已经完成了任务。kSafe大约有一个面包盒大小,由坚不可摧的透明塑料制成,可以容纳从饼干到苹果手机到阿片类药物的所有东西。转动转盘就能将保险箱锁定在一个定时器上。一旦设定了计时器,在时间结束之前,就无法通过锁或穿透透明塑料材料。
-
现在可以从你当地的药房获得物理性的自我束缚。与其把我们的药物锁在文件柜里,我们还可以选择在细胞层面上施加锁。
纳曲酮这种药物被用来治疗酒精和阿片类药物成瘾,同时也被用来治疗其他各种成瘾,从赌博到暴饮暴食到购物。纳曲酮阻断了阿片受体,这反过来又削弱了不同类型的奖励行为的强化作用。
我曾有病人报告说,使用纳曲酮后,他们几乎或完全停止了对酒精的渴望。对于那些与这个问题斗争了几十年的病人来说,能够完全不喝酒,或者像 “正常人 “一样适量地喝酒,是一种启示。
由于纳曲酮阻断了我们的内源性阿片系统,人们有理由怀疑它是否会诱发抑郁症。这方面没有可靠的证据,但我偶尔会看到一些病人报告使用纳曲酮后会出现快感平平的情况。
一位患者对我说:“纳曲酮帮助我不喝酒,但我不像以前那样喜欢吃培根,也不喜欢洗热水澡,而且我不能获得跑步的兴奋感。“我们通过让他在进入有风险的饮酒场合(如欢乐时光)前半小时服用纳曲酮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按需服用纳曲酮的方法使他能够适度饮酒,也能再次享受熏肉。
2014年夏天,我和我的一个学生前往中国,在北京的新医院采访寻求海洛因成瘾治疗的人,新医院是一家自愿的、非政府赞助的成瘾治疗医院。
我们与一名38岁的男子交谈,他描述了在来新医院治疗之前,,他接受了 “成瘾手术”。成瘾手术包括插入长效纳曲酮植入物以阻断海洛因的影响。
“2007年,“他说,“我去了武汉省做手术。我的父母让我去的,他们还付了钱。我不确定外科医生做了什么,但我可以告诉你,那并不奏效。手术后,我不断吸食海洛因。我再也找不到那种感觉了,但我还是做了,因为吸食是我的习惯。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我每天都吸食,没有任何感觉。我没有想过要停止,因为我还有钱买它。六个月后,这种感觉又出现了。所以我现在在这里,希望他们能有新的、更好的东西给我。”
这则轶事说明,如果没有洞察力、理解力和改变行为的意愿,仅靠药物治疗是不可能成功的。
另一种用于治疗酒精成瘾的药物是双硫仑。双硫仑能中断酒精代谢,导致乙醛积累,进而引起严重的脸红反应、恶心、呕吐、血压升高,以及整体感觉不适。
对于那些试图戒酒的人来说,每天服用双硫仑是一种有效的威慑,特别是对于那些早上起来决心不喝酒但到了晚上就失去决心的人来说。事实证明,意志力并不是一种无限的人力资源。它更像是在锻炼肌肉,我们越是使用它,它就会越累。
正如一位病人所说,“有了双硫仑,我只需要每天决定一次不喝酒。我不需要整天不停地决定”。
有些人,最常见的是东亚人,有一种基因突变,导致他们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对酒精产生类似于的双硫仑反应。这些人在历史上的酒精成瘾率较低。
值得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东亚国家酒精消费的增加导致了更高的酒精成瘾率,甚至在这个以前受保护的群体中。科学家们现在发现,那些无论如何都要喝酒的突变者患酒精相关癌症的风险更高。
与所有形式的自我束缚一样,双硫仑是易变的。我的病人阿诺德几十年来一直酗酒,这个问题在他遭受严重中风并失去部分额叶功能后才变得更糟。他的心脏病专家告诉他,他必须戒酒,否则他就会死。赌注很高。
我给他开了双硫仑,并告诉阿诺德,如果他在服药期间喝酒,这种药会让他生病。为了确保阿诺德服药,他的妻子每天早上给他服药,并在服药后检查他的嘴,确保他吞下了药。
有一天,当他的妻子外出时,阿诺德来到酒类商店,买了五分之一的威士忌,并把它喝了。当他的妻子回到家,发现他喝醉了,最让她不解的是为什么双硫仑没有让他生病。阿诺德醉了,但他没有生病。
一天后,他坦白了。在之前的三天里,他没有吞下药片。相反,他把它塞进了一颗缺失的牙齿留下的缝隙中。
-
其他现代形式的身体自我束缚涉及对我们身体的解剖学改变;例如,减肥手术,如胃束带、袖状胃切除术和胃绕道术。
这些手术有效地创造了一个较小的胃和/或绕过了肠道吸收热量的部分。胃箍将一个物理环套在胃上,使其变小,而不切除胃或小肠的任何部分。袖状胃切除术通过手术切除部分胃部,使其变小。胃绕道手术将小肠绕过胃和十二指肠,在那里吸收营养。
我的病人艾米丽在2014年接受了胃绕道手术,从而在一年内从250磅减至115磅。没有其他干预措施–她已经尝试了所有的干预措施–使她能够减肥。艾米丽并不孤单。
减肥手术是一种被证明有效的干预肥胖症的方法,特别是在其他补救措施失败后。但它们并非没有意外的后果。
每四个接受胃绕道手术的人中就有一个人出现了酒精成瘾的新问题。在她的手术后,艾米丽也开始对酒精上瘾。原因有很多。
大多数肥胖的人都有潜在的食物成瘾问题,仅靠手术是不能充分解决的。很少有接受这些手术的人得到他们需要的行为和心理干预,以帮助他们改变他们的饮食习惯。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重新以不健康的方式进食,扩大他们现在较小的胃,并最终出现医疗并发症和需要重复手术。当食物不再是一种选择时,许多人从食物转向另一种药物,如酒精。
此外,手术改变了酒精的代谢方式,增加了酒精的吸收率。没有正常大小的胃意味着酒精几乎瞬间被吸收到血液中,避免了通常发生在胃中的第一道代谢。因此,患者醉酒的速度更快,醉酒的时间更长,就像接受酒精静脉注射一样。
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庆祝一种能够改善如此多的人的健康的医疗干预。但是,我们必须诉诸于切除和重塑内部器官以适应我们的食物供应,这一事实标志着人类消费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
从限制我们进出的锁箱,到阻断我们阿片受体的药物,再到缩小我们胃部的手术,现代生活中随处可见身体的自我束缚,说明我们越来越需要给多巴胺踩刹车。
对我来说,当书籍只需一次点击就能获得时,我很容易在幻想中停留的时间超过我想要的,或者说超过对我有利的时间。我摆脱了我的Kindle和它对稳定的可下载情色小说的便利访问。因此,我能够更好地,以节制我沉溺于糖果小说的倾向。必须去图书馆或书店的简单行为在我和我选择的毒品之间建立了一个有用的屏障。
按时间顺序自行装订
另一种自我约束的形式是使用时间限制和终点线。
通过将消费限制在一天、一周、一个月或一年中的某些时间,我们缩小了消费的窗口,从而限制了我们的使用。例如,我们可以告诉自己只在节假日消费,只在周末消费,不在星期四之前消费,不在下午5点之前消费,等等。
有时,与其说是时间本身,不如说我们根据里程碑或成就来约束自己。我们会等到生日,或一完成任务,或拿到学位后,或一旦得到晋升。当时间流逝,或者我们已经越过了自我指定的终点线,药物就是我们的奖励。
神经科学家S.H.Ahmed和George Koob已经证明,每天不受限制地接触可卡因的大鼠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增加按压杠杆的次数,以至于体力不支甚至死亡。在 延长接触条件(六小时)下,也观察到甲基苯丙胺、尼古丁、海洛因和酒精的自我管理增加。
然而,每天只能接触可卡因一小时的大鼠,在许多连续的,使用稳定的可卡因量。也就是说,它们不会在连续的每一天中按下杠杆以获得更多的药物。
这项研究表明,通过将毒品消费限制在一个狭窄的时间窗口内,我们可能能够节制使用,并避免无限制使用所带来的强迫性和不断升级的消费。
-
仅仅跟踪我们花了多少时间消费,例如,通过对我们的智能手机使用情况进行计时,是意识到并由此减轻消费的一种方式。当我们有意识地利用客观事实,如我们使用了多少时间,我们就不太能够否认它们,因此处于更好的位置,可以采取行动。
然而,这可能会很快变得非常棘手。当我们追逐多巴胺的时候,时间有一种有趣的方式从我们身边溜走。
一位病人告诉我,当他使用甲基苯丙胺时,他说服自己,时间不算数。他觉得自己好像可以在以后把时间缝合起来,而没有人意识到有一块已经丢失了。我想象他漂浮在夜空中,大如一个星座,在宇宙中缝合一个租界。
高多巴胺商品会扰乱我们延迟满足的能力,这种现象称为延迟折扣。
延迟折扣指的是,我们要等待的时间越长,奖励的价值就越低。我们大多数人宁愿今天得到20美元,也不愿意一年后得到。我们高估短期回报而不是长期回报的倾向可能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一个因素是对成瘾药物和行为的消费。
行为经济学家Anne Line Bretteville-Jensen和她的同事调查了活跃的海洛因和安非他明使用者的贴现情况,并与前使用者和匹配的对照组(在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方面匹配的个人)进行了对比。调查人员要求参与者想象他们有一张价值10万挪威克朗(NOK),约14600美元的中奖彩票。
然后他们问参与者,他们是愿意现在得到更少的钱(少于100,000挪威克朗),还是愿意在一周后得到全部的钱。在活跃的吸毒者中,20%的人说他们现在就想要钱,并愿意少拿一点来得到它。只有4%的前吸毒者和2%的匹配对照组愿意接受这种损失。
吸烟者比匹配的对照组更有可能对金钱奖励打折扣(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必须等待更长的时间,他们对金钱奖励的重视程度就会降低)。他们抽得越多,尼古丁消耗得越多,他们对未来奖励的折扣就越大。这些发现对假设的金钱和真实的金钱都适用。
成瘾问题研究人员沃伦-K-比克尔和他的同事要求对阿片类药物成瘾的人和健康对照组完成一个以这句话开始的故事。“醒来后,比尔开始思考他的未来。一般来说,他期望……"。
阿片类药物成瘾的研究参与者提到的未来,,平均为9天。健康对照组提到的未来平均为4.7年。这一惊人的差异说明,当我们在成瘾药物的支配下,“时间视野 “是如何缩小的。
相反,当我问我的病人什么是他们尝试进入康复的决定性时刻时,他们会说一些表达了对时间的长远看法的话。正如一位在过去一年里一直吸食海洛因的病人告诉我的那样,“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吸食了一年的海洛因,我想,如果我现在不停止,我的余生可能都要这样做”。
反思自己整个人生的轨迹,而不仅仅是当下,让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的日常行为有了更准确的盘点。德利拉的情况也是如此,她在想象自己十年后仍在吸食大麻后,才愿意戒除大麻四周。
在今天这个富含多巴胺的生态系统中,我们都已经开始追求即时满足。我们想买东西,第二天它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门槛上。我们想知道什么,下一秒答案就会出现在我们的屏幕上。我们是否正在失去琢磨事情的诀窍,或者在寻找答案时感到沮丧,或者不得不等待我们想要的东西?
神经科学家塞缪尔-麦克卢尔和他的同事研究了大脑的哪些部分参与了选择即时奖励和延迟奖励。他们发现,当参与者选择立即奖励时,大脑中的情绪和奖励处理部分亮起。当参与者延迟奖励时,前额叶皮层–大脑中参与计划和抽象思维的部分–变得活跃。
这里的含义是,我们现在都很容易受到前额叶皮层萎缩的影响,因为我们的奖励途径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主要驱动力。
摄取高多巴胺商品并不是影响延迟折扣的唯一变量。
例如,与那些在资源丰富的环境中长大的人相比,那些在资源匮乏的环境中长大的人更有可能重视即时奖励而不是延迟奖励。生活在贫民窟的年轻巴西人比年龄匹配的大学生更看重未来的回报。
贫穷是成瘾的一个风险因素,尤其是在一个容易获得廉价多巴胺的世界里,这有什么奇怪的?
-
导致强迫性过度消费问题的另一个变量是我们今天拥有的休闲时间越来越多,随之而来的是无聊。
农业、制造业、家务和其他许多以前耗时的劳动密集型工作的机械化,减少了人们每天工作的时间,留下了更多的时间用于休闲。
在美国,就在内战(1861-1865年)之前,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普通工人的典型一天包括每天工作10至12个小时,每周6天半,每年51周,每天用于休闲活动的时间不超过2小时。一些工人,通常是移民妇女,每天工作13个小时,每周工作6天。其他人则是在奴隶制下劳动。
相比之下,,今天美国的休闲时间在1965年至2003年间每周增加了5.1小时,每年增加270个休闲时间。到2040年,美国典型的一天中的休闲时间预计为7.2小时,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3.8小时。其他高收入国家的数字也类似。
美国的休闲时间,因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的不同而不同,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1965年,美国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都享有差不多的休闲时间。今天,生活在美国的没有高中文凭的成年人比拥有学士学位或更高学历的成年人多出42%的闲暇时间,闲暇时间的最大差异发生在工作日的时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没有大学文凭的人就业不足。
多巴胺消费不仅是填补不工作时间的一种方式。它也成为人们不参加工作的一个原因。
经济学家Mark Aguiar和他的同事在一篇题为 “休闲奢侈品和年轻男性的劳动力供应 “的文章中写道:“在过去的15年中,21至30岁的年轻男性比年长的,男性或女性的工作时间下降更多。自2004年以来,时间使用数据显示,年轻男性明显,将他们的休闲转移到视频游戏和其他娱乐性的电脑活动”。
作家Eric J. Iannelli简要地影射了他自己的成瘾史,内容如下。
多年前,在现在看来是另一种生活中,一位朋友对我说:“你的整个存在可以归结为三部分循环。一:被搞死。二:搞砸了。三:破坏。损害控制”。我们认识的时间并不长,大概最多两个月,但他已经目睹了我经常喝得昏天黑地的情况,这只是成瘾的自我循环漩涡中更明显的表现之一,所以他已经得到了我的电话号码。他带着诡异的微笑,继续更普遍地假设–我怀疑只是半开玩笑地假设–成瘾者是无聊或沮丧的问题解决者,当没有其他挑战碰巧出现时,他们本能地设计出胡迪尼式的情况,让自己脱离困境。当他们成功时,药物成为奖励,当他们失败时,药物成为安慰奖。
-
当我第一次见到穆罕默德时,他是一条话语的河流。他的舌头几乎跟不上他的大脑,他的大脑里充满了各种想法。
“我想我可能有一点上瘾问题,“他说。我立刻喜欢上了他。
他用无懈可击的英语,带着轻微的中东口音,向我讲述了他的故事。
他于2007年从中东来到美国,学习本科数学和工程。在他的祖国,任何形式的吸毒都有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
到达美国后,对他来说,能够毫无顾忌地使用毒品是一种解放。开始时,他把吸毒和酗酒限制在周末,但在一年内,他每天都在吸食大麻,可以看到他的成绩和友谊因此受到影响。
他告诉自己,在我完成本科学位,被硕士课程录取,并获得资助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不会再吸烟。
他忠实于自己的承诺,在完成斯坦福大学机械工程硕士课程并获得资助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没有再吸烟。当他重新开始吸烟时,他保证只在周末吸烟。
博士毕业一年后,他每天都在抽烟,到了第二年年底,他为自己制定了新的规则:工作时抽10毫克的烟,不工作时抽30毫克的烟,只有在特殊场合才抽300毫克的烟……才会真正搞起来。
穆罕默德没有通过他的资格考试,这是他博士学习的高潮。他第二次参加考试,再次失败。他即将被终止学业,但他设法说服了他的教授给他最后一次机会。
2015年春天,穆罕默德承诺戒烟,直到他通过资格考试,无论需要多长时间。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戒掉了大麻,并比以前更努力地工作。他的最终报告有100多页长。
“他告诉我,“那是我生命中最积极和最有成效的几年”。
那一年,他通过了资格考试,考试后的晚上,一位朋友带着大麻过来帮他庆祝。起初,穆罕默德拒绝了。但他的朋友说:“像你这么聪明的人不可能上瘾”。
就这一次,穆罕默德告诉自己,然后在毕业前不要再来。
到了星期一,在毕业前不再 吸食大麻,变成了在 有课的日子里不吸食大麻,变成了在有硬课的日子里不吸食大麻,变成了在有考试的日子里不吸食大麻,变成了在上午九点前不吸食大麻。
穆罕默德很聪明。那么,为什么他不能弄清楚,每次他吸烟时,他都不能坚持他自我设定的时间限制?
因为一旦他开始使用大麻,他就不受理性的支配;他被快乐-痛苦的平衡所支配。即使是一根大麻也会产生一种不容易受逻辑影响的欲望状态。在这种影响下,他不再能客观地评估吸烟的直接回报和长期回报。延迟贴现支配了他的世界。
在穆罕默德的情况下,时间上的自我约束只能到此为止,而适量的大麻不太可能成为一种选择。他必须,而且最终也找到了另一种方法。
分类的自我约束
雅各布在复发一周后再次来找我。他整个星期都没有使用。他把他的机器放在一个垃圾桶里,他知道当天就会被运走。他也把他的笔记本电脑和平板电脑放好。他多年来第一次去教堂,为他的家人祈祷。
“不考虑自己和自己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改变。我也不再羞辱自己。我的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但我可以做一些事情。”
他停顿了一下。“但我感觉不好,“他说。“我在星期一见到你,到了星期五我就想到要自杀,但我知道我不会这么做。”
我说:“这是使用后的一种消退,“我说。“让你的感觉像波浪一样涌上心头。要有耐心,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感觉更好。
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雅各布不仅通过限制接触色情制品、聊天室和TENS装置,而且还通过限制 “任何形式的欲望 “来保持禁欲。
他不再看电视、电影、YouTube、女子排球比赛–几乎所有给他带来性挑逗形象的东西。他跳过了某些类型的新闻文章;例如,关于据称与唐纳德-特朗普有染的脱衣舞女郎斯托米-丹尼尔斯的文章。早上在镜子前刮胡子之前,他先把短裤穿上。看到自己的裸体本身就是一个触发点。
“我用自己的身体玩了很长时间。我不能再那样做了,“他说。“我必须避免任何可能娱乐我的成瘾心理的事情。”
-
分类自我约束通过将多巴胺分为不同的类别来限制消费:那些我们允许自己消费的亚型,以及那些我们不允许消费的亚型。
这种方法不仅可以帮助我们避免所选择的药物,还可以避免导致对药物渴望的触发因素。这种策略对我们不能完全消除但我们试图以更健康的方式消费的物质特别有用,如食物、性和智能手机。
我的病人米奇沉迷于体育博彩。在他四十岁时,他已经输掉了一百万美元的赌博。参加匿名赌徒协会是他康复的一个重要部分。通过参与匿名赌徒协会,他了解到他要避免的不仅仅是体育博彩。他还必须避免观看电视体育节目,阅读报纸上的体育版,浏览与体育有关的互联网网站,以及收听体育广播。他给他所在地区的所有赌场打电话,把自己列入 “禁止进入 “名单。通过避免使用他所选择的毒品以外的物质和行为,米奇能够使用分类约束来减少复发体育博彩的风险。
不得不禁止自己的行为,有种悲壮感人的感觉。
至于雅各布,隐藏赤裸的身体,他的和其他人的,是他康复的一个重要部分。隐藏身体作为一种方式,以尽量减少参与被禁止的性行为的风险,长期以来一直是许多文化传统的一部分,一直延续到今天。古兰经》中提到了女性的矜持。“你要告诉信道的,妇女要垂下眼帘,守住她们的私处,不要暴露她们的装饰品……要把头巾的一部分包在胸前,不要暴露她们的装饰品。”
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LDS Church)已经就其成员的适度着装发表了官方声明,例如不鼓励"短裤和短裙,不遮盖腹部的衬衫,以及不遮盖肩膀或前面或后面低胸的衣服”。
-
当我们无意中把一个触发器纳入我们可接受的活动清单时,分类的自我约束就会失效。我们可以通过基于经验的心理筛选过程来纠正这样的错误。但是,当类别本身发生变化时,怎么办?
美国老生常谈的饮食传统–素食主义者、素食主义者、生食主义者、无麸质食品、阿特金斯、Zone、生酮症、旧石器时代、葡萄柚–是分类自我约束的一个例子。我们追求这些饮食的原因多种多样:医疗、道德、宗教。但不管是什么原因,最终的效果是减少对大型食物类别的接触,这反过来又限制了消费。
但是,当类别因市场力量而随时间变化时,饮食作为一种分类的自我约束形式,,受到威胁。
超过15%的北美家庭使用无麸质产品。有些人无麸质食品是因为他们患有乳糜泻,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摄入麸质会导致小肠受损。但越来越多的人不含麸质,因为这有助于他们限制高热量、低营养的碳水化合物的消费。问题是什么?
从2008年到2010年,美国推出了约3000种新的无麸质零食产品,而烘焙产品是目前无麸质市场中收入最高的单一包装商品类别。2020年,仅在美国,无麸质产品的价值估计为103亿美元。
无麸质饮食以前有效地限制了高热量加工食品的消费,如蛋糕、饼干、饼干、麦片、意大利面和披萨,现在不再如此。对于那些使用无麸质饮食来避免麸质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个好消息。但是对于那些从无麸质饮食中受益的人来说,作为一个限制面包、蛋糕和饼干消费的类别,这个类别不再起作用。
无麸质饮食的演变说明了控制消费的企图是如何被现代市场力量迅速反击的,这只是我们的多巴胺经济中固有的挑战的又一个例子。
还有许多其他现代例子,以前禁忌的毒品被转化为社会可接受的商品,往往以药品的名义。香烟变成了vapepens和ZYN pouches。海洛因变成了奥施康定。大麻变成了 “医用大麻”。我们刚刚承诺戒烟,我们的旧毒品就以包装精美、价格合理的新产品的形式重新出现,说:"嘿!这没关系。我现在对你有好处。
-
将被妖魔化的人神化是另一种形式的分类自我约束。
自史前时代以来,人类已将改变心智的药物提升为神圣的类别,在宗教仪式、成年仪式上使用,或作为药物。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牧师、巫师或其他接受过特殊培训或被赋予特殊权力的指定人员才被允许使用这些药物。
7000多年来,致幻剂,也被称为迷幻剂(魔幻蘑菇、死藤水、佩奥特),在不同的文化中具有神圣的用途。然而,当致幻剂在20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中作为娱乐性药物变得流行和广泛可用时,危害成倍增加,导致LSD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被定为非法。
今天,有一场运动让致幻剂和其他迷幻剂重新投入使用,但只是在迷幻剂辅助心理治疗的伪神圣背景下。经过专门培训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现在正在施用致幻剂和其他强效精神药物(迷幻剂、氯胺酮、摇头丸)作为心理健康的补救措施。施加有限剂量(1到3种)的迷幻剂,并在数周内穿插进行多次谈话治疗,已经成为现代萨满教的等同物。
希望通过限制获得这些药物的机会,并让精神病医生把关,这些化学品的神秘特性–一体感、超越时间、积极的情绪和崇敬–可以得到利用,而不会导致滥用、过度使用和成瘾。
-
有些人既不需要萨满也不需要精神病学家来给他们选择的药物注入神圣的力量。在现在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棉花糖实验中,至少有一个孩子在实验中完全靠自己来管理神圣的东西。
斯坦福棉花糖实验是心理学家沃尔特-米歇尔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斯坦福大学领导的一系列研究,以研究延迟满足。
3至6岁的儿童可以选择立即提供一个小奖励(一个棉花糖)或两个小奖励(两个棉花糖),如果孩子能等待大约15分钟而不吃第一个棉花糖。
在这段时间里,研究人员离开房间,然后再回来。棉花糖被放在桌子上的一个盘子里,房间里没有其他干扰:没有玩具,没有其他孩子。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确定,儿童的延迟满足感何时发生。随后的研究考察了什么样的现实生活结果与延迟满足的能力,或缺乏这种能力有关。
研究人员发现,在大约一百名儿童中,有三分之一的儿童能够坚持到拿到第二块棉花糖。年龄是一个主要的决定因素:孩子越大,越能拖延。在后续研究中,能够等待第二颗棉花糖的儿童往往有更好的SAT分数和更好的教育程度,并且总体上是在认知和社会方面适应得更好的青少年。
实验的一个细节不太为人所知,那就是孩子们在挣扎着不吃第一个棉花糖的那十五分钟里做了什么。
研究人员的观察显示了自我束缚的字面体现。孩子们 “,用手遮住眼睛,或转过身去,使他们看不到托盘……开始踢桌子,或拽他们的小辫子,或抚摸棉花糖,好像它是一个小毛绒动物”。
遮住眼睛,转过身去,让人联想到身体上的自我束缚。拽着小辫子表明用身体上的疼痛来分散注意力……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详细谈及。但是抚摸棉花糖呢?这个孩子没有远离想要的东西,而是把它当作宠物,太珍贵了,不能吃,或者至少不能冲动地吃。
我的病人Jasmine因为过度饮酒,每天多达10瓶啤酒而来寻求帮助。作为治疗的一部分,我建议她把所有的酒精从家里拿走,作为一种自我约束的策略。她基本上接受了我的建议,但有一个转折。
她清除了所有的酒精,只有一种啤酒留在她的冰箱里。她称这是她的 “图腾啤酒”,她认为这是她选择不喝酒的象征,是她的意志和自主权的代表。她告诉自己,她只需要专注于不喝这一瓶啤酒,而不是从世界上大量的啤酒中不喝任何啤酒这一更艰巨的任务。
这种元认知的技巧,将诱惑的对象转化为克制的象征,有助于茉莉花的禁欲。
-
在他第二次尝试康复的半年后,我在等候室见到了雅各布。我已经有几个月没有见到他了。
我一看到他,就知道他干得不错。他的衣服很合身,拥抱他身体的方式。但这不仅仅是他的衣服。他的皮肤也适合他,当一个人感到与自己和世界相连时,他的皮肤也是如此。
不是说你会在任何精神病学教科书中找到这一点。这只是我看了几十年病人后注意到的事情。当人们病情好转时,一切都会保持一致,有一种正确性。那天,雅各布有一种正确的感觉。
“我的妻子回到了我的生活中,“我们一到我的办公室,他就说。“我们仍然分居,但我去西雅图看她,我们度过了两天美好的时光。我们要一起度过圣诞节。”
“我很高兴,雅各布。”
“我已经摆脱了我的执着。我没有被强迫以,以某种方式行事。我可以自由地再次决定我将做什么。我的病复发已经有将近六个月了。如果我继续做我正在做的事,我想我将会好起来。比没事更好。”
他看着我并微笑着。我也微笑着回应。
-
雅各布为避免任何可能激发性欲的东西所做的非凡努力,在我们现代人的感觉中似乎完全是中世纪的事,与一件毛衣仅一步之遥。
然而,他远没有感到被他的新生活方式所束缚,而是感到解放了。从强迫性过度消费的控制中解脱出来,他又能以快乐、好奇和自发的态度与其他人和世界互动。他感到有了某种尊严。
正如伊曼纽尔-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写道:“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有能力进行这种内在的立法时,(自然)人感到自己不得不,对自己身上的道德人产生敬意”。
捆绑自己是获得自由的一种方式。
第六章
破碎的平衡?
我希望,“克里斯说,他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调整他的背包,把掉进眼睛里的头发往后推,晃动他的膝盖(在随后的几年里,我知道他总是在运动),“你会继续给我服用丁丙诺啡。这很有帮助。事实上,这是一种轻描淡写的说法。我不确定没有它我还能不能活着,我需要找一个能给我开药的人。”
丁丙诺啡是一种半合成的阿片类药物,从罂粟中提炼出来的thebaine。与其他阿片类药物一样,丁丙诺啡与μ-阿片受体结合,可立即缓解疼痛和对阿片类药物的渴望。最简单的说法是,它的作用是将快乐-痛苦的平衡恢复到一个水平位置,以便像克里斯这样的人能够停止与渴望作斗争,重新开始生活。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丁丙诺啡可以减少非法阿片类药物的使用,降低过量的风险,并改善生活质量。
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丁丙诺啡是一种阿片类药物,可以被滥用、转用,并在街头出售。对于不依赖较强阿片类药物的人来说,丁丙诺啡可以产生一种兴奋的感觉。使用丁丙诺啡的人在停止或减少剂量时,会出现阿片类药物戒断和渴望。事实上,有一些病人告诉我,丁丙诺啡的戒断远比他们服用海洛因或奥施康定的情况要严重。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故事,“我对克里斯说,“然后我会让你知道我的想法。”
-
克里斯于2003年来到斯坦福大学。他的继父开着一辆借来的旧雪佛兰Suburban把他从阿肯色州送来。这辆越野车装满了克里斯的物品,在挤在学生宿舍门口的闪亮的新宝马和雷克萨斯中显得格外显眼。
克里斯没有浪费时间。他一丝不苟地整理他的宿舍,首先是他的CD收藏,他按字母顺序排列。他研究了课程目录,确定了创意写作、希腊哲学和德国文化中的神话与现代性。他梦想成为一名作曲家,一名电影导演,一名作家。他的计划,就像他的同学们一样,很宏伟。这将是他在斯坦福大学辉煌的开始。
一旦开始上课,克里斯在所有预期的方面表现良好。他努力学习。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在另一个层面上,他并没有茁壮成长。他独自上课,独自在房间或图书馆学习,独自在宿舍的公共休息室()里弹钢琴。他最喜欢的校园流行语–社区,让他无所适从。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回顾我们早期的大学生活时,都会记得为找到自己的人而挣扎。克里斯挣扎得更厉害。即使是现在,也很难说出确切的原因。他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富有思想。和蔼可亲。急于取悦。也许这与他是那个来自阿肯色州的穷小子有关。
他孤独的校园生活一直持续到大二,直到他在校园兼职工作中遇到一个女孩。他那棱角分明的五官、柔软的棕色头发,以及粗壮的肌肉构造一直吸引着人们的注意。他和那个女孩,一个本科生同学,接吻了,克里斯一下子就爱上了。当她告诉他她有一个男朋友时,他决定这并不重要。他想和她在一起,并反复寻找她。当他没有放弃时,她指责他跟踪她,并向他们共同的老板举报他。结果,他失去了工作,并被学校管理层训斥。没有工作和女朋友,他决定只有一个解决办法。他要自杀。
克里斯给他母亲写了一封临别邮件。“妈,我穿了干净的内裤。“他借了一把刀,带着他的CD机和一张精心挑选的CD,来到了罗布泊球场。当时正值黄昏,他的计划是吞下一瓶药片,割开手腕,在夕阳西下的时候死去。
音乐对克里斯很重要,他精心选择了他的最后一首歌。纽约独立后朋克复兴乐队Interpol的 “PDA”。“PDA “的节奏感很强,令人振奋。歌词是,很难说清楚。最后一节是这样的"今晚睡觉,今晚睡觉,今晚睡觉,今晚睡觉。有话可说,有事可做,无话可说,无事可做”。克里斯一直等到这首歌的最后,然后把刀的锋利边缘拉过两个手腕。
试图在一片空地上割腕自杀,结果发现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策略。半小时后,他手腕上的血已经凝固了,他坐在黑暗中,看着人们走过。他回到寝室,让自己把药丸吐出来,然后打了911。救护人员来了,把他带到斯坦福医院,在那里他被送进了精神病院。
他的继父是第一个来探望他的人。他的母亲也计划前来,但却无法登机。她对飞行有一种长期的恐惧。他的生父也出现了,他每年只见过他几次。当他的父亲看到克里斯托弗手腕上红色的、凸起的切口时,显得很震惊。
克里斯在精神病院总共呆了两个星期。在那段时间里,他主要是觉得在一个受控的、可预测的环境中得到了解脱。
斯坦福大学的一名代表来到单位看望他,并通知他,在这种情况下,他将被迫从斯坦福大学请病假,直到他康复到能够返回,由学校决定和决定。
克里斯回到阿肯色州,与他的母亲和继父一起生活。他找了一份服务台的工作。他发现了毒品。
2007年秋天,克里斯回到了斯坦福大学。在,他需要与学生心理健康负责人和他的驻校院长见面,向他们汇报他的最新进展,并提出令人信服的重新入学的理由。
在见面的前一天,他和一个在斯坦福大学认识的女孩住在一起。他和她并不熟,但她 “也有问题”,所以克里斯感觉更舒服,问他是否可以在她那里住上一两个晚上,同时让自己与大学的关系得到解决。
面试前一天晚上,克里斯熬夜 “吸食可卡因 “并阅读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到了早上,他得出结论,他太混乱了,无法与一群大学管理人员见面。他当天就飞回了家。
接下来的一年,克里斯在100多度的天气里为阿肯色大学铲土、铺设地膜、修剪草坪。他喜欢这种体力劳动,喜欢移动身体的方式来分散他的注意力。他被提拔为树艺师,主要工作是把树干和树枝塞进碎木机。
当他不工作的时候,他就在作曲,谱子一个接一个,同时吸食大麻,这对他来说已经是不可或缺的了。
第二年秋天,克里斯再次回到斯坦福。这一次不需要亲自见面。克里斯像杰克-里奇那样出现在他的宿舍里,除了口袋里的牙刷和手里的笔记本电脑,什么都没有。他穿着自己的衣服睡在床垫上,没有床单。
他让自己变得有条不紊,他认识到这是他成功所需要的。作为他新的心态的一部分,他改变了他的专业。他现在将学习化学。
他还发誓要戒掉大麻,但他的决心只持续了三天,就又开始每天吸烟,躲在房间里,试图在他的室友(他只记得是 “某个印度人”)不在的时候抽。
在期中考试的时候,克里斯推断,既然他大部分的学习时间都花在嗨上了,那么他的期中考试也应该很嗨。他在心理学课上读到了关于 “状态依赖学习 “的内容。他做了第二个问题,然后意识到他不知道这些材料,无法完成考试。他站起来走了出去,顺手把他的试卷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他就坐上了回家的飞机。
第三次离开斯坦福的感觉对克里斯来说有所不同。它带有无望的色彩。当他回到家时,他完全没有雄心壮志,甚至没有继续作曲的想法。他开始大量饮酒,此外还吸食大麻。然后他第一次尝试阿片类药物,这在2009年的阿肯色州很容易做到,当时阿片类药物制造商和经销商正在向该州注入数百万的阿片类止痛药。同年,,阿肯色州的医生为每100个生活在阿肯色州的人开了116张阿片类药物处方。
在服用阿片类药物时,克里斯认为他一直在寻找的一切似乎突然就在眼前。是的,他感到兴奋,但这并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是他感觉到了联系。
他开始给亲戚和其他他认识的人打电话,交谈,分享,倾诉。只要他还在吸毒,这种联系就显得很真实,但阿片类药物一过就消失了。他了解到,毒品制造的亲密关系并不持久。
间歇性使用阿片类药物的模式跟随克里斯进入了他在斯坦福大学的下一次入学尝试。当他在2009年秋天回来时,现在是他的第四次尝试,他在时间上和地理上都被他的本科生同龄人边缘化。他比一般的大二学生大五岁。
他被安排在研究生宿舍,与一名粒子物理学的研究生共用一套两居室的公寓。他们没有什么共同点,并努力不影响彼此的工作。
他养成了围绕学习和使用毒品的习惯。他已经放弃了尝试戒毒的想法。他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公认的 “吸毒者”。
他每天都在自己的卧室里独自吸食大麻。每个星期五晚上,他都会独自到旧金山去买海洛因。在街上打一针花了他15美元,持续5到15秒的兴奋,以及持续数小时的余韵。他抽了更多的大麻来缓解下坠感。第一季度的中期,他卖掉了他的笔记本电脑,以购买更多的海洛因。然后他卖掉了自己的外套。他记得当他在城市的街道上徘徊时很冷。
他曾经试图与他的语言课上的两个英国学生交朋友。他告诉他们,他想拍一部电影,里面有他们。他开始对摄影感兴趣,有时在校园里闲逛拍照。他们最初似乎被吸引住了,但当他告诉他的电影想法–拍摄他们在吃饭时用美国口音说话–他们不同意,此后就躲着他。
“我想我一直是这样的怪人。奇怪的想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来不想告诉别人我在想什么。”
在这一切中,克里斯去上课,除了在《异常行为的人际关系基础》中得到一个B以外,其余都是A。他在圣诞节时回家了,没有再回来。
2010年秋天,克里斯做了最后一次半心半意的尝试,想进入斯坦福大学学习。他在门洛帕克的校外租了一个房间,并宣布了另一个新专业:人类生物学。几天后,他从房东太太那里偷来了止痛药,并得到了安眠药的处方,他将其碾碎并注射了进去。他度过了五个痛苦的月份,然后离开了斯坦福大学,这次他不希望再回来。
在阿肯色州的家中,克里斯整天都在吸毒。他每天早上都会吸食毒品,几个小时后毒品消失,他就会躺在父母家的床上,希望时间能够过去。这个循环似乎没有尽头,无法逃避。
2011年春天,克里斯在醉酒的情况下偷吃冰激凌,被警察抓住。他被提供给监狱或康复中心。他选择了戒毒所。2011年4月1日,在康复中心,克里斯开始服用一种叫做丁丙诺啡的药物,商品名为Suboxone。克里斯认为丁丙诺啡拯救了他的生命。
在服用丁丙诺啡两年后,克里斯决定做最后一次尝试,回到斯坦福。2013年,他从一个中国老人那里租了一张拖车屋的床。他买不起其他东西。在他来到校园的第一个月,他来找我寻求帮助。
-
当然,我同意为克里斯开丁丙诺啡。
三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继续获得博士学位。事实证明,他的 “怪异 “想法很适合在实验室中使用。
2017年,他与女友结婚。她知道他的过去,理解他为什么要服用丁丙诺啡。她有时会感叹他的 “机器人式的缺乏情感”,特别是在她觉得应该生气的时候,他明显缺乏愤怒。
但基本上,生活是美好的。克里斯不再被渴望、愤怒和其他不可容忍的情绪所淹没。他每天都在实验室里工作,下班后赶回家去看他的妻子。他们很快就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
2019年的一天,在我们的一次月度会议上,我对克里斯说:“你做得很好,而且已经做了这么久,你有没有想过尝试摆脱丁丙诺啡?”
他的答案是确定的。“我永远不想离开丁丙诺啡。它对我来说就像一个电灯开关。它不只是阻止我吸食海洛因。它给了我的身体一些我需要的东西,而且在其他地方找不到。”
用药物来恢复水平平衡?
我经常想到克里斯那天说的话,关于丁丙诺啡给了他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东西。
长期使用毒品是否打破了他的快乐-痛苦平衡,以至于他在余生都需要阿片类药物来感受 “正常”?也许有些人的大脑失去了恢复平衡所需的可塑性,即使在长期戒断之后。也许即使在小精灵下马后,他们的天平仍然永久地偏向于疼痛的一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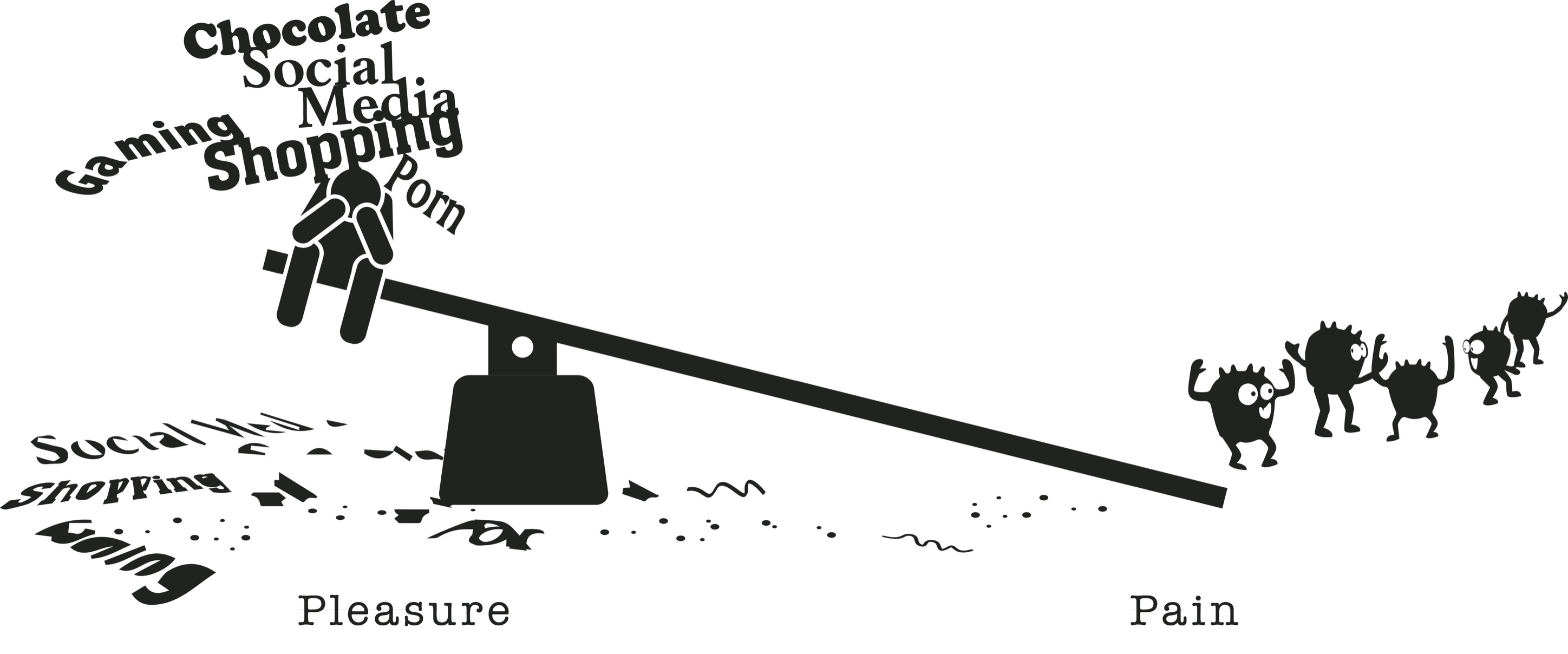
还是克里斯说阿片类药物纠正了他天生的化学失衡?
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读医学院和住院医师时,我被告知,患有抑郁症、焦虑症、注意力缺失、认知扭曲、睡眠问题等的人,他们的大脑没有按照他们应有的方式工作,就像糖尿病患者的胰腺没有分泌足够的胰岛素。根据该理论,我的工作是取代缺失的化学物质,使人们能够 “正常 “工作。这种信息被制药业广泛传播和积极推广,并在医生和病人消费者中找到了可以接受的受众。
或者,也许克里斯说的仍然是不同的东西。也许他是在说丁丙诺啡弥补了不是在他的大脑,而是在这个世界的不足。也许世界让克里斯失望了,而丁丙诺啡是他能看到的最好的适应方式。
无论问题是在克里斯的大脑中还是在这个世界上,无论问题是由长期使用药物造成的还是他天生就有的问题,这里有一些我在使用药物压制快乐方面的担心。
首先,任何压在快乐方面的药物都有可能让人上瘾。
迷上处方兴奋剂的大学生大卫是活生生的证据,他从医生那里获得兴奋剂,用于诊断医疗状况,并不意味着对依赖和成瘾的问题有免疫力。处方兴奋剂的分子相当于街头的甲基苯丙胺(冰毒、速效药、曲奇、克里斯蒂娜、无瞌睡、史酷比)。它们导致大脑奖励途径中的多巴胺激增,并且 “具有很高的滥用潜力”,这是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对Adderall的警告中的直接引用。
第二,如果这些药物实际上并不像它们应该的那样起作用,或者更糟糕的是,从长远来看会使精神症状恶化,那怎么办?尽管丁丙诺啡对克里斯有效,但,更普遍的精神药物的证据并不健全,尤其是长期服用时。
尽管四个高资源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对抗抑郁药(百忧解)、抗焦虑药(Xanax)和催眠药(Ambien)等精神病药物的资助大幅增加,但这些国家的情绪和焦虑症状的流行率并没有下降(1990至2015年)。在控制精神疾病风险因素(如贫困和创伤)的增加时,甚至在研究严重精神疾病(如精神分裂症)时,这些发现仍然存在。
焦虑和失眠患者如果每天服用苯二氮卓类药物(Xanax和Klonopin)和其他镇静催眠剂超过一个月,可能会出现焦虑和失眠恶化的情况。
每天服用阿片类药物超过一个月的疼痛患者,不仅有阿片类药物成瘾的风险,也有疼痛恶化的风险。如前所述,这是,称为阿片类药物引起的痛觉亢进,即阿片类药物在重复服用时使疼痛加剧。
像Adderall和Ritalin这样治疗注意力缺陷障碍的药物可以促进短期记忆和注意力,但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可以增强长期复杂的认知能力,提高学术水平,或提高成绩。
正如公共卫生心理学家格雷琴-勒弗-沃森和她的合著者在*《美国大学校园的多动症药物滥用危机*》中写道:“令人信服的新证据表明,,多动症药物治疗与学术和社会情感功能的恶化有关。”
最近的数据显示,即使是以前被认为不会 “形成习惯 “的抗抑郁药,也可能导致耐受性和依赖性,甚至可能使抑郁症长期恶化,这种现象被称为迟发性精神障碍症。
除了成瘾问题和这些药物是否有帮助的问题,我一直被一个更深的问题所困扰。如果服用精神药物使我们失去了人性的某些基本方面,那该怎么办?
1993年,精神病学家彼得-克莱默(Peter Kramer)博士出版了他的开创性著作《倾听百忧解》(Listening to Prozac),他在书中认为,抗抑郁药让人 “好上加好”。但是,如果克莱默搞错了呢?如果精神药物不是让我们比健康更好,而是让我们比健康更差呢?
多年来,我有许多病人告诉我,他们的精神药物虽然能在短期内缓解痛苦的情绪,但也限制了他们体验全部情绪的能力,特别是像悲伤和敬畏这样的强大情绪。
一位服用抗抑郁药似乎效果不错的病人告诉我,她不再为奥运会的广告而哭泣。当她谈到这一点时,她笑了,她高兴地放弃了她性格中多愁善感的一面,以缓解抑郁症和焦虑症。但是,当她在自己母亲的葬礼上都不能哭的时候,她的天平已经倾斜了。她停用了抗抑郁药,不久后经历了更广泛的情绪波动,包括更多的抑郁和焦虑。她决定为了感觉到自己是人,这些低谷是值得的。
我的另一个病人已经从大剂量的奥施康定(OxyContin)中减量,她已经为慢性疼痛服用了十多年,几个月后她和她丈夫一起回来看我。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么多年来,他已经厌倦了这么多的医生。“他说:“我的妻子在服用羟考酮后,不再听音乐。现在她不再听那些东西了,又喜欢上了音乐。对我来说,这感觉就像我找回了我结婚时的自己。”
我对精神药物治疗有自己的经验。
我从小就烦躁不安,对我的母亲来说,我是一个难以抚养的孩子。她努力帮助我控制我的,在这个过程中,她对自己作为父母感到很难过,或者至少这是我对过去的解释。她承认她更喜欢我的弟弟,他温顺、好说话。我也喜欢他,当我母亲沮丧地举手时,他有效地抚养了我。
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我开始服用百忧解,因为长期的低度烦躁和焦虑被诊断为 “非典型抑郁症”。我马上就感觉好了。最主要的是,我不再问那些大问题。*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有自由意志吗?我们为什么受苦?有上帝吗?*相反,我只是继续问。
另外,在我的生活中,我和我的母亲第一次相处得很好。她发现我很讨人喜欢,而我也喜欢更讨人喜欢。我更适合她。
几年后,当我因为想要怀孕而停止服用百忧解时,我又恢复了以前的样子:暴躁、质疑、不安。几乎就在同时,我和母亲又开始闹矛盾了。当我们两个人都在房间里时,房间里的空气似乎都在颤抖。
几十年后,我们的关系稍有好转。我们在互动最少的时候做得最好。这让我很难过,因为我爱我的妈妈,我知道她爱我。
但我并不后悔离开百忧解。我不服用百忧解的个性,虽然不适合我的母亲,但却让我能够做一些我本来不会做的事情。
今天,我终于可以接受自己是一个有点焦虑、有点抑郁的怀疑论者。我是一个需要摩擦的人,需要挑战,需要为之努力或抗争的东西。我不会为了适应这个世界而把自己缩小。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应该这样吗?
在通过药物治疗来适应这个世界的过程中,我们正在解决什么样的?在治疗疼痛和精神疾病的幌子下,我们是否正在使大部分人口在生物化学上对无法忍受的环境漠不关心?更糟的是,精神药物已经成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特别是对穷人、失业者和被剥夺权利者的控制?
穷人,特别是贫穷的儿童,更经常地被开具精神药物,而且用量更大。
根据CDC国家健康统计中心的全国健康访谈调查的2011年数据,,7.5%的6至17岁的美国儿童因 “情绪和行为困难 “而服用处方药。贫困儿童比非贫困儿童更有可能服用精神病药物(9.2%对6.6%)。男孩比女孩更有可能接受药物治疗。非西班牙裔的白人比有色人种更有可能接受药物治疗。
根据佐治亚州医疗补助数据对全国其他地区的推断,,可能有多达一万名幼儿正在接受像利他林这样的精神刺激剂药物。
正如精神病学家埃德-莱文(Ed Levin)就美国青年,特别是穷人的过度诊断和过度用药问题写道:“虽然像所有的行为一样,愤怒的倾向必须涉及一些生物学问题,但它可能更显著地反映出病人对不利和不人道的待遇的反应。”
这种现象并不限于美国。
瑞典的一项全国性研究分析了不同精神病药物的处方率,其依据是他们所谓的 “邻里贫困 “指数(教育、收入、失业和福利援助指数)。对于每一类精神病药物,他们发现随着社区社会经济地位的下降,精神病药物的处方率也在增加。他们的结论是。“这些发现表明,社区的贫困与精神病药物处方有关。”
阿片类药物也被不成比例地开给穷人。
根据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的说法,“贫困、失业率和就业人口比例与处方阿片类药物的流行和物质使用措施高度相关。平均而言,,经济前景较差的县更有可能有较高的阿片类药物处方率、阿片类药物相关的住院率和药物过量死亡率。”
享受医疗补助的美国人,即联邦资助的最贫穷和最脆弱人群的健康保险,被开具阿片类止痛药的比例是非医疗补助患者的两倍。医疗补助患者死于阿片类药物的比例是非医疗补助患者的三到六倍。
即使像丁丙诺啡维持治疗(BMT)这样的药物,也就是我给克里斯开的治疗阿片类药物成瘾的处方,当健康的社会心理决定因素没有得到同样的解决时,也可能构成一种 “临床放弃”。正如亚历山大-海切尔(Alexandrea Hatcher)和她的同事在《物质使用和滥用》杂志上写道。“如果不关注没有种族和阶级特权的病人的基本需求,BMT作为单独的药物治疗,而不是解放性的,可能会变成一种制度性的忽视,甚至结构性的暴力,以至于被认为足以让他们康复”。
-
由乔斯-韦登(Joss Whedon)执导的科幻电影《宁静》(Serenity)(2005年)想象了一个未来的世界,其中国家领导人进行了一项伟大的实验。他们给整个星球上的人接种疫苗,让他们远离贪婪、悲伤、焦虑、愤怒和绝望,希望能实现和平与和谐的文明。
马尔,一个流氓飞行员,电影的主人公,宁静号飞船的船长,与他的船员一起到这个星球去探索。他没有找到香格里拉,而是找到了没有现成解释的尸体。整个星球上的人都死于非命,他们躺在床上,踢在沙发上,斜躺在办公桌前。马尔和他的队员们最终解开了这个谜。基因突变使他们失去了对任何事物的饥饿感。
就像现实生活中的多巴胺耗尽的老鼠一样,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意为食物洗牌几厘米,这些人因缺乏欲望而死亡。
-
请不要误解我的意思。这些药物可以成为拯救生命的工具,我很感激在临床实践中拥有它们。但是,用药物消除人类的每一种痛苦都是有代价的,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有一条替代的道路可能效果更好:拥抱疼痛。
第三部分
对疼痛的追求
第七章
按压疼痛面
迈克尔坐在我对面,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看起来很轻松。男孩般的英俊和毫不费力的魅力,他的自然魅力既是他的天赋也是他的负担。
“我是一个关注的妓女,“他说。“我的任何一个朋友都会告诉你。”
迈克尔的生活曾经是一个硅谷的童话故事。大学毕业后,他在房地产行业赚了数百万。到35岁时,他已经富可敌国,英俊得令人羡慕,并与他所爱的女人幸福地结婚。
但他有另一种生活,很快就会解开他所努力的一切。
“我一直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寻找任何能给我带来动力的东西。可卡因是显而易见的,但酒精对我来说也是如此……从我第一次尝试时,就给我带来了兴奋和大量的能量。我告诉自己,我将成为一个可以娱乐性地吸食可卡因而不会陷入困境的人,。当时,我真的相信这一点。“他停顿了一下,笑了笑。“我应该知道。
“当我的妻子告诉我,解决我的毒瘾将是拯救我们婚姻的唯一途径时,我甚至没有犹豫。我想要她。我想要这段婚姻。恢复是唯一的选择。”
对迈克尔来说,辞职并不是最困难的部分。难的是弄清楚下一步该怎么做。戒烟后,他被他一直用毒品掩盖的所有负面情绪所淹没。当他不感到悲伤、愤怒和羞愧时,他根本就没有感觉,这可能更糟糕。然后他偶然发现了一些东西,给了他希望。
“第一次发生的时候,“他告诉我,“那是一个意外。我早上起来上网球课……在不吸毒的早期,这是一种分散自己注意力的方式。但在打完网球和淋浴后的一个小时,我仍然在流汗。我向我的网球教练提及此事,他建议我尝试用冷水澡代替。冷水浴有点疼,但只洗了几秒钟,直到我的身体适应了它。当我出来时,我感觉出奇的好,就像我喝了一杯非常好的咖啡。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开始注意到,洗完冷水澡后我的情绪会好一些。我在网上研究了冷水疗法,发现了一个洗冰水澡的社区。这似乎有点疯狂,但我很绝望。按照他们的思路,我从冷水浴发展到在浴缸里装满冷水,把自己浸泡在里面。这样做效果更好,所以我加大了力度,在浴缸的水中加入冰块,,使温度更低。通过这样做,我可以把温度调到50度左右。
“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每天早上把自己浸泡在冰水中5到10分钟,睡觉前再浸泡一次。在接下来的三年里,我每天都这样做。这是我康复的关键。”
“那是什么感觉?“我问,“把自己浸泡在冷水里?“我自己对冷水有厌恶感,甚至几秒钟都无法忍受那些温度。
“在最初的五到十秒钟里,我的身体在尖叫。停下来,你会杀了自己。它是那么的痛苦。”
“我可以想象。”
“但我告诉自己,这是有时间限制的,是值得的。在最初的冲击之后,我的皮肤就麻木了。刚出来后,我就觉得很兴奋。这完全像一种毒品……就像我记忆中的摇头丸或娱乐性的维柯丁一样。令人难以置信。我感觉好几个小时都很好。”
-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都在冷水中洗澡。只有那些住在天然温泉附近的人可以定期享受热水澡。难怪那时的人们会呆在更脏的地方。
古希腊人开发了公共浴池的加热系统,但继续提倡使用冷水来治疗各种疾病。在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文森茨-普里斯尼茨的德国农民提倡使用冰水来治疗各种生理和心理疾病。他甚至把自己的家变成了一个冰水治疗的疗养院。
自从现代管道和暖气的出现,热水浴和淋浴已经成为常态;但冰水浸泡最近又开始流行起来。
耐力运动员声称它能加速肌肉恢复。苏格兰式淋浴 “也被称为 “詹姆斯-邦德式淋浴”,是伊恩-弗莱明的007小说中的詹姆斯-邦德所采用的,是新近流行的,包括以至少一分钟的冷水淋浴结束热水淋浴。
像荷兰人维姆-霍夫(Wim Hof)这样的冰水浸泡大师已经成为他们自己的名人,因为他们能够在接近冰点的温度下一次浸泡数小时。
布拉格查尔斯大学的科学家在《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上撰文,进行了一项实验,十名男子自愿将自己(头朝外)浸入冷水(14摄氏度)一小时。这是华氏57度。
研究人员使用血液样本显示,由于冷水浸泡,血浆(血液)中的多巴胺浓度增加了250%,血浆中的去甲肾上腺素浓度增加了530%。
多巴胺在冷浴过程中逐渐稳定地上升,并在之后的一个小时内保持上升。去甲肾上腺素在前30分钟内急剧上升,在后30分钟内趋于平稳,并在之后的一小时内下降了大约三分之一,但它仍然比基线高得多,,甚至在浴后第二小时内也是如此。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的水平远远超出了痛苦刺激本身,这就解释了迈克尔的说法:“我一出来……就感觉好几个小时。我感觉好几个小时都很好”。
其他研究考察了人类和动物的冷水浸泡对大脑的影响,显示单胺类神经递质(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5-羟色胺)有类似的升高,这些神经递质也是调节快乐、动机、情绪、食欲、睡眠和警觉性的。
除了神经递质之外,动物的极度寒冷已被证明可以促进神经元的生长,这一点更加引人注目,因为已知神经元仅在少数情况下会改变其微观结构。
Christina G. von der Ohe和她的同事研究了冬眠的地松鼠的大脑。在冬眠期间,核心温度和大脑温度都下降到0.5-3摄氏度以内。在冰点温度下,冬眠地松鼠的神经元看起来就象是没有多少枝条(树突)和更少叶子(微树突)的骨干树。
然而,当冬眠的地鼠得到温暖时,神经元显示出显著的再生能力,就像春暖花开时的落叶林。这种重新生长发生得很快,可与只有在胚胎发育中才能看到的那种神经元可塑性相媲美。
该研究的作者在谈到他们的发现时写道。“我们在冬眠者大脑中展示的结构变化是自然界中发现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在恒河猴胚胎的海马体中,树突伸长可以达到每天114微米,而成年冬眠者仅在2小时内就表现出类似的变化。”
-
迈克尔意外地发现了冰水浸泡的好处,这是一个例子,说明在平衡的痛苦方面施加压力可以导致其相反的快乐。与按下快乐的一面不同,来自疼痛的多巴胺是间接的,而且可能更持久。那么,它是如何工作的呢?
疼痛通过触发身体自身的调节平衡机制而导致快乐。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的疼痛刺激之后,小精灵们就会在平衡的快乐方面跳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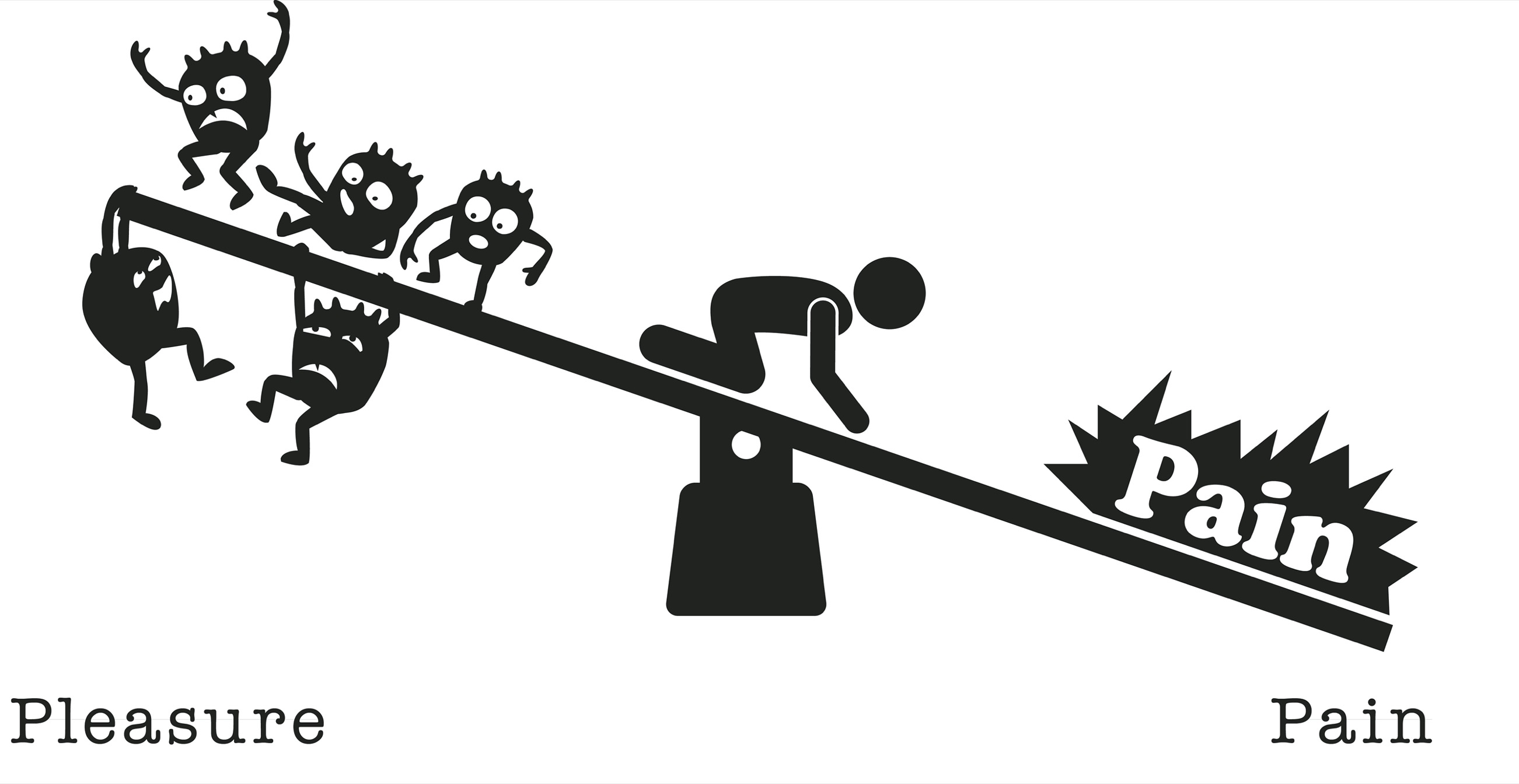
我们感受到的快乐是我们身体对痛苦的自然和反射性的生理反应。马丁-路德通过禁食和自我鞭笞来扼杀肉体,可能让他有点兴奋,即使是出于宗教原因。
随着间歇性地暴露在痛苦中,我们的自然享乐设定点会被加权到快乐一边,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变得不那么容易受到痛苦的影响,更能够感受到快乐。

20世纪60年代末,科学家在狗身上进行了,由于实验明显的残酷性,这些实验在今天是不被允许的,但还是提供了关于大脑平衡(或平衡)的重要信息。
在将狗的后爪与电流连接后,研究人员观察到。“在最初的几次电击中,这只狗显得很惊恐。它尖叫并乱动,瞳孔放大,眼睛凸起,毛发竖起,耳朵向后,尾巴蜷缩在两腿之间。出现了排便和排尿,以及许多其他强烈的自主神经系统活动的症状”。
第一次电击后,当狗被从束缚中解脱出来时,“它在房间里慢慢地移动,显得很隐蔽、犹豫不决,而且不友好”。在第一次电击中,狗的心率增加到每分钟150次,超过了静止的基线。当电击结束后,该狗的心率减缓到比基线低30次,持续了整整一分钟。
在随后的电击中,“它的行为逐渐改变。在电击过程中,恐怖的迹象消失了。相反,这只狗显得很痛苦、恼火或焦虑,但并不害怕。例如,它抱怨而不是尖叫,也没有表现出进一步的排尿、排便或挣扎。然后,当训练结束时突然被释放时,这只狗冲过来,跳到人身上,摇晃着尾巴,我们当时称之为’快乐的表现'。”
在随后的电击中,狗的心率只略微高于静止基线,而且只上升了几秒钟。电击结束后,心率大幅放缓,低于静止基线每分钟60次,是第一次的两倍。整整5分钟后,心率才恢复到静止基线。
随着反复接触痛苦的刺激,狗的情绪和心率也随之适应。最初的反应(疼痛)变得更短、更弱。之后的反应(快乐)变得更长更强。疼痛演变成高度警觉,演变成 “快乐”。与 “不战而屈人之兵 “的反应相一致的心率升高,演变成最小的心脏,然后是长时间的心动过缓,这是一种在深度放松状态下看到的心率减慢。
阅读这个实验,不可能不对遭受这种折磨的动物感到怜悯。然而,所谓的 “快乐的适应 “表明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通过压制平衡中的痛苦一方,我们是否可以获得更持久的快乐来源?
这个想法并不新鲜。古代哲学家们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苏格拉底(柏拉图在《苏格拉底不惧怕死亡的理由》中记载)在两千多年前就思考过痛苦和快乐之间的关系。
,这个被人们称为快乐的东西会显得多么奇怪!它与被认为是它的反面的东西–痛苦–的关系是多么奇怪啊!这两者在一个人身上永远不会被发现,但如果你寻求一个并得到它,你几乎一定会得到另一个。这两种东西在一个人身上永远不会被发现,但如果你寻求其中一种并得到它,你几乎必然也会得到另一种,就像它们都附在同一个头上一样。无论在哪里找到一个人,另一个人都会跟在后面。因此,在我的例子中,由于我的腿因脚镣而疼痛,快乐似乎也随之而来了。
美国心脏病专家海伦-陶西格(Helen Taussig)于1969年在《*美国科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描述了被雷电击中的人活到现在的经历。“我邻居的儿子,在他从高尔夫球场回来时被雷电击中。他被甩到了地上。他的短裤被撕成碎片,他的大腿被烧伤。当他的同伴让他坐起来时,他尖叫着说’我,我死了'。他的双腿麻木、发青,无法动弹。当他到达最近的医院时,他已经很兴奋了。他的脉搏非常缓慢”。这段叙述回顾了这只狗的 “喜悦之情”,包括脉搏变慢的情况。
我们都经历过某种形式的痛苦让位给快乐。也许像苏格拉底一样,你注意到在生病一段时间后情绪得到了改善,或者在运动后感觉到跑步的兴奋,或者在一部恐怖电影中获得了莫名其妙的快乐。就像痛苦是我们为快乐付出的代价一样,快乐也是我们对痛苦的回报。
荷尔蒙的科学
摩尔蒙斯是科学的一个分支,研究给予小到中等剂量的有毒和/或痛苦刺激的有益影响,如冷、热、重力变化、辐射、食物限制和运动。摩尔蒙斯来自古希腊语的荷尔蒙(hormáein):使其运动,推动,敦促。
美国毒理学家、激素作用领域的领导者爱德华-J-卡拉布雷斯将这种现象描述为 “生物系统对适度的环境或自我施加的挑战的适应性反应,通过这种反应,系统提高了其功能和/或对更严重挑战的耐受性”。
暴露在高于它们喜欢的20摄氏度的温度下的蠕虫(35摄氏度两小时)比没有暴露的蠕虫寿命长25%,并且在随后的高温下存活的可能性大25%。但是,过多的热量并不是好事。四小时而不是两小时的热暴露降低了随后的热耐力,并使寿命缩短了四分之一。
在离心机中旋转两到四周的果蝇不仅比未旋转的果蝇寿命长,而且在年老时更加敏捷,能够比未接触的同类爬得更高更久。但是,旋转时间超过这个时间的苍蝇并没有茁壮成长。
在生活在1945年核攻击中心以外的日本公民中,与未受辐射的人相比,那些受到低剂量辐射的人可能会显示出稍长的寿命和降低的癌症发病率。在那些生活在原子弹爆炸直接附近的人中,大约有20万人当场死亡。
作者认为,“低剂量刺激DNA损伤修复,通过刺激细胞凋亡[细胞死亡]来清除异常细胞,以及通过刺激抗癌免疫来消除癌细胞 “是辐射荷尔蒙效应的有利影响的核心。
请注意,,这些发现是有争议的,发表在著名的*《柳叶刀》*上的一篇后续论文对其提出了异议。
间歇性禁食和卡路里限制延长了啮齿动物和猴子的寿命,并增加了对与年龄有关的疾病的抵抗力,以及降低血压和增加心率变异性。
间歇性禁食作为一种减肥和改善健康的方法已经变得有些流行。断食算法包括隔天断食、每周一天断食、到第九小时断食、每天一餐断食、16:8断食 (每天断食16小时,在其他8小时的窗口内进行所有饮食),等等。
美国名人脱口秀主持人吉米-基梅尔实行间歇性禁食。“我已经做了几年的事情,,每周有两天让自己挨饿。在周一和周四,我每天吃不到500卡路里,然后在其他五天像猪一样吃。你让身体’吃惊',让它猜测。”
不久以前,这种禁食行为可能会被贴上 “饮食失调 “的标签。由于明显的原因,太少的卡路里是有害的。但是今天,禁食在一些圈子里被认为是正常的,甚至是健康的。
-
锻炼的情况如何?
运动会立即对细胞产生毒性,导致温度升高,有害的氧化剂,以及氧气和葡萄糖的剥夺。然而,有大量的证据表明,运动是促进健康的,而缺乏运动,特别是与长期久坐不动的饮食相结合–整天吃得太多–是致命的。
运动会增加许多参与积极情绪调节的神经递质:多巴胺、5-羟色胺、去甲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内分泌类固醇和内源性阿片肽(内啡肽)。锻炼有助于新神经元和支持性胶质细胞的诞生。锻炼甚至可以减少使用毒品和对毒品成瘾的可能性。
当大鼠在获得自由接触可卡因之前的六周,它们自我施用可卡因的时间比没有经过轮子训练的大鼠晚,而且次数也少。这一发现在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和酒精中也得到了重复。当运动不是自愿的,而是强迫动物进行的,它仍然会导致自愿药物消费的减少。
在人类中,在初中、高中和成年早期,高水平的体育活动可以预测较低的药物使用水平。锻炼也被证明可以帮助那些已经成瘾的人停止或减少。
多巴胺对运动回路的重要性已被报道,在每一个对其进行研究的动物门类中都是如此。线虫C. elegans是一种蠕虫,也是最简单的实验动物之一,它对环境刺激的反应是释放多巴胺,表示当地有丰富的食物。多巴胺在身体运动中的古老作用与它在动机中的作用有关。为了获得我们欲望的对象,我们需要去获得它。
当然,今天容易获得的多巴胺并不要求我们离开沙发。根据调查报告,今天典型的美国人在醒着的时候有一半时间是坐着的,比五十年前多了50%。全球其他富裕国家的数据也具有可比性。当你考虑到我们进化到,每天穿越几十公里来争夺有限的食物供应时,我们现代久坐的生活方式的不利影响是毁灭性的。
我有时会想,我们现代人对成瘾的偏爱,部分是由于毒品提醒我们还有身体的方式在起作用。最流行的视频游戏的特点是头像可以跑、跳、爬、射击和飞行。智能手机,要求我们滚动页面和点击屏幕,巧妙地利用了古代的重复运动习惯,可能是通过几个世纪的研磨小麦和采摘浆果获得的。我们当代对性的关注可能是因为它是最后一项仍然广泛进行的身体活动。
幸福的一个关键是我们离开沙发,移动我们真实的身体,而不是虚拟的身体。正如我告诉我的病人,每天只需在你的邻居家走30分钟就能带来改变。这是因为证据是毋庸置疑的。锻炼对情绪、焦虑、认知、能量和睡眠的积极影响比我能开出的任何药片都要深远和持续。
-
但追求痛苦比追求快乐更难。它违背了我们避免痛苦和追求快乐的先天条件反射。它增加了我们的认知负担。我们必须记住,我们会在痛苦之后感受到快乐,而我们在这种事情上是非常健忘的。我知道我每天早上都要重新学习痛苦的教训,因为我强迫自己下床去锻炼。
追求痛苦而不是快乐也是反文化的,与弥漫在现代生活许多方面的所有感觉良好的信息相悖。佛陀教导人们在痛苦和快乐之间寻找中庸之道,但即使是中庸之道也被 “方便的暴政 “所掺杂。
因此,我们必须寻找痛苦并邀请它进入我们的生活。
以痛治痛
至少从希波克拉底开始,有意应用疼痛来治疗疼痛就已经存在了,他在公元前400年的*《箴言》*中写道:",两种疼痛同时发生,不在身体的同一部位,较强的疼痛会削弱另一种疼痛。”
医学史上有很多使用痛苦或有毒刺激来治疗痛苦疾病状态的例子。有时被称为 “英雄疗法”–拔罐、水泡、烧灼、艾灸–疼痛疗法在1900年以前被广泛采用。随着医学界发现药物疗法,英雄疗法的流行在20世纪开始下降。
随着药物疗法的出现,以痛治痛开始被视为一种庸医。但随着近几十年来药物治疗的局限性和危害性被推到了前台,人们对非药物治疗的兴趣又重新升温,包括疼痛疗法。
2011年,来自德国的克里斯蒂安-斯普伦格(Christian Sprenger)和他的同事在一份权威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为希波克拉底关于疼痛的古老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他们使用神经影像学(大脑的实时图片)来研究热和其他疼痛刺激对20名健康年轻人的胳膊和腿的影响。
他们发现,由最初的疼痛刺激引起的疼痛的主观体验随着,第二个疼痛刺激的应用而减弱。此外,纳洛酮(一种阿片受体阻断剂)阻止了这一现象,这表明,疼痛的应用触发了身体自身的内源性(自制)阿片类药物。
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的教授刘翔于2001年在《*中国科学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重新审视了有几百年历史的针灸疗法,并依靠现代科学来解释它的作用。他认为,针灸的疗效是通过疼痛来介导的,针刺是主要的机制:",针刺会伤及组织,是一种诱发疼痛的有害刺激……以小痛抑制大痛!”
阿片类受体阻断剂纳曲酮目前正被探索作为一种慢性疼痛的医疗手段。其想法是,通过阻断阿片类药物的作用,包括我们制造的阿片类药物(内啡肽),我们欺骗我们的身体制造更多的阿片类药物,作为一种适应性反应。
28名患有纤维肌痛的妇女每天服用一粒低剂量纳曲酮(4.5毫克),持续12周,并服用糖丸(安慰剂)4周。纤维肌痛是一种病因不明的慢性疼痛状况,被认为可能与个人先天性的耐受疼痛的阈值降低有关。
这项研究是双盲的,这意味着参加研究的妇女和医疗保健团队都不知道她们在服用哪种药。每位妇女都有一台手持电脑,每天记录她的疼痛、疲劳和其他症状,并且在停止服用胶囊后继续记录他们的症状四周。
该研究的作者报告说,“参与者,与安慰剂相比,他们在服用LDN[低剂量纳曲酮]时的疼痛评分明显减少。他们还报告说,在服用低剂量纳曲酮时,对生活的总体满意度有所提高,情绪也有所改善”。
-
自20世纪初以来,人们就开始对大脑进行电疗,以治疗精神疾病。1938年4月,乌戈-切雷蒂和卢西诺-比尼对一名40岁的病人进行了首次电休克疗法(ECT)治疗,他们对病人的描述如下。
“他只用一种由奇怪的新词组成的难以理解的胡言乱语来表达自己,而且,自从他从米兰乘火车抵达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确定他的身份。”
当塞雷蒂和比尼第一次给他的大脑通电时,他们观察到 “病人在床上突然跳了起来,所有的肌肉都非常短暂地绷紧;然后他立即倒在床上,没有失去意识。病人现在开始用他的声音唱歌,然后就沉默了。从我们对狗的经验中可以看出,电压保持得太低了”。
塞雷蒂和比尼争论着是否应该在更高的电压下再进行一次电击。在他们交谈的时候,病人喊道:“不要再来了!"。Mortifera!"(“不要再来了!这会杀了我!")。尽管他抗议,他们还是实施了第二次电击–这是一个警告性的故事,提醒人们在1938年没有火车票或 “可确定的身份 “的情况下不要到达米兰。
一旦 “病人 “从第二次冲击中恢复过来,塞雷蒂和比尼观察到他 “自己坐了起来,平静地看着他,脸上带着模糊的微笑,好像在问他要干什么。我问他’你发生了什么事? ‘他回答,不再胡言乱语:‘我不知道,也许我一直在睡觉。最初的病人在两个月内又接受了13次ECT治疗,根据报告,出院时完全康复。
今天,ECT仍在实施,效果很好,尽管更加人道化。肌肉松弛剂和麻痹剂可以防止痛苦的收缩。麻醉剂允许病人在整个手术过程中保持睡眠和大部分无意识状态。因此,今天不能说疼痛本身是调解因素。
尽管如此,ECT为大脑提供了一种荷尔蒙冲击,这反过来又刺激了广泛的补偿反应,以重新确立平衡。“ECT在大脑的宏观和微观环境中带来各种神经生理和神经化学变化。涉及基因表达、功能连接、神经化学物质、血脑屏障的渗透性、免疫系统的改变等多种变化被认为是ECT治疗效果的原因。”
-
你会记得大卫,那个害羞的电脑迷,在对处方兴奋剂上瘾后,最终被送进了医院。
出院后,他开始每周与我们团队中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治疗师进行暴露疗法。暴露疗法的基本原则是让人们以递增的方式接触导致他们试图逃避的不舒服情绪的事物–在人群中、开车过桥、坐飞机–并通过这样做增强他们对该活动的容忍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甚至可能开始享受这种活动。
正如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的名言–古往今来许多人都有同感–“没有杀死我的东西使我更强大”。
鉴于David最害怕的是与陌生人交谈,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强迫自己与同事进行小范围的交谈。
“我的治疗功课,“他几个月后告诉我,“就是去厨房、休息室或工作场所的食堂,与随机的人交谈。我有一个剧本。‘嗨,我叫大卫。我在软件开发部门工作。我设定了一个时间表:午餐前、午餐时和午餐后。然后我必须测量我在午餐前、午餐中和午餐后的苦恼,从一到一百,一百是我能想象的最糟糕的苦恼。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越来越多地计算自己的步数、呼吸、心跳,给某些东西加上数字已经成为我们掌握和描述经验的一种方式。对我来说,量化事物并不是我的第二天性,但我已经学会了适应,因为这种自我意识的方法似乎对我们在硅谷拥有如此多的具有科学头脑的计算机和工程类型的人来说特别有共鸣。
“在互动之前,你的感觉如何?呃,你是几号?“我问道。
“在我一百岁之前。我只是觉得很害怕。我的脸变得通红。我在流汗。”
“你担心会发生什么?”
“我害怕其他人看着我并笑。或者打电话给人际关系或保安,因为我看起来很疯狂。
“进展如何?”
“我担心会发生的事情都没有发生。没有人打电话给人力资源部或保安。我尽可能长时间地呆在当下,只是让我的焦虑冲昏头脑,同时也尊重他们的时间。这些互动可能持续了四分钟”。
“事后你感觉如何?”
“事后我大约有四十岁了。焦虑少了很多。因此,我按计划每天做三次,持续了几个星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变得越来越容易。然后我在工作之外的人面前挑战自己。”
“告诉我。”
“在星巴克,我故意和咖啡师闲聊。过去我从来不会这样做。我总是用应用程序点餐,以避免与人交流。但是这一次,我直接走到柜台前,点了我的咖啡。我最害怕的是说或做一些愚蠢的事情。我做得很好,直到我把一点点咖啡洒在柜台上。我感到非常尴尬。当我把这件事告诉我的治疗师时,她让我再做一次–这次是故意打翻我的咖啡。下一次我在星巴克时,我,故意打翻了我的咖啡。我感到很焦虑,但我已经习惯了。”
“你在笑什么?”
“我几乎无法相信我的生活现在有多么不同。我的警惕性降低了。我不需要预先计划那么多,以避免与人交往。我现在可以坐上拥挤的火车而不至于上班迟到,因为我在等下一班,再下一班。我实际上很享受与我再也见不到的人见面。”
-
亚历克斯-霍诺德(Alex Honnold)因无绳攀登优胜美地的艾尔卡皮坦(El Capitan)而闻名世界,他在大脑成像过程中被发现杏仁核的激活低于正常水平。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杏仁核是大脑的一个区域,当我们看可怕的图片时,它在fMRI机器上会亮起来。
研究霍诺德大脑的研究人员推测,他与生俱来的恐惧感比其他人少,他们假设,这反过来使他能够完成超人的攀登壮举。
但Honnold本人并不同意他们的解释。“我已经做了很多单人攀登的工作,并且在我的攀登技能上做了很多工作,我的舒适区已经相当大。因此,我所做的这些看起来很离谱的事情,对我来说似乎很正常。”
对霍诺德的大脑差异最可能的解释是通过神经适应发展对恐惧的耐受性。我的猜测是,霍诺德的大脑在恐惧敏感性方面开始时与普通人的大脑没有什么不同。现在不同的是,他通过多年的攀登训练了自己的大脑,使其对恐惧的刺激不产生反应。吓唬霍诺德的大脑要比普通人多得多,因为他已经逐渐将自己暴露在死亡的壮举中。
值得注意的是,当Honnold进入fMRI机器为他的 “无畏的大脑 “拍照时,他几乎惊慌失措,这也告诉我们,恐惧容忍度不一定会在所有的经历中转化。
Alex Honnold和我的病人David一直在攀登同一座恐惧山的不同部分。正如霍诺德的大脑适应了在没有绳索的情况下攀登岩壁一样,大卫发展了精神上的老茧,使他能够忍受焦虑,并获得了对自己和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能力的信心和能力。
疼痛来治疗疼痛。用焦虑来治疗焦虑。这种方法是反直觉的,与我们在过去150年里所学到的关于如何管理疾病、痛苦和不适的方法完全相反。
对疼痛上瘾
“迈克尔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我在最初的冷水冲击中感受到的痛苦越多,之后的高潮就越大。因此,我开始想办法提高难度。
“我买了一个肉类冰柜–一个有盖子的槽子,内置冷却线圈,每天晚上往里面装水。到了早上,表面上有一层薄薄的冰,温度在30度以下。在进去之前,我必须先破冰。
“后来我读到,人体在几分钟后就会把水加热,除非水是流动的,就像一个漩涡。所以我买了一个马达,放入冰浴中。这样,我在里面的时候就可以维持接近冰点的温度。我还为我的床买了一个水力发电的床垫垫,我把它保持在最低温度,大约55°F(13°C)。”
迈克尔突然停止了说话,带着歪歪扭扭的笑容看着我。“哇,我在谈论这个的时候意识到……这听起来像是一种瘾。”
-
2019年4月,缅因大学的艾伦-罗森瓦瑟教授给我发来电子邮件,希望得到一份我最近与一位同事发表的关于运动对治疗成瘾的作用的章节。他和我从未见过面。在得到出版商的许可后,我把这一章发给他。
大约一周后,他再次写信,这次的内容如下。
谢谢你的分享。我注意到你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小鼠和大鼠的轮子运行是自愿运动的模型还是病理性运动(运动成瘾)的模型。一些被安置在轮子里的动物表现出可能被认为是过度的跑步水平,一项研究表明,野生啮齿动物会使用被放在外面环境中的跑步轮。
我很着迷,立即给他回了信。低的是一系列的对话,在这些对话中,罗森瓦瑟博士花了四十年的时间研究昼夜节律,也被称为 “时钟领域”,他向我传授了跑步轮。
“罗森瓦瑟告诉我:“当人们第一次开始做这项工作时,人们错误地认为,跑轮是一种跟踪动物自发活动的方式:休息与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敏感地意识到,跑轮并不是惰性的。它们本身就很有趣。其中一个开端是成人海马神经发生。”
这指的是几十年前的发现,与以前的教导相反,人类可以在大脑中生成新的神经元,直到中年和晚年。
“一旦人们接受了新神经元的诞生并整合到神经回路中,“罗森瓦瑟继续说,“刺激神经发生的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是用跑轮,甚至比丰富的环境[例如复杂的迷宫]更有效。这导致了整个跑步轮研究时代的到来。
“事实证明,“罗森瓦瑟说,“跑轮是由驱动强迫性药物使用的相同的内啡肽、多巴胺、内啡肽途径所支配。重要的是要知道,跑步轮不一定是健康生活方式的模式”。
简而言之,跑步轮是一种毒品。
小鼠被放置在一个由230米长的隧道组成的复杂迷宫中,包括水、食物、挖掘材料、巢穴–换句话说,一个有很多很酷的东西可以做的大区域–以及一个的转轮,它们会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转轮上,而把迷宫的大段区域留在那里不被探索。
一旦啮齿动物开始使用跑轮,它们就很难停下来。啮齿动物在跑轮上跑得比它们在平坦的跑步机上或在迷宫中跑得更远,也比它们在自然环境中正常运动时跑得更远。
笼子里的啮齿动物如果能接触到跑轮,就会跑到它们的尾巴永久地向上和向后弯曲,形成跑轮的形状:跑轮越小,尾巴的曲线就越尖锐。在某些情况下,大鼠一直跑到死。
运转轮的位置、新颖性和复杂性影响其使用。
野鼠喜欢方形的轮子而不喜欢圆形的,喜欢有障碍物的轮子而不喜欢没有障碍物的轮子。它们在跑轮子时表现出非凡的协调能力和杂技技巧。就像滑板公园里的青少年一样,它们允许 “自己在前进和后退的方向上反复被带到轮子的顶部,在轮子的顶部表面上运行,或在轮子的外部’上升’,同时用尾巴保持平衡”。
C.M. Sherwin在其1997年对跑步轮的评论中推测了跑步轮的内在强化特性。
轮子运行的三维质量可能对动物有强化作用。在轮子运行过程中,动物,将经历其运动速度和方向的快速变化,这部分是由于外源力:轮子的动量和惯性。这种经验可能是强化的,类似于(一些!)人类在游乐场享受快乐的游乐设施,特别是在垂直平面的运动……动物运动的这种变化在 “自然 “情况下不太可能经历。
荷兰莱顿大学医学中心的约翰娜-梅耶尔和尤里-罗伯斯在野鼠生活的城市地区放置了一个转轮,并在一个公众无法进入的沙丘上放置了另一个。他们在每个地方都放置了一台摄像机,以记录两年来访问笼子的每只动物。
结果是有数百个动物使用跑步轮的例子。“观察结果显示,,野鼠全年都在轮子里奔跑,在绿色城区,春末稳步增加,夏季达到高峰,而在沙丘区,夏中后期增加,在秋末达到高峰。”
使用转轮的不仅限于野鼠。还有鼩鼱、老鼠、蜗牛、蛞蝓和青蛙,它们中的大多数都表现出对轮子的有意和有目的的参与。
作者的结论是:“即使没有相关的食物奖励,轮子运行也可以被体验为奖励,这表明与觅食无关的动机系统的重要性”。
-
极限运动–跳伞、风筝冲浪、悬挂式滑翔、雪橇、下坡滑雪/滑雪板、瀑布皮划艇、攀冰、山地自行车、峡谷摇摆、蹦极、跳垒、翼装飞行–在快乐与痛苦的平衡中,狠狠地、快速地砸下。强烈的疼痛/恐惧加上一针肾上腺素创造了一种强有力的药物。
科学家已经表明,,仅仅是压力就可以增加大脑奖励途径中多巴胺的释放,导致与可卡因和甲基苯丙胺等成瘾药物相同的大脑变化。
正如我们通过反复接触而对快乐刺激产生耐受性一样,我们也可以对痛苦刺激产生耐受性,将我们的大脑重置到痛苦的一边。
一项对跳伞运动员与对照组(划船运动员)的研究发现,重复跳伞的人更有可能在他们的余生中出现失重症,即缺乏快乐。
作者写道:“跳伞与成瘾行为有相似之处,经常接触’自然高’的经历与失落症有关”。我很难把从13,000英尺的飞机上跳下来称为 “自然高”,但我确实同意作者的总体结论。跳伞可能会让人上瘾,如果反复参与,会导致持续的精神障碍。
技术使我们能够挑战人类痛苦的极限。
2015年7月12日,超级马拉松运动员斯科特-朱雷克(Scott Jurek)打破了跑完阿巴拉契亚山径的速度记录。他用46天8小时7分钟从乔治亚州跑到缅因州(2189英里)。为了完成这一壮举,他依靠了以下技术和设备。轻便、防水、防热的衣服,“气网 “跑鞋,GPS卫星追踪器,GPS手表,iPhone,补水系统,电解质片,铝制可折叠登山杖,“模拟雾化的工业喷水器”,“一个冰冷却器来冷却我的核心”,每天6000-7000卡路里,以及一个由他妻子和工作人员驾驶的支援车顶部的太阳能板驱动的气动压腿按摩器。
2017年11月,刘易斯-普格在南极洲附近零下3摄氏度(26˚F)的水中游了一公里,只穿着泳衣。到达那里需要从普格的家乡南非乘飞机和海运到南乔治亚岛,一个偏远的英国岛屿。普格一游完泳,他的船员就把他送到附近的一艘船上,把他浸在热水里,在那里呆了50分钟,使他的核心体温恢复到正常。如果没有这次干预,他肯定会死。
亚历克斯-霍诺德(Alex Honnold)登上埃尔卡皮坦(El Capitan)似乎是人类的终极技术成就。没有绳索。没有装备。只有一个人对抗地心引力,展示了勇气和技巧的死亡。但从各方面来看,如果没有 “在Freerider[他所走的路线]上花费数百个小时,系在绳索上,为每个部分进行精确排练的编排,,记住数以千计的复杂的手和脚的顺序”,霍诺德的壮举就不可能实现。
霍诺德的登顶被一个专业的电影摄制组拍摄下来,变成了一部有数百万人观看的电影,导致了大量的社交媒体追随者和全世界的名声。财富和名人,我们多巴胺经济的另一个层面,促成了这些极限运动的成瘾潜力。
“过度训练综合征 “是耐力运动员中一种被描述得很好但却不为人知的情况,他们训练得太多,以至于达到了运动不再产生曾经那么多的内啡肽的程度。相反,运动使他们感到枯竭和焦虑,就好像他们的奖励平衡已经达到极限并停止工作,这与我们在我的病人克里斯和阿片类药物中看到的情况相似。
我并不是说每个从事极限和/或耐力运动的人都会上瘾,而是强调任何物质或行为上瘾的风险会随着效力、数量和持续时间的增加而增加。在平衡中太过用力、太过长久地倚靠痛苦一方的人也可能最终陷入持续的多巴胺缺失状态。
-
太多的疼痛,或太强烈的形式,会增加对疼痛上瘾的风险,这是我在临床实践中看到的情况。我的一个病人经常跑步,她的腿骨出现了骨折,即使这样也没有停止跑步。另一个病人用剃刀片切割她的前臂内侧和大腿,以感受到一种快感,并平息她心中的不断反思。即使冒着严重的疤痕和感染的风险,她也不能停止切割。
当我把他们的行为概念化为成瘾,并像对待任何成瘾的病人一样对待他们时,他们就会好起来。
沉迷于工作
“工作狂 “是社会的一个著名成员。在硅谷,100小时的工作周和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是常态,这一点也许是最真实的。
2019年,在经历了三年的每月工作旅行后,我决定限制旅行,努力使工作和家庭生活恢复平衡。起初,我透明地让人们知道了其中的原因。我想有更多时间与家人在一起。人们似乎对我以 “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这样一个嬉皮士的理由拒绝他们的邀请感到恼火和不快。我最终不得不说我有另一个约定,这遇到的阻力较小。我在其他地方工作,似乎是可以接受的。
从奖金和股票期权的前景到晋升的承诺,无形的激励现在已经交织在白领工作的结构中。甚至在像医学这样的领域,医疗保健提供者看更多的病人,开更多的处方,做更多的手术,因为他们被激励这样做。我每个月都会收到一份关于我的生产力的报告,以我代表我的机构开出多少账单来衡量。
相比之下,蓝领工作越来越机械化,并且脱离了工作本身的意义。在遥远的受益人的雇佣下工作,自主性有限,经济收益不高,而且对共同的使命感不强。零散的流水线工作削弱了成就感,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与最终产品消费者的接触,而这两点都是内部激励的核心。其结果是一种 “努力工作/努力玩耍 “的心态,强迫性的过度消费成为一天工作结束后的奖励。
因此,难怪那些受过高中以下教育、从事低薪工作的人比以往更少工作,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工薪族则更多工作。
到2002年,收入最高的20%的人长时间工作的可能性是收入最低的20%的人的两倍,而且这种趋势还在继续。经济学家推测,这种变化是由于经济食物链顶端的人获得了更高的回报。
我发现有时一旦我开始工作,就很难阻止自己。深度集中的 “流动 “本身就是一种毒品,释放出多巴胺,创造出自己的高潮。这种一心一意的专注,虽然在现代富裕国家得到了大量的奖励,但当它使我们在生活的其余部分远离与朋友和家人的亲密联系时,可能是一个陷阱。
疼痛的裁决
似乎是在回答他自己关于是否对冷水浸泡上瘾的问题,迈克尔说:“它从未失控。有两到三年的时间,我每天早上洗十分钟的冰水澡。现在我不像以前那么喜欢了。我平均每周做三次。
“真正酷的是,“他继续说,“它已经成为一项家庭活动,是我们和朋友一起做的事情。吸毒是,总是社交。在大学里,很多人都在狂欢。他们总是坐在一起喝酒或吸食可卡因。
“现在我不再那样做了。相反,我们的几个朋友会过来。他们也有孩子,我们有一个冷水派对。我有一个定制的水槽,设置在40度左右,每个人都轮流进入,与热水池交替进行。我们有一个计时器,我们互相打气,包括孩子们。这一趋势在我们的朋友中也得到了响应。我们朋友圈里的这群女性每周去一次海湾,然后进去。她们把自己浸泡到脖子上。那水有五十多度。”
“然后呢?”
“我不知道,“他笑着说。“他们可能出去聚会了。”
我们都笑了。
“你已经说过好几次,你这样做是因为它让你感到活着。你能解释一下吗?”
“我不太喜欢活着的感觉。毒品和酒精是喜欢它的一种方式。现在我不能再那样做了。当我看到人们在聚会时,我还是有点嫉妒他们得到的逃避。我可以看到他们得到了缓和的机会。冷水提醒我,活着的感觉是好的。”
-
如果我们消费了太多的痛苦,或以太强烈的形式,我们就有可能出现强迫性、破坏性的过度消费。
但是,如果我们消耗的量恰到好处,“以小的痛苦抑制大的痛苦”,我们就会发现通往荷尔蒙治疗的道路,甚至可能偶尔会有 “快乐的感觉”。
第八章
彻底的诚实
每个主要的宗教和道德准则都把诚实作为其道德教义的基本内容。我所有实现长期康复的病人都依靠讲真话来维持心理和身体健康。我也相信,彻底的诚实不仅有助于限制强迫性的过度消费,也是美好生活的核心。
问题是,说实话如何改善我们的生活?
让我们首先确定,说真话是痛苦的。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有说谎的习惯,而且我们都会这样做,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
儿童早在两岁时就开始撒谎。孩子越聪明,他们就越有可能撒谎,而且越擅长撒谎。撒谎在三岁到十四岁之间趋于减少,这可能是因为孩子们越来越意识到撒谎是如何伤害他人的。另一方面,由于计划和记忆的能力越来越高,成年人能够比儿童更复杂地进行反社会的谎言。
成人平均每天说0.59至1.56个谎言。骗子,骗子,裤子着火了。我们的短裤上都有一点烟冒出来。
人类并不是唯一具有欺骗能力的动物。动物王国中充斥着欺骗作为武器和盾牌的例子。例如,Lomechusa pubicollis甲虫能够通过假装成蚂蚁的一员来渗透到蚂蚁群中,它通过释放一种化学物质,使自己闻起来像蚂蚁。一旦进入,该甲虫就以蚂蚁卵和幼虫为食。
但没有其他动物能与人类的撒谎能力相媲美。
进化生物学家推测,人类语言的发展解释了我们说谎的倾向和卓越的能力。这个故事是这样的。智人的进化在大型社会群体的形成中达到顶峰。大型社会群体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发展了复杂的交流形式,允许先进的相互合作。用于合作的话语也可以用来欺骗和误导。语言越是先进,谎言就越是复杂。
当涉及到竞争稀缺资源时,谎言可以说有一些适应性的优势。但在一个充裕的世界里,说谎有可能导致孤立、渴望和病态的过度消费。让我解释一下。
-
“你看起来不错,“2019年4月,我们坐在对面时,我对玛丽亚说。她的深棕色头发做了一个,专业而讨人喜欢的风格。她穿着一件适度的有领衬衫和休闲裤。她面带微笑,精神抖擞,看起来很有精神,就像过去五年我为她治疗时一样。
在我认识她的所有时间里,玛丽亚的酒精使用障碍得到了持续缓解。她来找我时已经处于康复状态,是通过参加匿名戒酒会和与她的戒酒会赞助人合作而实现的。她偶尔会来找我,检查和补充她的药物。我敢肯定,我从她那里学到的东西比她从我这里学到的要多。她教给我的一件事是,说实话是她康复的根本。
在成长过程中,她学到了相反的东西。她的母亲酗酒,包括在玛丽亚在车上时喝得酩酊大醉,并开车。她的父亲离开家庭好几年了,去了一个没有人被允许说出名字的地方,甚至现在她也不愿意透露,因为她尊重他的隐私。她不得不照顾她的弟弟妹妹,同时向外界假装家里一切都很好。当玛丽亚在20多岁时开始酗酒时,她已经很熟练地在不同的现实版本中洗牌了。
为了说明诚实在她新的清醒生活中的重要性,她告诉我这个故事。
“我下班回家,发现一个亚马逊包裹在等着马里奥。”
马里奥是玛丽亚的弟弟。她和她的丈夫迭戈一直和马里奥住在一起,以此来相互支持,并在硅谷的高端房地产市场节省租金。
“我决定打开它,尽管它不是写给我的。我的一部分知道我不应该这样做。以前我打开他的包裹时,他非常生气。但我知道我可以用上次的借口:我把他的名字误认为是我的,因为他们是如此相似。我告诉自己,在辛苦工作了一天之后,我应该得到一个小小的快乐。我现在不记得里面是什么了。
“在我打开包裹后,我把它重新封好,和其他的邮件放在一起。说实话,我忘了这件事。几个小时后,马里奥回到家,立即指责我打开了它。我撒谎,说我没有。他又问我,我又撒谎了。他一直说,‘看起来像是有人打开的。我一直说,‘不是我’。然后他真的很生气,拿着他的邮件和包裹,走进他的房间,把门关上。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好。第二天早上,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我走进厨房,马里奥和迭戈正在吃早餐,我说:“马里奥,我确实打开了你的包裹。我知道那是你的,但我还是打开了它。然后我试图把它掩盖起来。然后我撒了谎。我真的很抱歉。请原谅我’。”
“告诉我为什么诚实是你康复的一个重要部分,“我说。
“在我喝酒的时候,我永远不会承认真相。那时,我对所有事情都撒谎,从不为我所做的事情负责。有那么多的谎言,其中一半甚至没有意义。”
玛丽亚的丈夫迭戈曾经告诉我,玛丽亚曾经躲在浴室里喝酒,打开淋浴,这样迭戈就不会听到啤酒瓶打开的声音,没有,他可以听到她把开瓶器从浴室门后的藏身处拿出来时的叮当声。他描述了她以前是如何一口气喝掉六包啤酒的,然后把啤酒换成水,再把瓶盖粘上。“她真的以为我闻不到胶水的味道,也尝不出水和酒的区别吗?”
玛丽亚说:“我撒谎是为了掩盖我的酗酒,但我也对其他事情撒谎。那些根本不重要的事情:我去哪里,我什么时候回来,我为什么迟到,我早餐吃了什么。
玛丽亚已经养成了撒谎的习惯。一开始是为了掩盖她母亲的酗酒和她父亲的缺席,最后是为了掩盖她自己的酒瘾,后来变成了为了自己而说谎。
撒谎的习惯非常容易陷入。我们都经常说谎,大多数时候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的谎言是如此之小,难以察觉,以至于我们说服自己我们说的是实话。或者说,即使我们知道自己在撒谎,这也无关紧要。
“当我那天告诉马里奥真相时,尽管我知道他会生气,但我知道在我身上、在我的生活中有些东西真的改变了。我知道我致力于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以更好的方式生活。我受够了那些充斥在我脑海中的小谎言,它们使我感到内疚和害怕……为撒谎而内疚,害怕有人会发现。我意识到,只要我说的是真话,我就不必担心这些了。我是自由的。在我把包裹的真相告诉我哥哥后,这是我们的关系越来越近的垫脚石。之后我回到楼上,我感觉非常好。”
-
激进的诚实–对大大小小的事情说实话,特别是当这样做暴露了我们的缺点并带来后果时–不仅对戒除毒瘾至关重要,而且对我们所有试图在我们奖励饱和的生态系统中过上更平衡的生活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它在许多层面上发挥作用。
首先,激进的诚实促进对我们行为的认识。第二,它促进了亲密的人际关系。第三,它导致了真实的自传,使我们不仅对现在的自己负责,也对未来的自己负责。此外,说真话是有感染力的,甚至可以防止未来成瘾的发生。
认识
早些时候,我描述了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以说明身体的自我束缚。这个神话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尾声,与此有关。
你会记得,奥德修斯要求他的船员把他绑在帆船的桅杆上,以避免塞壬的引诱。但如果你仔细想想,他完全可以像他命令其他船员那样,把蜂蜡塞进自己的耳朵里,这样就可以省去很多麻烦了。奥德修斯并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只有当听到海妖的人能够活着讲述这个故事时,才可以杀死海妖。奥德修斯通过事后讲述他濒临死亡的航行,战胜了塞壬。杀人是在讲述过程中进行的。
奥德修斯的神话强调了行为的一个关键特征:改变。叙述我们的经历使我们掌握了这些经历。无论是在心理治疗的背景下,还是与戒酒协会的赞助人交谈,向牧师忏悔,向朋友倾诉,或者写日记,我们的诚实披露使我们的行为得到缓解,在某些情况下允许我们第一次看到它。对于那些涉及到有意识意识之外的自动程度的行为,这一点尤其真实。
当我强迫性地阅读言情小说时,我只是部分地意识到这样做。也就是说,在我意识到这种行为的同时,我也没有意识到它。这是一种公认的成瘾现象,一种类似于醒着的梦的半意识状态,通常被称为否认。
拒绝很可能是由我们大脑的奖励途径部分和高级皮质脑区之间的脱节所介导的,高级皮质脑区允许我们叙述我们的生活事件,欣赏后果,并计划未来。许多形式的成瘾治疗涉及加强和更新大脑这些部分之间的联系。
神经科学家Christian Ruff和他的同事研究了诚实的神经生物学机制。在一个实验中,他们邀请参与者(共145人)玩一个游戏,用电脑界面掷骰子换钱。在每次掷骰子之前,电脑屏幕都会显示哪些结果会产生金钱回报,最高可达90瑞士法郎(约100美元)。
与赌场的赌博不同,参与者可以对掷骰子的结果撒谎以增加他们的赢利。研究人员通过比较报告的成功掷骰子的平均百分比()和完全诚实报告所暗示的50%的基准,能够确定作弊的程度。毫不奇怪的是,参与者经常撒谎。与50%的诚实基准相比,参与者报告说,他们的掷骰子有68%得到了预期的结果。
然后,研究人员使用一种叫做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的工具,用电来提高参与者的前额脑皮层的神经元兴奋性。前额叶皮层是我们大脑最前面的部分,就在额头后面,参与决策、情绪调节和未来规划等许多复杂的过程。它也是参与讲故事的一个关键区域。
研究人员发现,当前额叶皮层的神经兴奋性上升时,说谎就会减少一半。此外,诚实度的提高 “不能用物质上的自我利益或道德信仰的变化来解释,而且与参与者的冲动性、承担风险的意愿和情绪无关。”
他们的结论是,诚实可以通过刺激前额叶皮层得到加强,这与 “人类大脑已经进化出专门控制复杂社会行为的机制 “的观点一致。
这个实验让我想到,练习诚实是否能刺激前额叶皮质的激活。我给瑞士的克里斯蒂安-鲁夫(Christian Ruff)发了电子邮件,问他对这个想法的看法。
“如果刺激前额叶皮层会使人们更加诚实,那么是否也有可能是更加诚实刺激了前额叶皮层?说实话的做法是否会加强我们用于未来规划、情绪调节和延迟满足的大脑部分的活动和兴奋性?“我问道。
他回答说:“你的问题很有意义。我没有明确的答案,但我同意你的直觉,即一个专门的神经过程(如涉及诚实的前额过程)应该通过反复使用得到加强。根据唐纳德-赫伯(Donald Hebb)的老话,这就是大多数类型的学习过程中发生的情况,‘什么东西一起开火,什么东西一起布线’。”
我喜欢他的回答,因为这意味着练习激进的诚实可能会加强专门的神经回路,就像学习第二语言、弹钢琴或掌握数独可以加强其他回路一样。
与康复者的生活经验相一致,讲真话可能会改变大脑,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快乐-痛苦平衡以及驱动强迫性过度消费的心理过程,从而改变我们的行为。
-
我自己对自己的言情小说问题的觉悟发生在2011年,当时我正在教一群圣马特奥的精神病学居民如何与病人谈论成瘾行为。这对我来说不无讽刺意味。
我当时在圣马特奥医疗中心的一楼教室里,给9名精神病学住院医生讲如何与病人进行有关毒品和酒精使用的通常很困难的谈话。讲座进行到一半时,我停下来邀请学生们参与一项学习练习。",与一个伙伴讨论你想要改变的习惯,并讨论你可能采取的一些步骤来实现这一改变。”
学生在这个练习中谈论的常见例子包括 “我想多运动 “或 “我想少吃糖”。换句话说,是比较安全的话题。严重的成瘾,如果他们有的话,通常不会被提及。尽管如此,通过谈论他们不满意并想改变的任何行为,学生们可以深入了解病人作为保健提供者与他们进行这些对话可能是什么情况。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总是有机会发现自己的一些问题。
我意识到,由于学生人数是单数,我必须与一名学生搭档。我和一个说话温和、思维缜密的年轻人结成搭档,他在整个讲座过程中一直在认真听讲。我扮演病人的角色,这样他可以练习他的技能。然后我们会交换。
他问了我一个我想改变的行为。他温和的态度邀请我说出来。令我惊讶的是,我开始向他讲述我深夜阅读小说的淡定版本。我没有说明我在读什么,也没有说明问题的程度。
我说:“我晚上熬夜看书太晚了,影响了我的睡眠。我想改变这种状况。”
我一说出来,就知道这是真的,既知道我熬夜读书,也知道我想改变这种行为。但在那一刻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两件事。
“你为什么想做出这种改变?“他问道,使用了动机访谈中的一个标准问题,这是一种由临床心理学家威廉-R-米勒和斯蒂芬-罗尔尼克开发的咨询方法,用于探索内部动机和解决矛盾。
“我说:“它干扰了我的能力,使我不能像我想的那样有效地工作和与我的孩子相处。
他点了点头。“这些听起来是很好的理由。”
他是对的。这些都是很好的理由。在大声说出这些理由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我的行为对我的生活和我关心的人产生了多么大的负面影响。
他接着问:“如果你停止这种行为,你会放弃什么?”
“我将放弃我从阅读中获得的乐趣。我喜欢这种逃避,“我马上回答。“但这种感觉对我来说没有我的家庭和工作那么重要。”
通过再次大声说出来,我意识到这是真的:我重视我的家庭和工作,高于我自己的乐趣,为了按照我的价值观生活,我需要停止强迫性的逃避性阅读。
“你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这种行为?”
“我可以摆脱我的电子阅读器了。易于获得廉价读物,助长了我的深夜阅读。”
“听起来是个好主意,“他说,并微笑着。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作为病人的工作。
第二天,我一直在想我们的谈话。我决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远离言情小说。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扔掉我的电子阅读器。头两个星期,我经历了低门槛的戒断,包括焦虑和失眠,特别是在晚上睡觉前,这时我通常会读故事。我已经失去了自己入睡的艺术。
月底时,我感觉好些了,允许自己再次阅读浪漫小说,计划更适度地阅读。
相反,我沉迷于色情小说,连续两晚熬夜,结果感到疲惫不堪。但现在我看到了我的行为是什么–强迫性的、自我毁灭的模式–这使我失去了乐趣。我感到越来越有决心要永远停止这种行为。我清醒的梦想即将结束。
诚实能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说出真相会吸引人们,特别是当我们愿意暴露自己的弱点时。这是反直觉的,因为我们认为揭开自己不太理想的一面会把人赶走。从逻辑上讲,当人们了解到我们的性格缺陷和过失时,他们会与自己保持距离,这是合理的。
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人们走得更近。他们在我们的破碎中看到自己的脆弱和人性。他们得到安慰,在他们的疑虑、恐惧和弱点中,他们并不孤单。
-
雅各布和我在他复发强迫性手淫后的数月和数年里断断续续地见面。在那段时间里,他继续戒除他的成瘾行为。实行彻底的诚实,特别是对他妻子的诚实,是他持续康复的基础。在我们的一次访问中,他与我分享了一个故事,那是他和妻子搬回一起住后不久发生的事情。
在搬回他们共同的家的第二天,她正在整理浴室,当她注意到浴帘的一个环不见了。她问雅各布是否知道它发生了什么。
“我愣住了,“雅各布告诉我。“我完全知道浴帘环的事,但我不想告诉她。我有很多好的理由。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果我告诉她,她只会不高兴。我们之间的关系现在是那么好。这将会把它搞乱。”
但他又提醒自己,他的谎言和偷偷摸摸的行为对他们的关系有多大的腐蚀性。在她搬回来之前,他曾向她保证,无论如何他都会对她诚实。
“所以我说,‘我用它来制造我的一台机器,现在差不多一年了,在你离开之后。这不是什么最近的事。但我保证我将对你诚实,所以我告诉你’。”
“她做了什么?“我问道。
“我认为她会告诉我一切都结束了,她又要离开了。但相反,她没有对我大喊大叫。她没有离开我。她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她说,‘谢谢你告诉我真相’。然后她拥抱了我。”
-
亲密关系是其自身的多巴胺来源。催产素是一种与恋爱、母子关系、和性伴侣的终身配对关系有很大关系的荷尔蒙,它与大脑奖励通路中分泌多巴胺的神经元上的受体结合,增强奖励通路的发射。换句话说,催产素会导致大脑多巴胺的增加,这是斯坦福大学神经科学家林洪、罗布-马伦卡和他们的同事最近的一项发现。
在他向妻子坦诚相告之后,在她表达了温暖和同情之后,雅各布可能经历了催产素和多巴胺在其奖励途径中的激增,鼓励他再次这样做。
虽然讲真话会促进人类的依恋,但强迫性地过度消费高多巴胺的商品是人类依恋的对立面。消费会导致孤立和冷漠,因为药物会取代从与他人的关系中获得的回报。
实验表明,一只自由的老鼠会本能地努力释放另一只被困在塑料瓶里的。但是,一旦这只自由的老鼠被允许自我施用海洛因,它就不再有兴趣帮助笼中的老鼠了,它可能太过沉浸在阿片类药物的迷雾中,而不关心它的同伴。
-
任何导致多巴胺增加的行为都有被利用的可能。我指的是一种已经在现代文化中盛行的 “披露色情”,在这种情况下,披露我们生活的私密方面成为一种,以操纵他人获得某种类型的自私满足,而不是通过共享人性的时刻促进亲密关系。
在2018年的一个关于成瘾的医学会议上,我坐在一个男人旁边,他说他正在从成瘾中长期康复。他在那里向观众讲述他的康复故事。就在他上台前,他转向我说:“准备好哭吧。“我被这句话吓到了。他预料到我对他的故事会有什么反应,这让我感到不安。
他确实讲述了一个令人痛心的成瘾和康复的故事,但我没有被感动得流泪,这让我感到惊讶,因为我通常会被苦难和救赎的故事深深感染。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故事似乎是不真实的,尽管它可能在事实上是正确的。他所说的话与背后的情感并不相符。与其说他让我们有幸了解了他生命中的一段痛苦时光,不如说他在哗众取宠和操纵。也许这只是他以前讲过很多次的问题。在重复中,它可能已经变得陈旧。不管是什么原因,它没有让我振作起来。
在AA中有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叫做 “醉生梦死”,指的是那些为了娱乐和炫耀而分享的醉生梦死的故事,而不是教导和学习。醉话往往会引发渴求,而不是促进康复。诚实的自我披露和操纵性的醉酒对话之间的界限是很细微的,包括内容、语气、腔调和影响上的细微差别,但当你看到它时,你就知道了。
我希望我在这里披露的信息,包括我自己的信息和我的病人允许我分享的信息,永远不要偏离这条线的错误方向。
真实的自传创造责任感
关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单一、简单的真相,就像链条上的一环,转化为真实的自传体叙事。自传式叙事是对生活时间的基本衡量。我们叙述的关于我们生活的故事不仅是对我们过去的衡量,而且还可以塑造未来的行为。
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作为一名精神病学家,我聆听了数以万计的病人的故事,我已经确信,我们讲述个人故事的方式是心理健康的标志和预测因素。
那些讲述自己经常是受害者,很少对不良结果负责的病人,往往身体不舒服,而且一直不舒服。他们忙于指责他人,而无暇顾及自己的康复工作。相比之下,当我的病人开始讲述准确描述自己责任的故事时,我知道他们正在好转。
受害者叙事反映了一种更广泛的社会趋势,即我们都容易把自己看作是环境的受害者,应该为自己的痛苦得到补偿或奖励。即使人们受到了伤害,如果叙述从未超越受害者的身份,就很难发生愈合。
好的心理治疗的工作之一是帮助人们讲述治愈的故事。如果自传式叙事是一条河流,那么心理治疗就是绘制这条河流的手段,在某些情况下还会改变路线。
治愈的故事与现实生活中的事件紧密相连。寻求和发现真相,或用手头的数据尽可能地接近真相,使我们有机会获得真正的洞察力和理解,这反过来又使我们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现代的心理治疗实践有时达不到这个崇高的目标。作为心理健康护理人员,我们已经被同理心的实践所吸引,以至于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没有责任感的同理心是缓解痛苦的短视尝试。如果治疗师和病人重新创造了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病人永远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受害者,那么很有可能病人会继续受害。
但是,如果治疗师能够帮助病人承担起责任,如果不是对事件本身负责,而是对他们在此时此刻的反应负责,那么病人就有能力在生活中继续前进。
在这一点上,AA的哲学和教义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AA的杰出座右铭之一,经常以粗体字印在其宣传册上,就是 “我负责”。
除了责任,匿名戒酒会还强调 “严格的诚实 “是其哲学的核心戒律,而这些理念是相辅相成的。AA的12个步骤中的第四个步骤要求成员进行 “搜索和无畏的道德盘点”,在这个过程中,个人要考虑自己的性格缺陷以及这些缺陷是如何导致问题的。第五步是 “忏悔步”。这是AA成员 “向上帝、向我们自己、向另一个人承认我们错误的确切性质 “的地方。这种直截了当的、实用的、系统的方法可以产生强大的、变革性的影响。
我三十多岁时在斯坦福大学接受精神病学住院医师培训时亲身经历过这种情况。
我的心理治疗主管和导师,也就是我在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戴着Fedora的人,建议我尝试12个步骤,作为解决我对母亲的怨恨的一种方式。他早在我之前就意识到,我是以一种反刍和上瘾的方式紧紧抓住我的愤怒。我之前花了几年时间接受心理治疗,试图弄清我和她的关系,其结果似乎只是助长了我对她的愤怒,因为她不是我希望的母亲,也不是我认为自己需要的母亲。
通过慷慨的自我披露,我的主管与我分享了他几十年来从酒瘾中恢复过来的经历,而AA和12步法帮助他达到了这个目的。虽然我的问题不是酒瘾本身,但他本能地感觉到12步骤会帮助我,他同意陪我一起完成。
我和他一起完成了这些步骤,这次经历确实是一种转变,尤其是第四和第五步。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我不再关注我认为母亲让我失望的方式,而是考虑我对我们紧张的关系有什么贡献。我专注于最近的互动,而不是童年的事件,因为我在童年时期的责任较小。
起初,我很难看出我是如何造成这个问题的。我真的认为自己在所有方面都是无助的受害者。我执着于她不愿意去我家看我,也不愿意与我的丈夫和孩子建立关系,与此相反,她与我的兄弟姐妹和他们的孩子关系更密切。我憎恨我所认为的她不能接受我这个人,我感觉她希望我成为一个不同的人–一个更温暖、更柔韧、更自我、更不自立、更有趣的人。
但后来我开始参与痛苦的过程,写下……是的,在纸上写下,从而使它变得非常真实,我的性格缺陷和那些导致我们紧张关系的方式。正如埃斯库罗斯所说,“我们必须受苦,受苦成真”。
事实是,我很焦虑和恐惧,尽管很少有人会猜到我的这些情况。我保持着严格的时间表,可预测的常规,以及对我的待办事项清单的严格遵守,以此来管理我的焦虑。这意味着其他人常常被迫屈从于我的意志和我的目标的紧迫性。
做母亲,虽然是我生命中最有价值的经历,但也是最令人焦虑的。因此,当我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的防卫和应对方式达到了新的高度。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在那段时间里,任何人来我们家都不会感到愉快,包括我自己的母亲。我一直紧紧抓住我们家的运作,当我觉得事情不对劲时,我就会变得非常焦虑。我不遗余力地工作,很少或根本没有时间为自己、为朋友和家人或为娱乐。事实上,在那些日子里,我没有什么乐趣,除了,我希望,和我的孩子们在一起。
至于我对母亲的怨恨,因为她想让我变得和以前不一样,我突然清楚地意识到,我对她也犯了同样的毛病。我拒绝接受她的本来面目,而是希望她成为某种特蕾莎修女,降临到我们家,以我们需要的方式照顾我们所有人,包括我的丈夫和孩子。
通过要求她达到一些我认为母亲和祖母应该有的理想化愿景,我只能看到她的缺点,而看不到她的优点,而她有很多优点。她是一个有天赋的艺术家。她很有魅力。她可以很风趣,也可以很古怪。她有一颗善良的心,只要她不觉得被评判或被抛弃,就会有奉献的天性。
经过努力,我能够更清楚地看到这些事情的真相,因此,我的怨恨也随之解除。我从对我母亲的愤怒的沉重负担中解脱出来。多么令人欣慰啊
我自己的痊愈促进了我与她关系的改善。我对她的要求少了,宽容多了,,对她的评价也少了。我也开始意识到我们之间的摩擦所带来的许多积极因素,即我的韧性和自立能力,如果我和她的关系更融洽,我可能不会这样。
我现在继续努力在我的所有关系中实践这种讲真话的做法。我并不总是成功,而且本能地想把责任推给别人。但是,如果我很自律和勤奋,我意识到我也有责任。当我能够到达那个地方,向自己和他人讲述真实的版本时,我就会体验到一种正确和公平的感觉,使世界有了我渴望的秩序。
-
真实的自传式叙述进一步让我们在当下更加真实、自发和自由。
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 “假我 “的概念。根据温尼科特的观点,假自我是一种自我构建的角色,以抵御不可容忍的外部需求和压力。温尼科特推断,假自我的产生会导致深刻的空虚感。没有那里。
社交媒体使我们更容易,甚至鼓励我们策划远离现实的生活叙事,从而助长了虚假自我的问题。
在他的网络生活中,我的病人托尼,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每天早上跑步看日出,整天从事建设性和雄心勃勃的艺术工作,并获得了许多奖项。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他,几乎不能起床,强迫性地在网上看色情内容,努力寻找有报酬的工作,并且孤立、抑郁和有自杀倾向。在他的Facebook页面上,几乎看不到他真实的日常生活。
当我们的生活经验与我们的预测形象相背离时,我们很容易感到脱离和不真实,就像我们所创造的虚假形象一样虚假。精神病学家把这种感觉称为去现实 *化和去人格化。*这是一种可怕的感觉,通常会导致自杀的想法。毕竟,如果我们不觉得自己是真实的,那么结束我们的生命就会觉得无足轻重。
虚假自我的解毒剂是真实的自我。激进的诚实是达到这一目的的一种方式。它将我们与我们的存在联系起来,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感到真实。它也减少了维持所有这些谎言所需的认知负荷,释放出精神能量,让我们更自发地生活在当下。
当我们不再努力呈现一个虚假的自我时,我们对自己和他人就会更加开放。正如精神病学家马克-爱泼斯坦(Mark Epstein)在他的《继续存在》(Going on Being)一书中写到他自己走向真实的旅程:“我不再努力管理我的环境,我开始感到振奋,找到一种平衡,允许,与自然界的自发性和我自己的内在自然相联系的感觉。”
说真话是会传染的……撒谎也是如此
2013年,我的病人玛丽亚正处于酗酒问题的高峰期。她经常到当地的急诊室就诊,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法定限度的四倍。她的丈夫迭戈承担了照顾她的大部分工作。
与此同时,他正在与自己的食物成瘾作斗争。他身高五英尺一英寸,体重为336磅。只有当玛丽亚停止饮酒时,迭戈才有动力去解决他的食物成瘾。
“他说:“看到玛丽亚进入康复期,“激励我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改变。当玛丽亚喝酒时,我逃脱了很多。我知道我正在走向一个糟糕的地方。我对自己的身体没有安全感。但是,正是她的戒酒让我变得积极。我可以看出她正在走向一个好的地方,而我不想被抛在后面。
“所以我买了一个Fitbit。我开始去健身房。我开始计算卡路里……只是计算卡路里让我意识到我吃了多少。然后我开始了酮症饮食和间歇性禁食。我不会让自己在深夜或早上吃东西,直到我锻炼完。我跑步。我举重了。我意识到饥饿是一种我可以忽略的通知。今年[2019年]我的体重为195磅。很久以来,我第一次有了正常的血压”。
在我的临床实践中,我经常看到一个家庭中的一个成员从毒瘾中恢复过来,然后很快就有另一个家庭成员也这样做。我见过丈夫戒酒后,妻子也不再有外遇。我见过父母停止吸食大麻后,孩子也会这样做。
-
我曾经提到过1968年斯坦福大学的棉花糖实验,在这个实验中,年龄在3到6岁之间的儿童,研究他们延迟满足的能力。他们被单独留在一个空荡荡的房间里,盘子里放着一块棉花糖,并被告知如果他们能整整15分钟不吃那块棉花糖,他们将得到那块棉花糖和第二块。如果他们能够等待,他们将得到双倍的奖励。
2012年,罗切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在一个关键方面改变了1968年斯坦福大学的棉花糖实验。一组儿童在进行棉花糖试验之前经历了一次违背承诺的行为。研究人员离开了房间,并说当孩子按铃时他们会回来,但后来并没有。另一组儿童被告知同样的情况,但是当他们按铃时,研究人员就回来了。
在后一组中,研究人员回来了,与违背承诺组的孩子相比,他们愿意为第二个棉花糖多等四次(12分钟)。
-
我们怎么能理解为什么玛丽亚从酒瘾中恢复过来,激励迭戈解决他的食物问题;或者为什么当成年人遵守对孩子的承诺时,这些孩子能够更好地调节他们的冲动?
我理解这一点的方法是区分我所说的充足与稀缺心态。讲真话会使人产生"富足 “心态。撒谎则会产生匮乏的心态。我来解释一下。
当我们周围的人是可靠的,并告诉我们真相,包括遵守他们对我们的承诺,我们对这个世界和我们自己在其中的未来感到更加自信。我们觉得我们不仅可以依靠他们,还可以依靠这个世界成为一个有序的、可预测的、安全的地方。即使在匮乏的情况下,我们也感到有信心,事情会好起来的。这是一种富足的心态。
当我们周围的人撒谎,不遵守他们的承诺时,我们就会对未来感到没有信心。世界变成了一个危险的地方,无法依靠有序、可预测或安全。我们进入竞争性的生存模式,倾向于短期收益而不是长期收益,与实际的物质财富无关。这是一种匮乏的心态。
神经科学家沃伦-比克尔(Warren Bickel)和他的同事做了一个实验,研究参与者在阅读了一段预测富足状态和匮乏状态的叙述后,对延迟满足金钱奖励的倾向的影响。
大量的叙述是这样的。“在你的工作中,你刚刚被提升。你将有机会搬到你一直想住的国家的一个地方,或者你可以选择留在你现在的地方。无论哪种方式,公司都会给你一大笔钱来支付搬家费用,并告诉你不花钱的地方可以留着。你的收入将比以前多出百分之百”。
稀缺性的叙述是这样的。“你已经,刚刚被你的工作解雇。你现在不得不搬到一个住在你不喜欢的地方的亲戚家,你将不得不花掉你所有的积蓄来搬到那里。你没有资格领取失业金,所以在你找到另一份工作之前,你将没有任何收入。”
研究人员发现,毫不奇怪,阅读稀缺性叙述的参与者不太愿意等待遥远的未来回报,而更有可能现在就想要得到奖励。而那些读了大量叙述的人则更愿意等待他们的奖励。
直观地说,当资源稀缺时,人们会更多地投资于眼前的收益,而不太相信这些回报在某个遥远的未来仍然会出现。
问题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生活在物质资源丰富的富裕国家,但在日常生活中却以匮乏的心态行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拥有太多的物质财富和拥有太少的财富一样糟糕。多巴胺超载损害了我们延迟满足的能力。社交媒体的夸张和 “后真相 “政治(让我们称其为谎言)放大了我们的稀缺感。其结果是,即使在丰富的环境中,我们也会感到贫穷。
正如有可能在富足中拥有匮乏的心态一样,也有可能在匮乏中拥有富足的心态。富足的感觉来自于物质世界之外的一个来源。相信或努力实现我们自己以外的东西,并培养丰富的人类联系和意义的生活,可以作为社会胶水,让我们即使在赤贫中也有丰富的心态。寻找联系和意义需要彻底的诚实。
讲真话就是预防
“让我先解释一下我的角色,“我对德雷克说,他是我们的职业福利委员会要求我评估的一名医生。
“我来这里是为了确定你是否可能有对你行医能力产生不利影响的精神疾病,以及是否有必要为你的工作提供任何合理的便利。但我希望你在今天的评估之后还能把我看作是一种资源,如果你需要心理健康治疗或更广泛的情感支持。
“谢谢你,“他说,看起来很轻松。
“我知道你得了酒驾?”
DUI,或在影响下驾驶,是一种法律上的违规行为,即在醉酒的情况下操作车辆。在美国,对于21岁或以上的司机来说,血液中酒精浓度(BAC)达到或超过0.08%的情况下驾驶是非法的。
“是的,十多年前,当我在医学院的时候。”
“嗯,我很迷惑。你为什么现在要见我?通常情况下,我被要求在医生得到酒驾后立即评估他们的做法。”
“我是这里的新教员。我在我的申请表上报告了酒后驾车的情况。我猜他们[福利委员会]只是想确保一切正常。”
“我想这是有道理的,“我说。“好吧,告诉我你的故事。”
-
2007年,德雷克正处于医学院第一年的第一学期。他从加利福尼亚开车到东北部,用太平洋沿岸被太阳晒过的草原换取新英格兰地区色彩斑斓的起伏山峦,在所有的秋天都是如此。
他很晚才决定从医,在加州完成本科学习后的一段时间,在那里他实际上主修冲浪,并花了一个学期住在校园后面的树林里,“写坏诗”。
第一次考试后,他的一些医学院同学在乡下的房子里举办了一个派对。计划是由一个朋友来开车,但在最后一刻,这个朋友的车出了问题,所以德雷克最后还是开车。
“我记得那是九月的一个美丽的初秋。房子在一条乡间小路上,离我住的地方不远。”
派对结果比德雷克预期的要有趣。这是他来到医学院后第一次放纵自己。他先是喝了几瓶啤酒,然后又喝了尊尼获加蓝牌。到了晚上11点半,当警察因为邻居报警而出现的时候,德雷克已经喝醉了。他的朋友也是如此。
“我的朋友和我意识到我们喝得太多,无法开车。所以,我们呆在家里。我睡了。警察和其他大多数客人都离开了。我找到一张沙发,想睡一觉。凌晨2点30分,我起来了。我仍然有点醉,但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沿着一条空旷的乡村公路直奔我家。最多两到三英里。我们去了”。
德雷克和他的朋友刚把车开到乡村公路上,就看到一辆警车在路边等着。警察把车停在他们身后,开始跟踪他们,好像他们一直在等他们。他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那里有一个悬挂在一根电线上的信号灯。它在风中被吹动和扭曲。
“我以为是黄灯往我这边闪,红灯往另一边闪,但它那样摆动,很难说。而且,警察就在我身后,我很紧张。我慢慢地穿过十字路口,什么也没发生,所以我想我对黄灯闪烁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我继续前进。再过一个十字路口,就可以左转到我家了。我转了个弯,但忘了打闪光灯,这时警察把我拉了过去。”
这名警察很年轻,和德雷克差不多大。
“他似乎是新来的,几乎是觉得把我拉过去不好,但又不得不这样做。”
他给德雷克做了一个路边清醒测试,并对他进行了呼吸分析。他吹出了0.10%的酒精浓度,刚刚超过法定限度。警官把德雷克带到车站,德雷克在那里填写了一堆文件,并了解到他的执照因受影响驾驶而被暂时吊销。局里有人开车送他回家。
“第二天,我想起了一个传言,说和我一起长大的一个朋友在急诊科住院期间得了酒驾。他是我非常尊敬的人。他曾是我们的班长。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无论你做什么,‘我的朋友在我找到他时说,‘你的记录上不能有酒驾,尤其是作为一名医生。立即找律师,他们会想办法把它降为 “湿性鲁莽 “或完全取消。这就是我所做的。”
德雷克找到一个当地的律师,先付给他5000美元,这是他从学生贷款中取出的钱。
律师对他说:“他们要给你指定一个出庭日期。穿好衣服。看起来不错。法官会叫你上庭,问你如何认罪,你会说’无罪'。就这样。这就是你要做的一切。两个字。'无罪。‘我们将从那里接手。”
在听证会那天,德雷克按要求打扮了一番。他住在离法院几个街区的地方,当他走到那里时,他开始思考。他想到了他在内华达州的表弟,他在醉酒的情况下开车,与对面的一个18岁的女孩迎面相撞。他们都死了。之前在酒吧看到他表弟的人说,他喝得像想死一样。
“在法院,我看到一群与我年龄相仿的其他男人。他们看起来,你知道,比我更没有特权。我在想,他们可能没有像我这样的律师。我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卑鄙。”
一旦进入法庭,等待被传唤,德雷克就像他的律师告诉他的那样,不停地在脑子里运转这个计划。“法官会叫你上台,问你,你怎么认罪,你会说’无罪’。就是这样。这就是你所要做的一切。两个字。‘无罪’。"
法官叫德雷克上证人席。德雷克坐到了法官席下方右侧的硬木椅上。他被要求举起他的右手,保证说实话。他答应了。
他望着法庭上的人们。他看了看法官。法官转身对他说:“你是如何辩护的?”
德雷克知道他应该说什么。他打算说出来。两个字。*无罪。*这些话几乎就在他的嘴唇上。如此接近。
“但后来我想到了我五岁时的这一次,我向我爸爸要冰激凌,他说我必须等到午餐后。我告诉他,‘我吃过午饭了。我去了隔壁的迈克尔家,他给了我一个热狗。但事实是我从未去过迈克尔的家。迈克尔和我并不是真正的朋友,我爸爸知道这一点。好吧,我爸爸没有浪费任何时间。他当时就拿起电话,问迈克尔,‘你给了德雷克一个热狗吗?然后我爸爸让我坐下来,完全冷静,告诉我撒谎总是更糟糕。他说,撒谎永远不值得承担后果。那一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直以来,我都打算为’无罪’辩护,就像律师告诉我的那样。在我出庭作证之前,我并没有做出不同的决定。但在法官问我的那一刻,我说不出话来。我就是说不出来。我知道我是有罪的。我一直在喝酒和开车。”
“有罪,“德雷克说。
法官在椅子上站了起来,仿佛那天早上第一次醒来。慢慢地,他转过头来。他眯着眼睛直视德雷克,钻进他的心里。“你确定这是你的最后答辩吗?你意识到后果了吗?因为你不能再回去了。”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转过头来看着我的样子,“德雷克说。“我觉得他这样问我有点奇怪。我有那么一瞬间想知道我是否犯了一个错误。然后我告诉他我很确定。”
德雷克事后打电话给律师,告诉他发生的事情。“他肯定很惊讶”。
德雷克的律师说,“我尊重你的诚实。我通常不这样做,但我要把你的五千美元送回来。”
而律师做到了。全额退款。
德雷克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参加了强制酒驾课程。这些课程是在偏远的地方。由于他不能开车,他不得不乘坐公交车,每次都要花上几个小时。在强制性的会议上,他与他通常不会接触的人坐在一个圈子里。“与我在医学院时的人有很多不同”。据他回忆,班上的其他人大多是有多次酒驾的老年白人男子。
在支付了1000多美元的罚款和花了几十个小时参加强制酒驾课程后,德雷克拿回了他的驾驶执照。事实证明,这仅仅是个开始。
他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习并申请了住院医师资格,在他所有的住院医师资格申请中报告了酒后驾车的定罪。当他申请医疗执照时,他不得不做同样的事情。当他申请专业委员会认证时也是如此。在这一切结束后,当他在旧金山湾区找到一个住院医师职位时,他得知他在佛蒙特州上的酒驾课程在加州都不算数,所以他不得不重新做一遍。
“我在这些漫长的日子里一直工作到晚上,然后从医院赶到这些会议现场,乘坐公共汽车。如果我迟到一分钟,我就必须支付一笔费用。当时我曾想过,如果我撒谎会不会更好。但现在回头看,我很高兴我说了实话。
“在我成长过程中,我的父母都有酗酒问题。我的父亲仍然如此。他可以连续几周不喝酒,但一旦喝酒,情况就不妙了。我妈妈已经康复十年了,但是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她一直在喝酒,虽然我不知道,也从未见过她喝醉。但即使他们有问题,我的父母也很好,让我觉得我可以对他们开诚布公。
“他们似乎总是对我有爱和自豪感,即使在我行为不端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放纵我。例如,他们从来没有给我钱来支付我的诉讼费,尽管他们有一些钱。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从未评判过我。我认为他们创造了一个舒适和安全的成长空间。这使我能够开放和诚实。
“今天,我自己很少喝酒。我容易做一些过激的事情,我是一个冒险者,所以我绝对可以走这条路。但我认为,在我生命中那个关键的,当我酒驾的时候,说出真相,可能让我走上了另一条路。也许多年来的诚实帮助我对自己更加放心。我没有秘密”。
-
说出真相并承受加速的后果可能改变了德雷克的生活轨迹。他似乎这样认为。他父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灌输给他的对诚实的灼热尊重,似乎比他相当大的成瘾基因负荷影响更大。激进的诚实可能是一种预防措施吗?
德雷克的经历并没有说明在一个腐败和功能失调的系统中,激进的诚实可能会适得其反,也没有说明他的种族和阶级在美国社会中的特权是如何帮助他克服巨大反响的。如果他是穷人和/或有色人种,结果可能会非常不同。
尽管如此,他的故事让我相信,作为父母,我可以而且应该强调诚实是培养孩子的核心价值。
-
我的病人告诉我,诚实可以提高意识,创造更令人满意的关系,使我们对更真实的叙述负责,并加强我们延迟满足的能力。它甚至可以防止未来发展成瘾。
对我来说,诚实是一种日常的斗争。我的一部分人总是想把故事稍微美化一下,让自己看起来更好,或者为不良行为找借口。现在我很努力地与这种冲动作斗争。
虽然在实践中很困难,但这个方便的小工具–说真话–竟然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任何人都可以在任何一天醒来,决定 “今天我不会对任何事情撒谎”。这样做,不仅会使他们的个人生活变得更好,甚至可能改变。
第九章
亲社会的羞耻感
当涉及到强迫性过度消费时,羞耻感是一个固有的棘手概念。它可以是延续行为的工具,也可以是停止行为的动力。那么,我们如何调和这种矛盾呢?
首先,让我们谈谈什么是耻辱。
今天的心理学文献将羞耻感确定为一种有别于内疚的情绪。这种想法是这样的。羞耻感使我们对自己的为人感到难过,而内疚感则使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难过,同时保持一种积极的自我感觉。羞愧是一种不适应的情绪。内疚是一种适应性的情绪。
我对羞愧-内疚二分法的问题是,从经验上看,羞愧和内疚是相同的。在智力上,我可能能够从 “作为一个做错事的好人 “中分离出自我厌恶,但在感到羞愧-内疚的那一刻,一种直击心灵的情绪,这种感觉是相同的:后悔与对惩罚的恐惧和被抛弃的恐惧相混合。遗憾是由于被发现了,可能也可能,不包括对行为本身的遗憾。被遗弃的恐惧,是它自己的惩罚形式,特别强烈。这是一种被抛弃、被回避、不再是群体的一部分的恐惧。
然而,羞愧与内疚的二分法是在挖掘真实的东西。我相信区别不在于我们如何体验这种情绪,而在于其他人如何回应我们的违法行为。
如果别人以拒绝、谴责或回避的方式回应我们,我们就进入了我称之为破坏性羞耻的循环。破坏性的羞耻感会加深羞耻感的情绪体验,并使我们延续当初导致羞耻感的行为。如果其他人的反应是拉近我们的距离,并为我们提供明确的救赎/恢复指导,我们就进入了亲社会性羞耻的循环。亲社会的羞耻感会减轻羞耻感的情绪体验,帮助我们停止或减少可耻的行为。
考虑到这一点,让我们先谈谈什么时候羞耻感会出错(即破坏性羞耻感),作为谈论什么时候羞耻感会正确(即亲社会羞耻感)的前奏。
破坏性的耻辱
我的一位精神病学同事曾对我说:“如果我们不喜欢我们的病人,我们就不能帮助他们。”
当我第一次见到洛里时,我并不喜欢她。
她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很快就告诉我她去那里只是因为她的主治医生让她去的,顺便说一下,这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她从来没有任何形式的成瘾或其他精神健康问题,只是需要,我说了这么多,这样她就可以回到 “真正的医生 “那里去拿药。
她说:“我做了胃绕道手术,“似乎这应该是对她正在服用的危险的高剂量处方药的足够解释。她就像一个老式的女教师,说起话来就像在教训她那不太有天赋的学生。“我以前体重超过两百磅,现在没有了。所以我当然有因肠道改道而产生的吸收不良综合症,这就是为什么我需要120毫克的来士普,只是为了达到普通人的血液水平。你,医生,所有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一点。”
来士普是一种抗抑郁药,可以调节神经递质5-羟色胺。平均每日剂量为10-20毫克,使洛里的剂量至少是正常的六倍。抗抑郁药通常不会被滥用来获取高额利润,但多年来我已经看到了这样的案例。虽然洛里为减肥而接受的Roux-en-Y手术确实会导致对食物和药物的吸收出现问题,但需要这么高的剂量是非常不寻常的。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你是否使用任何其他药物或任何其他物质?”
“我服用加巴喷丁和医用大麻治疗疼痛。我服用安眠药来睡觉。这些都是我的药物。我需要它们来治疗我的病症。我不知道这有什么不对。”
“你在治疗什么病症?“当然,我读过她的病历,知道上面写的是什么,但我总是喜欢听病人对其医疗诊断和治疗的理解。
“我有抑郁症,而且我的脚因旧伤而疼痛。”
“好吧。这很有道理。但剂量很高。我在想,你在生活中是否曾经因为服用超过你计划的物质或药物而挣扎过,或者用食物或药物来应对痛苦的情绪。”
她身体僵硬,背部挺直,双手紧握在膝上,脚踝紧紧交叉。她看起来好像会从椅子上蹦起来,跑出房间。
“我告诉你,医生,我没有这个问题。“她抿了抿嘴唇,然后看向远方。
我叹了口气。“我们换个话题吧,“我说,希望能挽回我们粗糙的开始。“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的生活,就像一本小型自传:你在哪里出生,谁把你养大,你小时候是什么样子,主要的人生里程碑,一直到今天。”
一旦我了解了一个病人的故事–塑造他们的力量造就了我眼前的这个人–敌意就会在同理心的温暖中烟消云散。真正理解一个人就是关心他们。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教导我的医科学生和住院医生–他们急于将经验解析为 “当前疾病史”、“精神状态检查 “和 “系统回顾 “等不连续的方框,就像他们被教导要做的那样–转而专注于故事。故事不仅再现了病人的人性,也再现了我们的人性。
-
罗瑞在20世纪70年代在怀俄明州的一个农场长大,是她父母抚养的三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她记得在很小的时候就觉得自己与众不同。
“我有些不对劲。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我感到很尴尬,不适应。我有语言障碍,口齿不清。我一生都觉得自己很愚蠢。“洛里显然是个聪明人,但我们早期的自我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很大的比重,挤掉了所有相反的证据。
她记得自己很害怕她的父亲。他很容易发怒。但在他们家,更大的威胁是惩罚性上帝的幽灵。
“在成长过程中,我知道有一个令人讨厌的上帝。如果你不完美,你就会下地狱”。因此,告诉自己她是完美的,或者至少比其他人更完美,成为她一生中的一个重要主题。
罗莉是一个普通的学生和一个高于平均水平的运动员。她创造了初中100米跨栏的记录,并开始梦想着参加奥运会。但在她高中三年级时,她在跑跨栏时摔断了脚踝。她需要做手术,而她刚刚开始的跑步生涯实际上已经结束。
“我唯一擅长的东西被夺走了。那是我开始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在麦当劳停下来,我可以吃两个巨无霸。我为此感到自豪。当我上大学时,我不再关心我的外表。大一的时候,我的体重是125磅。当我毕业并进入医学技术学校时,我的体重是180磅。我也开始尝试使用毒品:酒精、大麻、药片……主要是维柯丁。但我选择的药物始终是食物。”
接下来的15年里,洛丽的生活充满了流浪的痕迹。城镇到城镇,工作到工作,男朋友到男朋友。作为一名医疗技术员,几乎在任何一个的城镇都很容易找到工作。萝莉生活中唯一不变的是,无论她住在哪里,她每周日都去教堂。
在这段时间里,她用食物、药片、酒精、大麻,任何她能得到的东西来逃避自己。在一个典型的日子里,她会在早餐时吃一碗冰淇淋,在工作中吃零食,并在回家后立即服用安眠药。晚餐时,她会再吃一碗冰淇淋、一个巨无霸、一份超大号薯条和一杯健怡可乐,然后再吃两片安眠药和一个 “大方块蛋糕 “作为甜点。有时她在下班时服用安眠药,以获得一个跳跃性的开始,这样她在回家时就会很兴奋。
“如果我在服用[安眠药]后不让自己睡觉,我就会感到兴奋。然后我在两小时后再吃两颗,我就会变得更兴奋。欣快感。几乎和阿片类药物一样好”。
她会日复一日地重复这个循环或类似的循环。在休假的日子里,她会把安眠药和咳嗽药混在一起,以获得兴奋,或者饮酒至醉,并从事危险的性行为。当洛丽三十多岁的时候,她独自住在爱荷华州的一个镇上的房子里,把闲暇时间花在嗑药和听美国电台主持人和阴谋论者格伦-贝克的话上。
“我开始相信世界末日即将到来。大决战。穆斯林。伊朗人的入侵。我买了一堆装在容器里的气体。我把它们储存在我额外的卧室里。然后我把它们放在天井的篷布下。我买了一把.22口径的步枪。然后我意识到我可以炸掉,所以我开始用容器里的气体填满我的车,直到全部用完。”
在某种程度上,洛丽知道她需要帮助,但她很害怕寻求帮助。她害怕如果她承认她,不是 “完美的基督徒”,人们就会对她产生反感。她偶尔会向教会成员暗示自己的问题,但通过微妙的信息传递,她了解到有些问题是不应该让教徒们分享的。那时,她的体重几乎达到250磅,感觉到一种压抑,并开始怀疑自己是否会死得更好。
“罗瑞,“我说,“当我们从整体上看,无论是食物、大麻、酒精还是处方药,其中一个持久的问题似乎是强迫性的、自我毁灭的过度消费。你认为这公平吗?”
她看着我,没有说什么。然后她开始哭。当她能够说话时,她说:“我知道这是真的,但我不想相信它。我不想听到它。我有一份工作。我有一辆车。我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我以为做胃绕道手术会解决一切问题。我以为减轻体重会改变我的生活。即使当我减掉体重时,我仍然想死。”
我建议洛里可以采取一些不同的途径来获得改善,包括参加戒酒会。
“我不需要这个,“她毫不犹豫地说。“我已经有了我的教堂。”
一个月后,洛里如期回来了。
“我会见了教会的长老们”。
“发生了什么事?”
她看着远方。“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敞开心扉……除了对你。我告诉了他们一切……或几乎一切。我只是把一切都放在那里。”
“还有呢?”
“这很奇怪,“她说。“他们看起来……很困惑。焦虑。好像他们真的不知道该拿我怎么办。他们让我祈祷。他们说会为我祈祷。他们还鼓励我不要和教会的其他成员讨论我的问题。就是这样。”
“这对你来说是怎样的?”
“在那一刻,我感觉到了那个令人羞愧的上帝。我能够引用经文,但我觉得与经文中的慈爱之神没有任何联系。我无法达到那个期望。我没有那么好。所以我不再去教堂。我已经一个月没去了。而你知道吗,似乎没有人注意到。没有人打电话。没有人联系我。没有一个人。”
-
洛丽陷入了破坏性羞耻的循环中。当她试图对教会成员坦诚相待时,她被劝阻不要分享她生活的这一部分,隐晦地告诉她,如果她公开她的挣扎,她会被拒绝或进一步羞辱。她不能冒失去她所拥有的一点社区的风险。但是,将她的行为隐藏起来也使她的羞耻感长期存在,进一步加剧了孤立,所有这些都助长了持续的消费。
研究表明,平均而言,积极参与宗教组织的,其滥用药物和酒精的比率较低。但是,当基于信仰的组织通过回避违法者和/或鼓励保密和谎言的网络,最终站在羞耻方程式的错误一边时,他们就会促成破坏性羞耻的循环。
破坏性的羞耻感是这样的。过度消费导致羞耻,而羞耻又导致群体的回避,或向群体撒谎以避免回避,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进一步的孤立,在循环的过程中促成持续的消费。

破坏性羞辱的解毒剂是亲社会的羞辱。让我们来看看这可能如何发挥作用。
戒酒会是亲社会羞耻感的典范
我的导师曾经告诉我,是什么促使他停止饮酒。我经常回忆起他的故事,因为它说明了羞耻感的双刃刀刃。
到了四十多岁,他每天晚上都会在妻子和孩子睡觉后偷偷喝酒。他在,向他的妻子保证他已经戒酒后,还长期这样做。他为掩饰自己的饮酒而撒的所有小谎,以及饮酒的事实本身,都累积起来,压在他的良心上,这反过来又使他喝得更多。他喝酒是为了羞耻。
有一天,他的妻子发现了他的吸毒行为。“她失望和背叛的眼神让我发誓我再也不喝酒了”。他在那一刻感受到的羞愧,以及他想重新获得妻子的信任和认可的愿望,推动他第一次认真尝试康复。他开始参加匿名酗酒者会议。他认为匿名戒酒会给他带来的主要好处是 “去羞辱的过程”。
他是这样描述的。“我意识到我不是唯一的人。还有其他像我一样的人。还有其他医生也在与酒瘾作斗争。知道我有一个可以去的地方,在那里我可以完全诚实,并且仍然被接受,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重要。它创造了我需要的心理空间,使我能够原谅自己并做出改变。在我的生活中向前迈进”。
亲社会的羞耻感的前提是,羞耻感对于繁荣的社区来说是有用的和重要的。没有羞耻感,社会将陷入混乱。因此,对越轨行为感到羞耻是适当的,是好的。
亲社会的羞耻感是建立在我们都是有缺陷的,能够犯错,需要被原谅的想法之上的。鼓励遵守团体规范的关键是,在不赶走每个人的情况下,有一个羞耻后的 “待办事项 “清单,提供弥补的具体步骤。这就是AA的12个步骤。
亲社会的羞耻循环是这样的。过度消费导致羞耻感,这需要彻底的诚实,并不是像我们看到的破坏性羞耻感那样导致回避,而是导致接受和同情,再加上一系列必要的行动来弥补。其结果是增加归属感和减少消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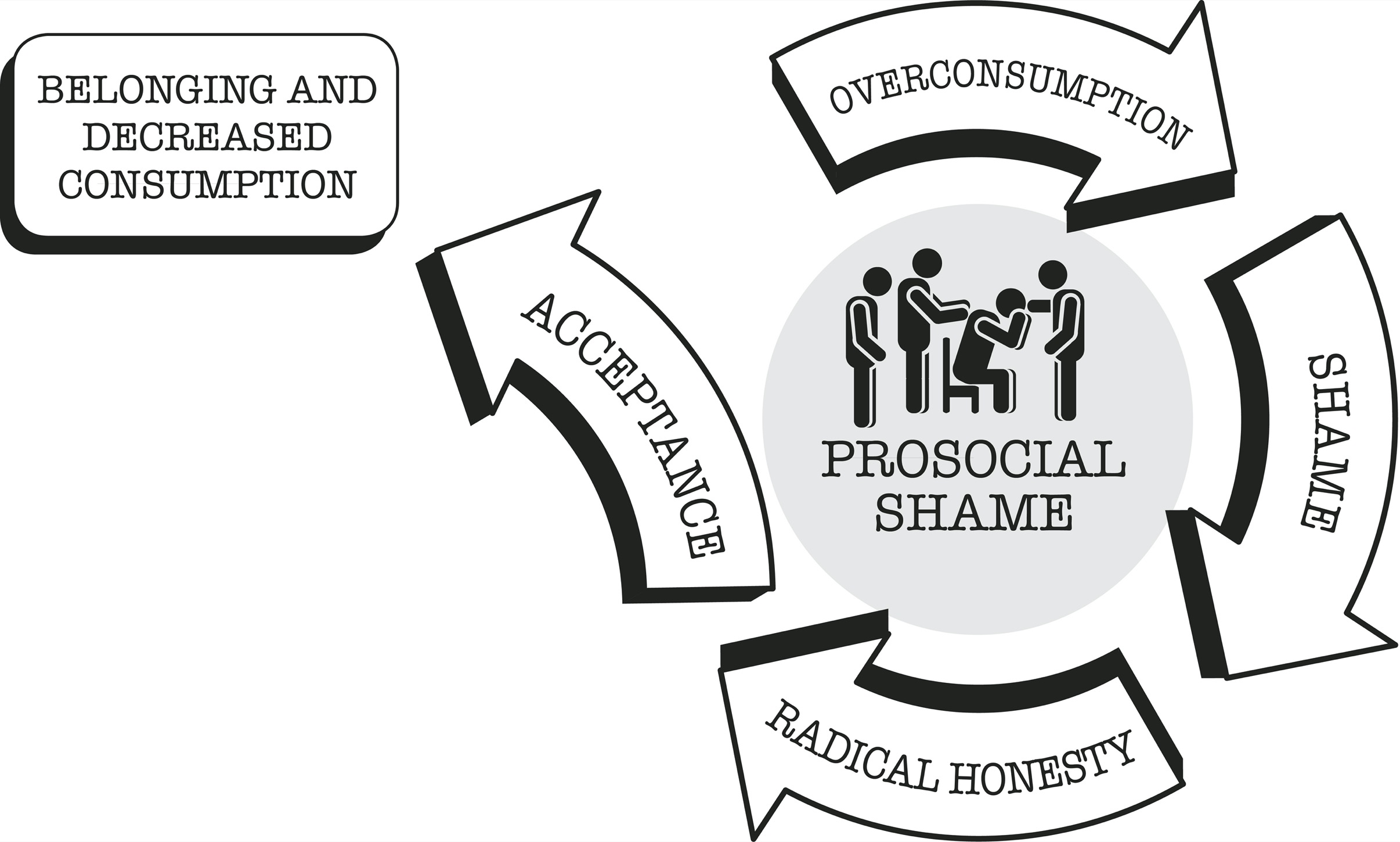
我的病人托德,一位正在戒酒的年轻外科医生,告诉我戒酒会如何 “是第一个表达脆弱的安全场所”。在他的第一次戒酒会上,他哭得很厉害,无法说出自己的名字。
“之后,每个人都走过来,给我他们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打电话。这是我一直想要但从未的社区。我不可能像这样向我的攀岩朋友或其他外科医生敞开心扉。”
经过五年的持续康复,托德与我分享说,12个步骤中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一步是第10步(“继续盘点个人,当我们犯错时及时承认”)。
“每一天,我都会对自己进行检查。*好吧,我是不是扭曲了?如果是,我怎样才能改变它?我是否需要做出补偿?我怎样才能做出补偿?*例如,有一天,我正在处理一个居民,他没有给我关于一个病人的正确信息。我开始感到沮丧。*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当我感到这种挫折感时,我告诉自己。*好吧,托德,停下来。想一想这个问题。这个人的经验几乎比你少十年。他们可能很害怕。与其感到沮丧,你怎么能帮助他们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不是我在进入康复期之前会做的事。
“几年前,“托德告诉我,“在我康复的大约三年时间里,我在监督一个医学生,他的表现非常糟糕。我是说真的很糟糕。我不会让他去照顾病人。到了中期反馈的时候,我和他坐下来,决定坦诚相待。我告诉他:“除非你做出一些重大改变,否则你不可能通过这次轮换。
“在我的反馈之后,他决定重新开始,并真正努力提高自己的表现。他能够变得更好,他最终确实通过了轮换。问题是,在我喝酒的时候,我不会对他诚实。我只会让他继续下去,让他无法通过轮换,或者把问题留给别人去处理。”
真实的自我评估不仅能使我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缺点。它也使我们能够更客观地评价和回应他人的缺点。当我们对自己负责的时候,我们就能对别人负责了。我们可以利用羞辱而不羞辱。
这里的关键是带有同情心的问责制。这些课程适用于我们所有人,无论是否上瘾,并转化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每一种关系。
-
匿名酗酒者协会是一个亲社会羞耻感的示范组织。在戒酒会中,亲社会的羞耻感利用了对团体规范的遵守。作为一个 “酒鬼 “并不羞耻,这与 “AA是一个无羞耻区 “的说法一致;但对 “清醒 “的半心半意的追求是羞耻的。病人告诉我,不得不向团体承认他们已经复发的预期羞耻感是对复发的主要威慑,并促进对团体规范的进一步坚持。
重要的是,当AA会员真的复发时,复发本身就是一种俱乐部商品。行为经济学家把属于一个团体的回报称为俱乐部物品。俱乐部物品越健全,该团体就越有可能维持现有成员并吸引新成员。俱乐部物品的概念可以适用于人类的任何群体,从家庭到友谊团体到宗教团体。
正如行为经济学家Laurence Iannaccone在谈到基于信仰的组织中的俱乐部商品时写道:“我从周日的服务中获得的,不仅取决于我自己的投入,也取决于其他人的投入:有多少人参加,他们如何热情地迎接我,他们唱得如何好,他们如何热情地阅读和祈祷。“俱乐部商品通过积极参与团体活动和聚会,以及遵守团体规则和规范而得到加强。
向AA团契诚实地披露复发情况,可以为其他团契成员创造机会,让他们体验到同理心、利他主义,以及,让我们面对它,某种程度的幸灾乐祸,比如 “这可能发生在我身上,我肯定很高兴它没有发生”,或者 “上帝保佑我”。
俱乐部商品受到自由骑手的威胁,他们试图在没有充分参与该社区的情况下从群体中获益,类似于更通俗的术语freeloaders或moochers。当涉及到团体规则和规范时,当自由人不遵守、撒谎和/或不努力改变他们的行为时,他们就会威胁到社团利益。他们的个人行为对加强社团物品没有任何作用,但他们却从团体成员资格中获得了个人利益–归属感的好处。
Iannaconne指出,即使不是不可能,也很难衡量对创造俱乐部物品的团体原则的遵守情况,特别是当这些要求涉及个人习惯和非物质的主观现象,如讲真话。
Iannaconne的牺牲和污名理论认为,“衡量 “群体参与的一种方式是间接的,即通过规定,污名化的行为,减少在其他背景下的参与,并要求牺牲个人的资源,排除其他活动。这样,免费搭车者就被揪出来了。
特别是,那些在现有宗教机构中看起来过分的、无偿的、甚至是不合理的行为,如留某些发型或某些衣服,禁食各种食物或现代技术形式,或拒绝某些医疗,当被理解为个人为减少组织内的免费搭车而付出的代价时,就是合理的。
你可能会认为,宗教组织和其他社会团体更轻松,规则和约束更少,会吸引更多的追随者。事实并非如此。“更严格的教会 “获得了更多的追随者,并且通常比自由散漫的教会更成功,因为它们清除了免费搭车者,并提供了更强大的俱乐部商品。
雅各布在其康复过程的早期就加入了12步团体 “匿名性瘾者”(SA),并在每次复发时加强参与。这种承诺是非常艰巨的。他每天都亲自或通过电话参加小组会议。他经常每天与其他成员打八个或更多的电话。
戒酒会和其他12步团体被诋毁为 “邪教 “或组织,在这些组织中,人们将他们对酒精和/或毒品的成瘾换成对团体的成瘾。这些批评没有意识到该组织的严格性,其邪教性,可能正是其有效性的来源。
12步团体中的免费搭车者可以有多种形式,但,其中最危险的是那些不承认自己复发的成员,不重新宣布自己是新人,也不重新制定步骤。他们使团体失去了亲社会的耻辱感,更不用说对康复至关重要的清醒的社会网络。为了维护俱乐部的利益,AA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有时似乎是不合理的措施来反对这种搭便车的行为。
琼通过参加戒酒会得以戒酒。她也定期参加聚会,有一个赞助人,自己也赞助别人。她在戒酒会中已经戒酒四年了,而我的病人已经戒酒十年了,所以我能够观察并欣赏戒酒会在她生活中带来的所有积极变化。
琼在21世纪初发生过一次事件,她在不知不觉中使用了酒精。她在语言不通的意大利旅行时,不小心点了一种饮料并饮用了,这种饮料的酒精含量非常小,与在美国市场上销售的无酒精啤酒相当。事后,她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不是因为她觉得被改变了,而是因为她看了标签。
当她从旅行中回来并告诉她的赞助人所发生的事情时,她的赞助人坚持认为她已经复发了,并鼓励她告诉团体并重新设定她的清醒日期。我对琼的赞助人采取如此强硬的立场感到惊讶。毕竟,她喝的酒量微乎其微,大多数美国人都不认为这种饮料是 “酒精”。但琼同意了,尽管她是含泪同意的。她一直保持着她的康复和对AA的参与,直到今天。
琼的赞助人坚持让她重新设定戒酒日期,当时我觉得很过分,但现在我明白了,这既是为了防止一点点酒精变成大量的酒精–滑坡,也是为了团体的更大利益,“效用最大化”。琼愿意遵守对复发的非常严格的解释,加强了她与团体的联系,从长远来看,这对她也是积极的。
另外,琼自己也指出,“也许我有一部分人知道酒里有酒精,想以身处外国为借口”。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团体的功能是一个扩展的良知。
当然,团体思维策略可以被用来达到邪恶的目的。例如,当归属感的成本超过俱乐部的商品,成员受到伤害。NXIVM是一个自称的高管成功计划,其领导人于2018年因联邦性交易和敲诈勒索指控被逮捕和起诉。同样,也有这样的情况:一个团体的成员受益,但他们伤害了团体之外的人,比如今天的各种实体利用社交媒体传播虚假信息。
-
在停止教会活动几个月后,洛丽参加了她的第一次戒酒会。戒酒会提供了她一直在寻找的、但在教会中无法找到的支持性团契,。2014年12月20日,洛丽戒掉了所有物质,并从那时起一直保持着康复状态。
“我不能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或者什么时候发生的,“罗瑞说,多年后回顾自己的康复,她把这归功于她参加了AA。“听到人们的故事。我感到松了一口气,放下了我最深、最黑暗的秘密。看到新来者眼中的希望。我以前是如此孤立无援。我记得我只是想死。晚上躺在床上,为我所做的一切鞭打自己。在戒酒会中,我学会了接受自己和其他人的本来面目。现在我与人有了真正的关系。我属于他们。他们知道真正的我”。
亲社会的羞耻感和养育孩子
作为一个在充斥着多巴胺的世界中担心孩子们的幸福的父母,我一直试图将亲社会的羞耻感的原则纳入我们的家庭生活。
首先,我们已经建立了彻底的诚实作为家庭核心价值。我努力尝试在自己的行为中树立彻底诚实的榜样,但并不总是成功的。有时,作为父母,我们认为通过隐藏我们的错误和不完美,只展示我们最好的自我,我们会教孩子什么是正确的。但这可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导致孩子们觉得他们必须是完美的,才能得到爱。
相反,如果我们对孩子开诚布公地讲述我们的挣扎,我们就会为他们创造一个空间,让他们开诚布公地讲述自己的挣扎。因此,我们也必须准备好,,愿意承认我们在与他们和其他人的互动中的错误。我们必须接受自己的耻辱,并愿意做出补偿。
大约五年前,当我们的孩子还在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我在复活节给他们每人送了一只巧克力兔子。它们是由奶油牛奶巧克力制成的,来自一家专业巧克力店。我的孩子们吃了一点兔子,把剩下的放在储藏室里备用。
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我在这里啃了一点,那里啃了一点他们的巧克力兔子,我想,这还不足以让任何人注意到。当我的孩子们想起他们的巧克力兔子时,我已经把它们削得差不多了。他们知道我对巧克力的亲和力,所以先指责我。
“这不是我,“我说。这个谎言很自然。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继续撒谎。他们坚持怀疑我说的是真的,但后来他们开始互相指责。我知道我必须把它纠正过来。*如果我自己都不诚实,我怎么能教我的孩子诚实?而且撒谎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啊!我花了三天的时间来建立起自己的信心。*我花了三天时间才鼓起勇气告诉他们真相。我感到非常羞愧。
在得知真相后,他们感到欣慰和惊恐。平反的是,他们的第一次猜测是正确的。惊恐的是,他们自己的母亲会对他们撒谎。这对我和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有启发。
我提醒自己,并向他们发出信号,我的缺陷有多深。我还示范说,当我犯错时,我至少可以承担自己的责任。我的孩子们原谅了我,至今还喜欢讲我如何 “偷 “了他们的巧克力,然后 “为此撒谎"的故事。他们的取笑是我的忏悔,我欢迎。我们一起重申,作为一个家庭,我们的家庭是一个人们会犯错误但不会被永久谴责或抛弃的家庭。我们在一起学习和成长。
就像我的病人托德一样,当我们对自己进行积极和诚实的重新评估时,我们就更能也更愿意给别人诚实的反馈,本着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优势和不足的精神。
-
这种彻底的诚实而不羞辱的方式对于教导孩子们的长处和短处也很重要。
当我们的大女儿五岁时,她开始学钢琴。我在一个音乐家庭长大,期待着与我的孩子分享音乐。结果发现我的女儿没有节奏感,虽然不是完全的音盲,但也很接近了。然而,我们都顽强地坚持她的日常练习,我坐在她旁边,试图鼓励她,同时又抑制住我对她完全缺乏能力的惊恐。事实是我们都不喜欢这样。
在她上课的大约一年时间里,我们正在看电影*《快乐的大脚*》,讲述一只企鹅咕哝,他有一个大问题:他不会唱一个音符,在这个世界上,你需要一首心曲来吸引一个灵魂伴侣。我们的女儿在电影看了一半的时候看着我说:“妈妈,我是不是像咕哝一样?”
我在这一刻被父母的自我怀疑牢牢抓住。我该说什么?我是告诉她真相并冒着损害她自尊的风险,还是撒谎并试图利用欺骗来点燃她对音乐的热爱?
我冒了个险。“是的,“我说,“你很像咕哝。”
我女儿的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我把它理解为验证的笑容。我知道当时我做了正确的事情。
在验证她已经知道的事实–她缺乏音乐能力–的过程中,我鼓励她掌握准确的自我评价技能,她至今仍在展示这种技能。我还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不可能样样精通,重要的是要知道你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这样你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
她在一年后决定放弃钢琴课–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而她至今仍喜欢音乐,跟着收音机唱,完全不走调,而且丝毫不觉得难为情。
相互的诚实排除了羞耻感,并预示着亲密关系的爆发,当我们的缺陷被接受时,一种情感上的温暖涌上心头,感觉与他人深深相连。创造我们所渴望的亲密关系的不是我们的完美,而是我们愿意一起工作来补救我们的错误。
这种亲密关系的爆发几乎肯定伴随着我们大脑自身内源性多巴胺的释放。但与我们从廉价的快乐中得到的多巴胺冲动不同,我们从真正的亲密关系中得到的冲动是适应性的、恢复活力的和促进健康的。
-
通过牺牲和成见,我的丈夫和我试图加强我们家庭的俱乐部商品。
我们的孩子直到上了高中才被允许拥有自己的手机。这使他们在同龄人中成为一个异类,尤其是在初中。起初,他们乞求和劝说要有自己的手机,但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把这种差异看作是他们身份的核心部分,还有我们坚持尽可能骑自行车而不是开车,并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一家人一起度过。
我相信我们孩子的游泳教练有一个秘密的行为经济学博士。他经常利用牺牲和污名来加强俱乐部的商品。
首先,是巨大的时间投入,高中生每天要进行长达4个小时的游泳训练,以及当孩子们错过训练时发生的隐性羞辱。对高出勤率的认可和奖励(与戒酒会在30天内参加30次会议的奖励不一样),包括参加旅行比赛的机会。对参加比赛的穿着有严格的规定:周五穿红色游泳T恤,周六穿灰色游泳T恤,只穿团队标志的服装(帽子、套装、护目镜)。这成功地将这支队伍的孩子与其他队伍的孩子的休闲打扮区分开来。
这些规则中有许多似乎是过度的和无偿的,但当从效用最大化原则的角度来看,加强参与,减少免费搭车,增加俱乐部商品,它们是有意义的。而孩子们对这个团队趋之若鹜,特别是,似乎喜欢这种严格性,即使他们在抱怨它。
-
我们倾向于认为羞辱是一种负面的东西,尤其是在羞辱–脂肪羞辱、荡妇羞辱、身体羞辱等等是一个如此沉重的词,并且(正确地)与欺凌相关的时候。在我们越来越多的数字世界中,社交媒体上的羞辱及其相关的 “取消文化 “已经成为一种新的回避形式,是对羞辱的最具破坏性方面的现代扭曲。
即使没有人把矛头指向我们,我们也都准备好把矛头指向自己。
社交媒体通过邀请这么多令人反感的区别,推动了我们的自惭形秽的倾向。我们现在不仅与我们的同学、邻居和同事进行比较,而且与整个世界进行比较,这使得我们很容易说服自己,我们应该做得更多,或得到更多,或只是以不同的方式生活。
为了使我们的生活 “成功”,我们现在觉得我们必须达到史蒂夫-乔布斯和马克-扎克伯格的神话般的高度,或者像Theranos公司的伊丽莎白-霍姆斯,一个后世的伊卡洛斯,在努力中倒下。
但我的病人的生活经验表明,亲社会的羞耻感可以产生积极、健康的影响,它可以抚平一些自恋的粗糙边缘,将我们与我们的支持性社会网络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并遏制我们的成瘾性。
结论
平衡的教训
我们都渴望从世界中获得喘息的机会–从我们经常为自己和他人设定的不可能的标准中解脱出来。我们自然会从自己无情的反思中寻求喘息的机会。我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我不能这样做? 看看他们对我做了什么?我怎么能这样对他们?
因此,我们被任何一种现在可以获得的愉悦的逃避形式所吸引:时髦的鸡尾酒、社交媒体的回声室、狂看真人秀、网络色情之夜、薯片和快餐、沉浸式视频游戏、二流的吸血鬼小说……。这个名单真的是无穷无尽。成瘾的药物和行为提供了这种喘息的机会,但从长远来看却增加了我们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是通过逃离世界来寻求遗忘,而是转向它呢?如果我们不是把世界抛在后面,而是把自己沉浸在其中呢?
穆罕默德,你会记得,是我的病人,他尝试了各种形式的自我束缚来限制他的大麻消费,,却发现自己又回到了起点,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从节制到过度消费再到成瘾。
他到旧金山北部的雷伊角(Point Reyes)自然小径徒步旅行,希望在以前给他带来快乐的活动中找到庇护,因为他再次试图控制他的大麻消费。
但是,每一个转弯都会带来吸食大麻的新鲜记忆,过去的徒步旅行几乎都是在半醉状态下进行的,因此,徒步旅行不是一种逃避,而是变成了一种渴望的痛苦和对损失的痛苦提醒。他对能够解决他的大麻问题而感到绝望。
然后他有了他的 “哈 “的时刻。在一个特定的视野点,他对与朋友一起抽大麻有明确的记忆,他把相机举到眼前,对准附近的植物。他看到一片叶子上有一只虫子,于是将镜头进一步聚焦,放大了甲虫鲜红的甲壳、条纹的触角和凶猛的毛腿。他被迷住了。
他的注意力被他十字准线上的生物所吸引。他拍了一系列照片,然后改变角度,拍了更多。在接下来的徒步旅行中,他停下来给甲虫拍了极近距离的照片。只要他这样做,他对大麻的渴望就会减少。
“我必须强迫自己非常安静,“他在2017年我们的一次会议上告诉我。“我必须达到一个完美的静止状态,才能拍出好的对焦照片。这个过程让我接地气,从字面上看,并让我集中精力。我发现在我的相机末端有一个奇怪的、超现实的、引人注目的世界,可以和我用毒品逃到的。但这是更好的,因为不需要毒品”。
许多个月后,我意识到穆罕默德的康复之路与我的相似。
我做了一个有意识的决定,让自己重新沉浸在病人护理中,专注于我工作中一直以来都很有价值的方面:与病人长期的关系,以及沉浸在作为给世界带来秩序的叙述方式中。这样一来,我就能从强迫性的浪漫主义阅读中走出来,进入一个更有价值和意义的职业。我的工作也更加成功,但我的成功是一个意外的副产品,而不是我所追求的东西。
我敦促你找到一种方法,使自己完全沉浸在你被赋予的生活中。不要再逃避你想要逃避的东西,而是要停下来,转身,面对它。
然后我让你敢于向它走去。通过这种方式,世界可能会向你显示出它是一种神奇的、令人敬畏的东西,不需要逃避。相反,世界可能成为值得关注的东西。
寻找和保持平衡的回报既不是立即的也不是永久的。它们需要耐心和维护。我们必须愿意向前迈进,尽管对前面的情况不确定。我们必须有信心,今天的行动在当下似乎没有影响,但实际上是在向积极的方向积累,这将在未来某个未知的时间向我们揭示。健康的做法一天天发生。
我的病人玛丽亚对我说:“康复就像*《哈利-波特》*中的那个场景,邓布利多走在一条黑暗的小巷里,沿途照亮灯柱。只有当他走到巷子的尽头,停下来回头看时,他才看到整个巷子都被照亮了,那是他进步的光芒。”
我们在这里结束了,但这可能只是一个新方法的开始,即如何对待今天这个被过度麻醉、过度刺激、充满快乐的世界。练习平衡的课程,这样你也可以回过头来看看你进步的光芒。
平衡的教训
- 对快乐的不懈追求(和对痛苦的回避)导致了痛苦。
- 康复始于节制。
- 戒酒可以重置大脑的奖赏途径,随之而来的是我们在更简单的快乐中获得快乐的能力。
- 自我束缚在欲望和消费之间创造了字面和元认知的空间,这在我们多巴胺超载的世界中是一种现代需要。
- 药物治疗可以恢复平衡,但考虑到我们因药物治疗疼痛而失去的东西。
- 按住痛苦的一面,就会把我们的平衡重新调整到快乐的一面。
- 谨防对疼痛上瘾。
- 彻底的诚实可以促进认识,增强亲密关系,并培养一种丰富的心态。
- 亲社会的羞耻感肯定了我们属于人类的部落。
- 与其逃避这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沉浸在这个世界中找到逃避。
作者的说明
本书中的亲密对话和故事是在受访者的知情同意下收录的。为了保护隐私,我已经删除和改变了姓名和其他人口统计学细节,即使参与者愿意不加改动地包括它们。获得同意的过程包括参与者同意以下内容。“如果有人熟悉你并在这里读到你的故事,即使我改变了你的名字,他也可能认出你。你能接受吗?“以及 “如果有任何你不希望我包括的细节,请告诉我,我会把它们。”
笔记
“我们所忽略的当代先知 **"。**Kent Dunnington,Addiction and Virtue: Beyond the Models of Disease and Choice(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Academic, 2011)。这是一部关于成瘾和信仰的精彩神学和哲学论文。
美国阿片类药物的流行 。Anna Lembke,Drug Dealer, MD: How Doctors Were Duped, Patients Got Hooked, and Why It’s So Hard to Stop, 1st ed.(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6)。关于这个话题有很多优秀的书籍,包括《疼痛杀手》。欺骗的帝国和美国阿片类药物流行的起源》,作者巴里-梅尔;《梦境》。美国阿片类药物流行的真实故事》(Sam Quinones);以及《Dopesick:经销商、医生和使美国上瘾的毒品公司》,作者是贝丝-梅西。这些书中的每一本,包括我自己的书,都通过略微不同的视角探讨了阿片类药物流行的起源。
“供应量的巨大扩张 **"。**ASPPH应对阿片类药物危机的公共卫生倡议特别小组,将科学带入阿片类药物。报告和建议,2019年11月。
“反复接触阿片类药物 **"。**ASPPH应对阿片类药物危机的公共卫生倡议特别小组,将科学引入阿片类药物。报告和建议,2019年11月。
禁酒令导致了急剧下降 。Wayne Hall, “What Are the Policy Lessons of National Alcohol Prohib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1920-1933?”,Addiction105, no.7 (2010):1164-73,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0331549/。
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Robert MacCoun,“毒品与法律。禁毒的心理学分析》,《*心理学通报》*113期(1993年6月1日)。497–512,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13.3.497. 对于精神活性药物的禁止、非刑事化和合法化的影响,有相当多的争议和。罗伯-麦克库恩(Rob MacCoun)关于这个话题的著作融合了经济学、心理学和政治哲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可诊断的酒精成瘾上升了50% 。Bridget F. Grant, S. Patricia Chou, Tulshi D. Saha, Roger P. Pickering, Bradley T. Kerridge, W. June Ruan, Boji Huang, et al., “2001-2002年至2012-2013年美国12个月酒精使用、高危饮酒和DSM-IV酒精使用障碍的普遍性。来自全国酒精及相关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美国医学会精神病学》74期,第9期(2017年9月1日)。911–23,https://doi.org/10.1001/jamapsychiatry.2017.2161.
精神疾病是一个风险因素 。安娜-伦布克(Anna Lembke),“是时候放弃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治疗假说了”,《美国药物和酒精滥用杂志》第38期(2012年)。524–29,https://doi.org/10.3109/00952990.2012.694532.
“肢体资本主义 **"。**David T. Courtwright,The Age of Addiction:How Bad Habits Became Big Business(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9),https://doi.org/10.4159/9780674239241。 这是一个扣人心弦和博学的观点,探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化的不同,对成瘾性商品和行为的获取增加是如何促成消费增加的。
卷烟机 。Matthew Kohrman, Gan Quan, Liu Wennan, and Robert N. Proctor, eds.,Poisonous Pandas:批判性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卷烟制造》(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吗啡成瘾 **。David T. Courtwright,“对鸦片和吗啡上瘾”,载于《黑暗天堂》。A History of Opiate Addiction in America(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https://doi.org/10.2307/j.ctvk12rb0.7。 这是历史学家David Courtwright的另一本神奇的书,通过历史追溯阿片类药物流行的起源,包括19世纪末,当时医生经常给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庭主妇等人开吗啡。
薯片和薯条的自动化 **:**国家马铃薯委员会,《2016年马铃薯统计年鉴》,2020年4月18日访问,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0707034920/https://www.nationalpotatocouncil.org/files/7014/6919/7938/NPCyearbook2016_-_FINAL.pdf。
泰式番茄椰子浓汤 **。**安妮-加斯帕罗和杰西-纽曼,“口味的新科学:1000种香蕉口味”,《华尔街日报》,2014年10月31日。另见大卫-T-考特怀特的《*成瘾的时代》。坏习惯如何成为大企业》,*对食品工业的变化进行了出色的、广泛的讨论。
全球领先的死亡风险 **。**Shanthi Mendis, Tim Armstrong, Douglas Bettcher, Francesco Branca, Jeremy Lauer, Cecile Mace, Vladimir Poznyak, Leanne Riley, Vera da Costa e Silva, and Gretchen Stevens,2014年全球非传染性疾病现状报告(世界卫生组织,2014),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148114/9789241564854_eng.pdf。
现在全世界有更多的人……是肥胖的 **。**Marie Ng, Tom Fleming, Margaret Robinson, Blake Thomson, Nicholas Graetz, Christopher Margono, Erin C Mullany, et al., “1980-2013年期间全球、区域和国家儿童及成人超重和肥胖的流行率。201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系统分析》,*《柳叶刀》*384期,第9945期(2014年8月)。766–81,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4)60460-8.
全球死于毒瘾的人数上升 **:**汉娜-里奇和马克斯-罗泽,“毒品使用”,《我们的数据世界》,2019年12月,https://ourworldindata.org/drug-use。
"绝望的死亡 **"。**安妮-凯斯和安格斯-迪顿,《绝望的死亡和资本主义的未来》(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0),https://doi.org/10.2307/j.ctvpr7rb2。
世界的自然资源正在迅速减少 :“资本之痛”,《经济学人》,2020年7月18日。原始资料见https://www.unenvironment.org/resources/report/inclusive-wealth-report-2018, 和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0306261919305215。
“宗教的人诞生了 **"。**菲利普-里夫,《治疗学的胜利》。弗洛伊德之后信仰的使用(纽约:Harper and Row,1966)。
新时代的 “内在上帝 “神学 **。**Ross Douthat,Bad Religion: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异教徒的国家》(纽约:自由出版社,2013年)。
疼痛是健康的 **。**Maricia L. Meldrum, “A Capsule History of Pain Management,"JAMA290, no. 18 (2003):2470–75,https://doi.org/10.1001/jama.290.18.2470.
手术期间的阿片类药物 **。**Victoria K. Shanmugam, Kara S. Couch, Sean McNish, and Richard L. Amdur, “Relation between Opioid Treatment and Rate of Healing in Chronic Wounds,"Wound Repair and Regeneration25, no. 1 (2017):120–30,https://doi.org/10.1111/wrr.12496.
“自然界所使用的工具 **"。**Thomas Sydenham, “A Treatise of the Gout and Dropsy,” inThe Works of Thomas Sydenham, M.D., on Acute and Chronic Diseases(London, 1783), 254,https://wellcomecollection.org/works/xusf5q4r/items?canvas=349.
大量开出感觉良好的药片 **。**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物质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行为健康,美国,2012年”,HHS出版物编号(SMA)13-4797,2013年,http://www.samhsa.gov/data/sites/default/files/2012-BHUS.pdf。
每二十个美国儿童中就有一个 **。**Bruce S. Jonas, Qiuping Gu, and Juan R. Albertorio-Diaz, “Psychotropic Medication Use among Adolescents:美国,2005-2010年,"NCHS数据简报,第135期(2013年12月)。1-8.
像Paxil、Prozac和Celexa这样的抗抑郁药的使用正在上升 **。**经合组织,《经合组织卫生统计》,2020年7月,http://www.oecd.org/els/health-systems/health-data.htm。 Laura A. Pratt, Debra J. Brody, Quiping Gu, “12岁及以上人群中抗抑郁药的使用。United States, 2005-2008,"*NCHS Data Brief No. 76,*October 2011,https://www.cdc.gov/nchs/products/databriefs/db76.htm.
兴奋剂的处方(Adderall, Ritalin) 。Brian J. Piper, Christy L. Ogden, Olapeju M. Simoyan, Daniel Y. Chung, James F. Caggiano, Stephanie D. Nichols, and Kenneth L. McCall, “Trends in Use of Prescription Stimul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erritories, 2006 to 2016, “PLOS ONE13, no. 11 (2018),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6100.
苯二氮卓类药物(Xanax、Klonopin、Valium),也会让人上瘾,正在上升 **。**Marcus A. Bachhuber, Sean Hennessy, Chinazo O. Cunningham, and Joanna L. Starrels, “Increasing Benzodiazepine Prescriptions and Overdose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6-2013,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106, no.4 (2016):686–88,https://doi.org/10.2105/AJPH.2016.303061.
“对分心的无限胃口 **"。**Aldous Huxley,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
“美国人不再相互交谈,而是相互娱乐 **"。**尼尔-波兹曼,《把我们自己逗死》。演艺界时代的公共话语》(纽约:企鹅出版社,1986)。
世界幸福报告》 **。**John F. Helliwell, Haifang Huang, and Shun Wang, “Chapter 2-Changing World Happiness, “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19 , March 20, 2019, 10-46.
较富裕国家的焦虑率较高 **。**Ayelet Meron Ruscio, Lauren S. Hallion, Carmen C.W. Lim, Sergio Aguilar-Gaxiola, Ali Al-Hamzawi, Jordi Alonso, Laura Helena Andrade, et al., “Cross-Sec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Epidemiology ofDSM-5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across the Globe, “JAMA Psychiatry74, no.5 (2017):465–75,https://doi.org/10.1001/jamapsychiatry.2017.0056.
全世界的抑郁症患者增加了50% **。**刘青青、何海荣、杨进、冯晓杰、赵凡凡和柳俊,“1990年至2017年全球抑郁症负担的变化。来自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发现》,《精神病学研究杂志》126(2019年6月)。134–40,https://doi.org/10.1016/j.jpsychires.2019.08.002.
身体的疼痛也在增加 **。**David G. Blanchflower和Andrew J. Oswald,“现代美国的不快乐和痛苦。A Review Essay, and Further Evidence, on Carol Graham’s Happiness for All?IZA劳动经济研究所讨论文件,2017年11月。
一个空前富裕的时代 **。**Robert William Fogel,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凯瑟琳-蒙塔古,位于伦敦以外 **。**Kathleen A. Montagu,“大鼠组织和不同动物大脑中的儿茶酚化合物”,*《自然》*180(1957)。244–45,https://doi.org/10.1038/180244a0.
渴望 多于 喜欢 **。**布莱恩-阿迪诺夫,“药物奖励和成瘾的神经生物学过程”,《哈佛精神病学评论》12,第6期(2004)。305–20,https://doi.org/10.1080/10673220490910844.
无法制造多巴胺的小鼠 **。**Qun Yong Zhou and Richard D. Palmiter, “Dopamine-Deficient Mice Are Severely Hypoactive, Adipsic, and Aphagic,"Cell83, no. 7 (1995):1197–1209,https://doi.org/10.1016/0092-8674(95)90145-0.
对于盒子里的老鼠来说,是巧克力 **。**Valentina Bassareo和Gaetano Di Chiara,“食欲刺激引起的中枢多巴胺传递的调控及其与动机状态的关系”,《欧洲神经科学杂志》11,第12期(1999)。4389–97,https://doi.org/10.1046/j.1460-9568.1999.00843.x.
性的百分之百 **。**Dennis F. Fiorino, Ariane Coury, and Anthony G. Phillips, “Dynamic Changes in Nucleus Accumbens Dopamine Efflux during the Coolidge Effect in Male Rats,"Journal of Neuroscience17, no. 12 (1997):4849–55,https://doi.org/10.1523/jneurosci.17-12-04849.1997.
尼古丁的150% **。**Gaetano Di Chiara和Assunta Imperato,“人类滥用的药物优先增加自由活动大鼠中脑系统的突触多巴胺浓度”,*《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85,第14期(1988年)。5274–78,https://doi.org/10.1073/pnas.85.14.5274.
重叠的大脑区域 **。**Siri Leknes和Irene Tracey, “A Common Neurobiology for Pain and Pleasure,"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9, no.4 (2008):314–20,https://doi.org/10.1038/nrn2333.
“偏离享乐主义或情感中立性 **"。**Richard L. Solomon 和 John D. Corbit, “An Opponent-Process Theory of Motiv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8, no. 6 (1978):12-24.
阿片类药物引起的痛觉减退 **:**Yingghui Low, Collin F. Clarke, and Billy K. Huh, “阿片类药物引起的痛觉减退。A Review of Epidemiology, Mechanisms and Management,"Singapore Medical Journal53, no.5 (2012):357-60.
当这些病人逐渐停止使用阿片类药物时 **。**Joseph W. Frank, Travis I. Lovejoy, William C. Becker, Benjamin J. Morasco, Christopher J. Koenig, Lilian Hoffecker, Hannah R. Dischinger, et al., “Dose Reduction or Discontinuation of Long-Term Opioid Therapy的病人结果。A Systematic Review,"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167, no.3 (2017):181–91,https://doi.org/10.7326/M17-0598.
“奖励电路的敏感性下降 **"。**Nora D. Volkow, Joanna S.Fowler, and Gene-Jack Wang, “Role of Dopamine in Drug Reinforcement and Addiction in Humans:成像研究的结果”,《行为药理学》13,第5期。5 (2002):355–66,https://doi.org/10.1097/00008877-200209000-00008.
“抑郁症驱动的复发 **"。**George F. Koob, “Hedonic Homeostatic Dysregulation as a Driver of Drug-Seeking Behavior,"Drug Discovery Today:疾病模型5, no.4 (2008):207–15,https://doi.org/10.1016/j.ddmod.2009.04.002.
赌博成瘾 **。**Jakob Linnet, Ericka Peterson, Doris J. Doudet, Albert Gjedde, and Arne Møller, “Dopamine Release in Ventral Striatum of Pathological Gamblers Los Money, “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122, no.4 (2010):326–33,https://doi.org/10.1111/j.1600-0447.2010.01591.x.
经验依赖的可塑性 *。*Terry E. Robinson和Bryan Kolb,“与接触滥用药物有关的结构可塑性”,Neuropharmacology47, Suppl.1 (2004):33–46,https://doi.org/10.1016/j.neuropharm.2004.06.025.
大鼠的学习能力 **。**Brian Kolb, Grazyna Gorny, Yilin Li, Anne-Noël Samaha, and Terry E. Robinson, “Amphetamine or Cocaine Limits the Ability of Later Experience to Promote Structural Plasticity in the Neocortex and Nucleus Accumben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States America 100, no. 18 (2003):10523–28,https://doi.org/10.1073/pnas.1834271100.
新的突触途径来创造健康的行为。 Sandra Chanraud, Anne-Lise Pitel, Eva M. Muller-Oehring, Adolf Pfefferbaum, and Edith V. Sullivan, “Remapping the Brain to Compensate for Impairment in Recoverying Alcoholics,"Cerebral Cortex23 (2013):97-104,https://doi.org/10.1093/cercor/bhr381; Changhai Cui, Antonio Noronha, Kenneth R. Warren, George F. Koob, Rajita Sinha, Mahesh Thakkar, John Matochik, et al., “Brain Pathways to Recovery from Alcohol Dependence, “Alcohol49, no.5 (2015):435–52.https://doi.org/10.1016/j.alcohol.2015.04.006.
光遗传学 **。**Vincent Pascoli, Marc Turiault, and Christian Lüscher, “Reversal of Cocain-Evoked Synaptic Potentiation ResetsDrug-Induced Adaptive Behaviour, “Nature481 (2012):71–75,https://doi.org/10.1038/nature10709.
“一张通往安全的门票 **"。**亨利-比彻,“战斗中受伤的人的疼痛”,《麻醉与镇痛》,1947年,https://doi.org/10.1213/00000539-194701000-00005。
脚先踩在15厘米长的钉子上 **。**J. P. Fisher, D. T. Hassan, and N. O’Connor, “Case Report on Pain,"British Medical Journal310, no. 6971 (1995):70,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548478/pdf/bmj00574-0074.pdf。
“我们是雨林中的仙人掌 **"。**汤姆-菲纽肯博士是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学教授,我在那里以客座教授身份讲课时接触到他的作品。正是在与他的一些学生共进晚餐时,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我知道我必须找到一种方法将其纳入这本书中。
多巴胺传输仍低于正常水平 。Nora D. Volkow, Joanna S.Fowler, Ke-Jack Wang, and James M. Swanson, “Dopamine in Drug Abuse and Addiction:成像研究结果和治疗意义》,《*分子精神病学》*第9期,第6期(2004年6月)。557–69,https://doi.org/10.1038/sj.mp.4001507.
不喝酒一个月后 **。**Sandra A. Brown和Marc A. Schuckit,《戒酒者的抑郁症变化》,《酒精研究杂志 》第49期。5 (1988):412-17,https://pubmed.ncbi.nlm.nih.gov/3216643/。
抑郁症的标准治疗方法 。Kenneth B. Wells, Roland Sturm, Cathy D. Sherbourne, and Lisa S. Meredith,Caring for Depress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以有控制的方式使用他们选择的药物 **。**马克-B-索贝尔和琳达-C-索贝尔,“25年后有控制的饮酒。大辩论有多重要?"瘾君子90,第9期(1995)。1149-53.Linda C. Sobell, John A. Cunningham, and Mark B. Sobell, “通过和不通过治疗从酒精问题中恢复。两个人口调查的流行率,"美国公共卫生杂志86,第7期(1996)。966-72.
禁欲违规效应 。Roelof Eikelboom和Randelle Hewitt,“大鼠间歇性获得蔗糖溶液导致长期消费增加”,《生理学与行为》165(2016)。77–85,https://doi.org/10.1016/j.physbeh.2016.07.002.
他们一有机会就会狂饮 **。**Valentina Vengeliene, Ainhoa Bilbao, and Rainer Spanagel, “研究复发行为的酒精剥夺效应模型。大鼠和小鼠之间的比较”,《酒精》第48期。3 (2014):313–20,https://doi.org/10.1016/j.alcohol.2014.03.002.
自我束缚 是描述的术语 **。**我第一次接触到自我束缚这个词是在萨利-萨特尔和斯科特-O-利连菲尔德的这篇文章中。萨利-萨特尔和斯科特-O-利连菲尔德,“成瘾和大脑疾病谬论”,《精神病学前沿》4(2014年3月)。1–11,https://doi.org/10.3389/fpsyt.2013.00141. 我喜欢萨特尔的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在这里她用自我约束来强调 “个人机构在延续使用和复发的循环中的巨大作用”。但我不同意这篇文章的基本前提,它认为我们自我约束的能力反驳了成瘾的疾病模型。对我来说,我们对自我约束的需求说明了成瘾的强大拉力和随之而来的大脑变化,与疾病模型一致。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Thomas Schelling)也谈到了自我约束的概念,但称其为 “自我管理 “和 “自我命令”。“Self-Command in Practice, in Policy, and in a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no. 2 (1984):1-11,https://econpapers.repec.org/article/aeaaecrev/v_3a74_3ay_3a1984_3ai_3a2_3ap_3a1-11.htm。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syt.2013.00141/full。
纳曲酮半小时前 。J. D. Sinclair,“关于使用纳曲酮的证据以及在酒精中毒治疗中使用纳曲酮的不同方式,"酒精和酒精中毒36,第1期(2001年)。2–10,https://doi.org/10.1093/alcalc/36.1.2.
北京的戒毒医院 **。**Anna Lembke和Niushen Zhang, “A Qualitative Study of Treatment-Seeking Heroin Us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Addiction Science & Clinical Practice10, no. 23 (2015),https://doi.org/10.1186/s13722-015-0044-3.
对酒精产生的类似双硫仑的反应 **。**Jeffrey S. Chang, Jenn Ren Hsiao, and Che Hong Chen, “ALDH2多态性和亚洲人的酒精相关癌症。A Public Health Perspective,"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24, no. 19 (2017):1–10,https://doi.org/10.1186/s12929-017-0327-y.
胃绕道手术……酒精的新问题 **。**Magdalena Plecka Östlund, Olof Backman, Richard Marsk, Dag Stockeld, Jesper Lagergren, Finn Rasmussen, and Erik Näslund, “与限制性减肥手术相比,胃旁路手术后酒精依赖症的入院率增加,"JAMA Surgery148, no.4 (2013):374–77,https://doi.org/10.1001/jamasurg.2013.700.
扩展访问 …甲基苯丙胺 **。**Jason L. Rogers, Silvia De Santis, and Ronald E. See, “Extended Methamphetamine Self-Administration Enhances Reinstatement of Drug Seeking and Impairs Novel Object Recognition in Rats, “Psychopharmacology199, no.4 (2008):615–24,https://doi.org/10.1007/s00213-008-1187-7.
扩展访问…尼古丁 **。**Laura E. O’Dell, Scott A. Chen, Ron T. Smith, Sheila E. Specio, Robert L. Balster, Neil E. Paterson, Athina Markou, et al., “延长尼古丁自我管理的机会导致依赖。昼夜节律措施、戒断措施和大鼠的灭绝行为”,*《药理学和实验治疗学杂志》*320,第1期(2007年)。180–93,https://doi.org/10.1124/jpet.106.105270.
海洛因 **:**Scott A. Chen, Laura E. O’Dell, Michael E. Hoefer, Thomas N. Greenwell, Eric P. Zorrilla, and George F. Koob, “Unlimited Access to Heroin Self-Administration:阿片类药物依赖性的独立动机标志”,《*神经精神药理学》*31,第12期(2006)。2692–707,https://doi.org/10.1038/sj.npp.1301008.
扩展访问 ……酒精 **。**Marcia Spoelder, Peter Hesseling, Annemarie M. Baars, José G. Lozeman-van’t Klooster, Marthe D. Rotte, Louk J. M. J. Vanderschuren, and Heidi M. B. Lesscher, “酒精摄入的个体差异预测大鼠的强化、动机和强迫性酒精使用,"Alcoholism: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39, no. 12 (2015): 2427-37,https://doi.org/10.1111/acer.12891.
稳定数量的可卡因 **。**Serge H. Ahmed和George F. Koob,“从适度的药物摄入到过度的药物摄入的过渡。Hedonic Set Point的变化”,《*科学》*282,no.5387 (1998):298–300,https://doi.org/10.1126/science.282.5387.298.
一张中奖 的彩票**。**Anne L. Bretteville-Jensen, “Addiction and Discounting,"*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18, no.4 (1999):393–407,https://doi.org/10.1016/S0167-6296(98)00057-5.
吸烟者……对未来的奖赏打折扣 **。**Warren K. Bickel, Benjamin P. Kowal, and Kirstin M. Gatchalian, “将成瘾理解为时间地平线的病理学,"Behavior Analyst Today7, no.1(2006)。32–47,https://doi.org/10.1037/h0100148.
“时间视野 “缩减 **。**Nancy M. Petry, Warren K. Bickel, and Martha Arnett, “Shortened Time Horizons and Insensitivity to Future Consequences in Heroin Addicts, “Addiction93, no.5 (1998):729–38,https://doi.org/10.1046/j.1360-0443.1998.9357298.x.
即时奖励与延迟奖励 **。**Samuel M. McClure, David I. Laibson, George Loewenstein, and Jonathan D. Cohen, “Separate Neural Systems Value Immediate and Delayed Monetary Rewards, “Science306, no.5695 (2004):503–7,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00907.
生活在 贫民区的****年轻巴西人 **。**Dandara Ramos, Tânia Victor, Maria L. Seidl-de-Moura, and Martin Daly, “Future Discounting by Slum-Dwelling Youth versus University Students in Rio de Janeiro,"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23, no. 1 (2013)。95–102,https://doi.org/10.1111/j.1532-7795.2012.00796.x.
的闲暇时间的数量 。Robert William Fogel,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这些关于美国休闲和工作的数据来自福格尔的书,这本书对美国过去四百年来的经济、社会和精神变革进行了令人敬畏的分析。
高收入国家也是如此。 经合组织,“特别关注。衡量经合组织国家的休闲,“见《2009年社会概览》。经合组织社会指标(巴黎:经合组织出版社,2009年),https://doi.org/10.1787/soc_glance-2008-en。
因教育和社会经济地位不同而不同 **。**David R. Francis,“为什么高收入者工作时间更长”,国家局经济研究摘要,2020年9月,http://www.nber.org/digest/jul06/w11895.html。
“将他们的休闲转移到视频游戏"。 Mark Aguiar, Mark Bils, Kerwin K. Charles, and Erik Hurst, “Leisure Luxuries and the Labor Supply of Young Men,”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 June 2017,https://doi.org/10.3386/w23552.
“无聊或受挫的问题解决者 **"。**Eric J. Iannelli, “Species of Madness”,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September 22, 2017.
“妇女要抛下她们的目光 "。"《古兰经》。24:31节”,2020年7月2日访问,http://corpus.quran.com/translation.jsp?chapter=24&verse=31。
“短裤和短裙 **"。**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着装和外观”,2020年7月2日访问,https://www.churchofjesuschrist.org/study/manual/for-the-strength-of-youth/dress-and-appearance?lang=eng。
3,000种新的无麸质零食产品 **。**M. Shahbandeh,“2014至2025年美国无麸质食品市场价值”,Statista,2019年11月20日,2020年7月2日访问,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884086/us-gluten-free-food-market-value/。
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棉花糖实验 。Yuichi Shoda, Walter Mischel, and Philip K. Peake, “从学前的延迟满足中预测青少年的认知和自我调节能力。识别诊断条件”,发展心理学26,第6期(1990年)。978–86,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26.6.978.
“用手遮住他们的眼睛 **"。**罗伊-F-鲍迈斯特,“你的意志力去哪儿了?"*《新科学家》*213期,第2849期(2012年)。30–31,https://doi.org/10.1016/s0262-4079(12)60232-2.
“对道德人的敬畏"。 伊曼纽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1785年),《剑桥哲学史文献》(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
buprenorphine减少非法阿片类药物的使用 **。**John Strang, Thomas Babor, Jonathan Caulkins, Benedikt Fischer, David Foxcroft, and Keith Humphreys, “Drug Policy and the Public Good:有效干预的证据》,*《柳叶刀》*379(2012)。71-83.
阿肯色州的医生开了116张阿片类药物处方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美国阿片类药物处方率地图”,2020年7月2日访问,https://www.cdc.gov/drugoverdose/maps/rxrate-maps.html。
一般来说,精神药物的证据并不强大 **。**罗伯特-惠特克(Robert Whitaker),《流行病的解剖》(Anatomy of an Epidemic)。魔法子弹、精神病药物和美国精神疾病惊人的增长(纽约:Crown,2010)。
儘管精神科藥物的經費大幅增加 …。Anthony F. Jorm, Scott B. Patten, Traolach S. Brugha, and Ramin Mojtabai, “增加治疗的提供降低了常见精神障碍的流行率吗?对四个国家证据的回顾》,*《世界精神病学》*第16期(2017年)。90–99,https://doi.org/10.1002/wps.20388.
这个过程被称为阿片类药物引起的痛觉减退 **。**Larry F. Chu, David J. Clark, and Martin S. Angst, “Opioid Tolerance and Hyperalgesia in Chronic Pain Patients after One Month of Oral Morphine Therapy:A Preliminary Prospective Study,"Journal of Pain7, no. 1 (2006):43–48,https://doi.org/10.1016/j.jpain.2005.08.001.
“ADHD药物治疗与病情恶化有关 **"。**Gretchen LeFever Watson, Andrea Powell Arcona, and David O. Antonuccio, “The ADHD Drug Abuse Crisis on American College Campuses,"Ethical Human Psychology and Psychiatry17, no. 1 (2015),https://doi.org/10.1891/1559-4343.17.1.5.
迟发性精神障碍 **。**Rif S. El-Mallakh, Yonglin Gao, and R. Jeannie Roberts, “Tardive Dysphoria: The Role of Long Term Antidepressant Use in-Inducing Chronic Depression,"Medical Hypotheses76, no. 6 (2011):769–73,https://doi.org/10.1016/j.mehy.2011.01.020.
抗抑郁药使人 “好上加好 "。 Peter D. Kramer,Listening to Prozac(New York: Viking Press, 1993).
7.5%的美国儿童 **。**Lajeana D. Howie, Patricia N. Pastor, and Susan L. Lukacs, “Use of Medication Prescribed for Emotional or Behavioral Difficulties among Children Aged 6-17 Year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11-2012, “Health Care in the United States:发展与考虑5,第148期(2015年):25-35。
多达一万名幼儿 **。**艾伦-施瓦茨,“报告发现,成千上万的幼儿被用于治疗A.D.H.D.,引起了人们的担忧”,《纽约时报》,2014年5月16日。
“对不良和非人道待遇的反应 **"。**埃德蒙-C-莱文,“在青少年寄宿机构中治疗发展性创伤障碍的挑战”,《*美国精神分析和动态精神病学学会杂志》*37期。3 (2009):519–38,https://doi.org/10.1521/jaap.2009.37.3.519.
“邻里关系的匮乏是相关的 **"。**Casey Crump, Kristina Sundquist, Jan Sundquist, and Marilyn A. Winkleby, “邻里贫穷与精神药物处方。A Swedish National Multilevel Study,"Annals of Epidemiology21, no.4 (2011):231–37,https://doi.org/10.1016/j.annepidem.2011.01.005.
“经济前景较差的县 **"。**Robin Ghertner和Lincoln Groves,“阿片类药物危机和经济机会。地理和经济趋势》,来自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的ASPE研究简报,2018年,https://aspe.hhs.gov/system/files/pdf/259261/ASPEEconomicOpportunityOpioidCrisis.pdf。
医疗补助患者死于阿片类药物 **。**Mark J. Sharp和Thomas A. Melnik, “Poisoning Deaths Involving Opioid Analgesics-New York State, 2003-2012,"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64, no. 14 (2015):377-80;P. Coolen, S. Best, A. Lima, J. Sabel, and L. J. Paulozzi, “Overdose Deaths Involving Prescription Opioids among Medicaid Enrollees-Washington, 2004-2007,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Report 58, no.42 (2009):1171-75.
“单独用药,而不是解放 **"。**Alexandrea E. Hatcher, Sonia Mendoza, and Helena Hansen, “At the Expense of a Life:种族、阶级和丁丙诺啡在药物化 “护理 “中的意义,” 《物质使用和滥用》第53期(2018年)。301–10,https://doi.org/10.1080/10826084.2017.1385633.
10名男子自愿将自己浸入水中 **。**PetrŠrámek, MarieŠimečková, Ladislav Janský, Jarmila Šavlíková, and Stanislav Vybíral, “人类对浸入不同温度的水的生理反应”,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81(2000)。436–42,https://doi.org/10.1007/s004210050065.
冬眠地松鼠的大脑 **。**Christina G. von der Ohe, Corinna Darian-Smith, Craig C. Garner, and H. Craig Heller, “Ubiquitous and Temperature-Dependent Neural Plasticity in Hibernators, “Journal of Neuroscience26, no.41 (2006):10590–98,https://doi.org/10.1523/JNEUROSCI.2874-06.2006.
在狗身上进行了一系列的实验 **。**Russell M. Church, Vincent LoLordo, J. Bruce Overmier, Richard L. Solomon, and Lucille H. Turner, “Cardiac Responses to Shock in Curarized Dogs: Effects of Shock Intensity and Duration, Warning Signal, and Prior Experience with Shock, “Journal of Comparative and Physiological Psychology62, no:1-7,https://doi.org/10.1037/h0023476; Aaron H. Katcher, Richard L. Solomon, Lucille H. Turner, Vincent LoLordo, J. Bruce Overmier, and Robert A. Rescorla, “心率和血压对有信号和无信号冲击的反应。心交感神经切除术的影响”,《比较和生理心理学杂志》第68期(1969年)。163-74;Richard L. Solomon和John D. Corbit, “An Opponent-Process Theory of Motiv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68, no. 6 (1978):12-24.
“这东西,人们称之为快乐! **"。*R. S. Bluck,Plato’sPhaedo: A Translation of Plato’s*Phaedo (London: Routledge, 2014),https://www.google.com/books/edition/Plato_s_Phaedo/7FzXAwAAQBAJ?hl=en&gbpv=1&dq=%22how+strange+would+appear+to+be+this+thing+that+men+call+pleasure%22&pg=PA41&printsec=frontcover 。
“儿子被雷电击中 **"。**Helen B. Taussig, “‘死亡’来自闪电和重生的可能性”,American Scientist57, no.3 (1969):306-16.
“环境或自我施加的挑战"。 Edward J. Calabrese和Mark P. Mattson,“Hormesis如何影响生物学、毒理学和医学?"npj Aging and Mechanisms of Disease3,no.13(2017),https://doi.org/10.1038/s41514-017-0013-z。
暴露在温度下的蠕虫 。James R. Cypser, Pat Tedesco, and Thomas E. Johnson, “Hormesis and Aging inCaenorhabditis Elegans,"Experimental Gerontology41, no. 10 (2006):935–39,https://doi.org/10.1016/j.exger.2006.09.004.
在离心机中旋转的果蝇 **。**Nadège Minois, “The Hormetic Effects of Hypergravity on Longevity and Aging,"Dose-Response4, no. 2 (2006),https://doi.org/10.2203/dose-response.05-008.minois. 当我读到这项研究时,我想象着在当地游乐园的重力机中度过两到四个星期,这种大型直立桶以每分钟33转的速度旋转,在地板掉下来之前产生相当于近3g的离心效应。鉴于果蝇的平均寿命是50天,这相当于在重力机里呆了50多年的人类。那些可怜的苍蝇!
“刺激了抗癌免疫力 **"。**Shizuyo Sutou, “来自A-Bombs的低剂量辐射延长了寿命,相对于未受辐射的个体,癌症死亡率降低,"Genes and Environment40, no. 26 (2018),https://doi.org/10.1186/s41021-018-0114-3.
这些发现是有争议的 **。**John B. Cologne 和 Dale L. Preston, “Longevity of Atomic-Bomb Survivors,"Lancet356, no. 9226 (July 22, 2000):303–7,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00)02506-X.
卡路里限制延长寿命 **。**Mark P. Mattson和Ruiqian Wan,“Intermittent Fasting and Caloric Restriction对心血管和脑血管系统的有益影响”,《*营养生物化学杂志》*16,no。3 (2005):129–37,https://doi.org/10.1016/j.jnutbio.2004.12.007.
“每周让自己饿两天 **"。**Aly Weisman和Kristen Griffin, “Jimmy Kimmel Lost a Ton of Weight on This Radical Diet,"Business Insider, January 9, 2016.
锻炼可以增加许多神经递质 **。安娜-莱姆克(Anna Lembke)和阿米尔-拉赫穆拉(Amer Raheemullah),《成瘾与锻炼》,载于《生活方式精神病学》。使用运动、饮食和正念来管理精神疾病》,编辑:Doug Noordsy(华盛顿特区:美国精神病学会)。Doug Noordsy(华盛顿特区:美国精神病学出版社,2019年)。
多巴胺在身体运动中的古老作用 **。**Daniel T. Omura, Damon A. Clark, Aravinthan D. T. Samuel, and H. Robert Horvitz, “Dopamine Signaling Is Essential for Precise Rates of Locomotion byC. Elegans, “PLOS ONE7, no. 6 (2012),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38649.
他们醒着的时候有一半时间是坐着的 **。**Shu W. Ng和Barry M. Popkin,“时间使用和身体活动。全球范围内的运动转移”,《*肥胖症评论》*13,第8期(2012年8月)。659–80,https://doi.org/10.1111/j.1467-789X.2011.00982.x.
每天穿越几十公里的路程 **。**Mark P. Mattson,“能量摄入和运动是大脑健康和对伤害和疾病的脆弱性的决定因素”,《*细胞代谢》*16,第6期(2012)。706–22,https://doi.org/10.1016/j.cmet.2012.08.012.
锻炼比我能开出的任何药片都更……。 B. K. Pedersen和B. Saltin,“运动作为药物–在26种不同的慢性病中开具运动治疗的证据*"*,*斯堪的纳维亚体育医学和科学杂志*25,no.S3 (2015): 1-72.
“便利的暴政 **"。**蒂姆-吴,“便利的暴政”,*纽约时报,*2018年2月6日。
“关于两种疼痛同时发生 **"。**希波克拉底,《箴言》,2020年7月8日访问,http://classics.mit.edu/Hippocrates/aphorisms.1.i.html。
应用第二个痛苦的刺激 。Christian Sprenger, Ulrike Bingel, and Christian Büchel, “Treating Pain with Pain: Supraspinal Mechanisms of Endogenous Analgesia Elicited by Heterotopic Noxious Conditioning Stimulation, “Pain152, no:428–39,https://doi.org/10.1016/j.pain.2010.11.018.
“针刺,可以伤人 **"。**刘翔,《以痛制痛–针灸镇痛的基本神经机制》,《*中国科学报》*46期(2001年)。1485–94,https://doi.org/10.1007/BF03187038.
“他们的疼痛评分减少得更多 **"。**Jarred Younger, Noorulain Noor, Rebecca McCue, and Sean Mackey, “低剂量纳曲酮治疗纤维肌痛。一个小型、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平衡、交叉试验的结果,评估每日疼痛水平,"《关节炎和风湿病》第65期(2013)。529–38,https://doi.org/10.1002/art.37734.
“由奇怪的新名词组成的难以理解的胡言乱语 **"。**Ugo Cerletti,“关于电击的新旧信息”,《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7,第2期(1950)。87–94,https://doi.org/10.1176/ajp.107.2.87.
“ECT带来了各种 **"。**阿米特-辛格和苏吉塔-库马尔-卡尔,“电休克疗法如何发挥作用?了解神经生物学机制》,《临床精神药理学和神经科学》15,no.3 (2017):210–21,https://doi.org/10.9758/cpn.2017.15.3.210.
“我做了这么多独奏 **"。**Mark Synnott,The Impossible Climb:Alex Honnold, El Capitan, and the Climbing Life(New York: Dutton, 2018).
老鼠跑到死 **。**Chris M. Sherwin, “Voluntary Wheel Running:A Review and Novel Interpretation,"Animal Behaviour56, no. 1 (1998):11–27,https://doi.org/10.1006/anbe.1998.0836.
“野鼠常年在车轮上奔跑 **"。**Johanna H. Meijer和Yuri Robbers,“野外的车轮奔跑”,《皇家学会论文集B:生物科学》,2014年7月7日,https://doi.org/10.1098/rspb.2014.0210。
仅仅是压力就可以增加多巴胺的释放 **。**Daniel Saal, Yan Dong, Antonello Bonci, and Robert C. Malenka, “Drugs of Abuse and Stress Trigger a Common Synaptic Adaptation in Dopamine Neurons, “Neuron37, no.4 (2003):577–82,https://doi.org/10.1016/S0896-6273(03)00021-7.
“跳伞与成瘾行为有相似之处 **"。**Ingmar H. A. Franken, Corien Zijlstra, and Peter Muris, “非药物诱导的奖励与失重症有关吗?A Study among Skydivers,"Progress in Neuro-Psychopharmacology and Biological Psychiatry30, no. 2 (2006):297–300,https://doi.org/10.1016/j.pnpbp.2005.10.011.
“冰块冷却器为我的核心降温 **"。**凯特-克尼布斯,“一位超级马拉松运动员传奇人物在旅途中携带的所有装备”,Gizmodo,2015年10月29日,https://gizmodo.com/all-the-gear-an-ultramarathon-legend-brings-with-him-on-1736088954。
“记住数以千计的复杂的手脚顺序 **"。**Mark Synnott,“Alex Honnold如何在没有绳子的情况下完成终极攀登”,国家地理在线,2020年7月8日访问,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magazine/2019/02/alex-honnold-made-ultimate-climb-el-capitan-without-rope。
“过度训练综合症 **"。**Jeffrey B. Kreher和Jennifer B. Schwartz,“过度训练综合症。A Practical Guide,"Sports Health4, no. 2 (2012),https://doi.org/10.1177/1941738111434406.
受过高等教育的工薪族工作更多 **。**David R. Francis,“为什么高收入者工作时间更长”,国家经济研究局摘要,2021年2月5日访问,https://www.nber.org/digest/jul06/w11895.html。
成人平均每天讲0.59至1.56个谎言 **。**Silvio José Lemos Vasconcellos, Matheus Rizzatti, Thamires Pereira Barbosa, Bruna Sangoi Schmitz, Vanessa Cristina Nascimento Coelho, and Andrea Machado, “理解基于进化心理学的谎言。A Critical Review,"Trends in Psychology27, no. 1 (2019):141–53,https://doi.org/10.9788/TP2019.1-11.
诚实的神经生物学机制 **。**Michel André Maréchal, Alain Cohn, Giuseppe Ugazio, and Christian C. Ruff, “Increasing Honesty in Humans with Noninvasive Brain Stimulation,"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America114, no. 17 (2017):4360–64,https://doi.org/10.1073/pnas.1614912114.
催产素会导致大脑多巴胺的增加 **。**催产素也会导致多巴胺的主要目标–阿肯色核–释放5羟色胺(5HT)–对于促进 “亲社会 “行为来说,阿肯色核中的5羟色胺的释放比多巴胺的释放更重要。然而,同时释放的多巴胺可能是使亲社会行为可能成瘾的原因。林伟雄, 苏菲-诺伊纳, 杰-斯.Polepalli, Kevin T. Beier, Matthew Wright, Jessica J. Walsh, Eastman M. Lewis, et al., “Gating of Social Reward by Oxytocin in the Ventral Tegmental Area, “Science357, no. 6358 (2017):1406–11,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n4994.
大鼠被困在一个塑料瓶内 。Seven E. Tomek, Gabriela M. Stegmann, and M. Foster Olive, “Effects of Heroin on Rat Prosocial Behavior, “Addiction Biology24, no.4 (2019): 676-84,https://doi.org/10.1111/adb.12633.
AA哲学和教义 。 十二个步骤和十二个传统(纽约:匿名酗酒者世界服务)。
“假我 **"的概念 。唐纳德-W-温尼科特,“在真我和假我方面的自我扭曲”,载于《成熟过程和促进环境》。情感发展理论研究》(纽约:国际大学出版社,1960),140-57。
“一种联系的感觉 **"。**Mark Epstein,Going on Being:生活在佛教和心理治疗的十字路口(波士顿:智慧出版社,2009)。
孩子们经历了一个失败的承诺 **:**Celeste Kidd, Holly Palmeri, and Richard N. Aslin, “Rational Snacking:Young Children’s Decision-Making on the Marshmallow Task Is Moderated by Beliefs about Environmental Reliability,"Cognition126, no. 1 (2013):109–14,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12.08.004.
“刚刚被解雇 **"。**Warren K. Bickel, A. George Wilson, Chen Chen, Mikhail N. Koffarnus, and Christopher T. Franck, “Stuck in Time: Negative Income Shock Constricts the TemporalWindow of Valuation spanning the Future and the Past,"PLOS ONE11, no. 9 (2016):1–12,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63051.
积极参加宗教组织 。Mark J. Edlund, Katherine M. Harris, Harold G. Koenig, Xiaotong Han, Greer Sullivan, Rhonda Mattox, and Lingqi Tang, “Religiosity and Decreased Risk of Substance Use Disorders:社会精神病学和精神病学流行病学》,第45期(2010年)。827–36,https://doi.org/10.1007/s00127-009-0124-3.
“我从周日的服务中获得的快乐 **"。**Laurence R. Iannaccone,“牺牲和耻辱。减少邪教、公社和其他集体的自由活动,"*《政治经济学杂志》*100,第2期(1992)。271-91.
“减少参与的污名化行为 **"。**Laurence R. Iannaccone, “Why Strict Churches Are Strong,"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9, no.5 (1994):1180–1211,https://doi.org/10.2307/2781147.
书目
Adinoff, Bryon.“药物奖励和成瘾的神经生物学过程”。Harvard Review of Psychiatry12, no. 6 (2004):305–20.https://doi.org/10.1080/10673220490910844.
Aguiar, Mark, Mark Bils, Kerwin Kofi Charles, and Erik Hurst.“休闲奢侈品和年轻男性的劳动供应”。国家经济研究局工作文件,2017年6月。https://doi.org/10.3386/w23552。
Ahmed, S. H., and G. F. Koob.“从适度的药物摄入过渡到过度的药物摄入。Hedonic Set Point的变化”。Science282, no.5387 (1998):298–300.https://doi.org/10.1126/science.282.5387.298.
ASPPH应对阿片类药物危机的公共卫生倡议特别小组。将科学带入阿片类药物。报告和建议,2019年11月。
Bachhuber, Marcus A., Sean Hennessy, Chinazo O. Cunningham, and Joanna L. Starrels.“1996-2013年美国不断增加的苯并二氮䓬类药物处方和过量的死亡率”。美国公共卫生杂志》106, no.4 (2016):686–88.https://doi.org/10.2105/AJPH.2016.303061.
巴萨雷奥,瓦伦蒂娜,和加塔诺-迪基亚拉。“食欲刺激引起的中枢多巴胺传递激活的调制及其与动机状态的关系”。欧洲神经科学杂志》11,第12期(1999年)。4389–97.https://doi.org/10.1046/j.1460-9568.1999.00843.x.
Baumeister, Roy F. “你的意志力去哪了?"新科学家》213期,第2849期(2012年)。30–31.https://doi.org/10.1016/s0262-4079(12)60232-2.
比彻,亨利。“在战斗中受伤的人的疼痛”。麻醉与镇痛26, no. 1 (1947):21.https://doi.org/10.1213/00000539-194701000-00005.
Bickel, Warren K., A. George Wilson, Chen Chen, Mikhail N. Koffarnus, and Christopher T. Franck.“困在时间里:负收入冲击限制了跨越未来和过去的估值时间窗口。"PLOS ONE11, no. 9 (2016):1–12.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163051.
Bickel, Warren K., Benjamin P. Kowal, and Kirstin M. Gatchalian.“将成瘾理解为一种时间范围的病理学”。今日行为分析师》7,第1期(2006)。32–47.https://doi.org/10.1037/h0100148.
Blanchflower, David G., and Andrew J. Oswald.“现代美国的不快乐和痛苦。A Review Essay, and Further Evidence, on Carol Graham’s Happiness for All?“IZA劳动经济研究所讨论文件,2017年11月。
Bluck, R. S.Plato’sPhaedo*: A translation of Plato’s*Phaedo.伦敦。Routledge, 2014.https://www.google.com/books/edition/Plato_s_Phaedo/7FzXAwAAQBAJ?hl=en&gbpv=1&dq=%22how+strange+would+appear+to+be+this+thing+that+men+call+pleasure%22&pg=PA41&printsec=frontcover .
Bretteville-Jensen, A. L. “成瘾和贴现”。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18, no.4 (1999):393–407.https://doi.org/10.1016/S0167-6296(98)00057-5.
Brown, S. A., and M. A. Schuckit.“戒酒者的抑郁症变化”。酒精研究杂志49, no.5 (1988):412-17。http://www.ncbi.nlm.nih.gov/entrez/query.fcgi?cmd=Retrieve&db=PubMed&dopt=Citation&list_uids=3216643。
Calabrese, Edward J., and Mark P. Mattson.“Hormesis如何影响生物学、毒理学和医学?"npj Aging and Mechanisms of Disease3, no. 13 (2017). https://doi.org/10.1038/s41514-017-0013-z。
“资本之痛”。经济学家》,2020年7月18日。
Case, Anne, and Angus Deaton.绝望的死亡和资本主义的未来。普林斯顿,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0。https://doi.org/10.2307/j.ctvpr7rb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美国阿片类药物处方率地图”。2020年7月2日访问。https://www.cdc.gov/drugoverdose/maps/rxrate-maps.html。
Cerletti, Ugo.“关于电击的新旧信息”。美国精神病学杂志107,第2期(1950)。87–94.https://doi.org/10.1176/ajp.107.2.87.
Chang, Jeffrey S., Jenn Ren Hsiao, and Che Hong Chen.“ALDH2多态性和亚洲人的酒精相关癌症。公共卫生的视角”。Journal of Biomedical Science24, no. 1 (2017):1–10.https://doi.org/10.1186/s12929-017-0327-y.
Chanraud, Sandra, Anne-Lise Pitel, Eva M. Muller-Oehring, Adolf Pfefferbaum, and Edith V. Sullivan.“重绘大脑以补偿酗酒者的损伤》,《大脑皮层》23 (2013)。97–104.https://doi.org/10.1093/cercor/bhr381.
Chen, Scott A., Laura E. O’Dell, Michael E. Hoefer, Thomas N. Greenwell, Eric P. Zorrilla, and George F. Koob.“无限制地获得海洛因自我管理。阿片剂依赖的独立动机标志”。Neuropsychopharmacology31, no. 12 (2006):2692–707.https://doi.org/10.1038/sj.npp.1301008.
Chiara, G. Di, and A. Imperato.“人类滥用的药物优先增加自由活动的大鼠中脑系统的突触多巴胺浓度”。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第85期(1988年)。5274–78.https://doi.org/10.1073/pnas.85.14.5274.
Chu, Larry F., David J. Clark, and Martin S. Angst.“口服吗啡治疗一个月后,慢性疼痛患者的阿片类药物耐受性和痛觉减退。一个初步的前瞻性研究”。疼痛杂志》7,第1期(2006年)。43–48.https://doi.org/10.1016/j.jpain.2005.08.001.
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衣着和外观”。Accessed July 2, 2020.https://www.churchofjesuschrist.org/study/manual/for-the-strength-of-youth/dress-and-appearance?lang=eng.
Church, Russell M., Vincent LoLordo, J. Bruce Overmier, Richard L. Solomon, and Lucille H. Turner.“鬈毛狗对休克的心脏反应:休克强度和持续时间、警告信号和先前休克经验的影响。比较和生理心理学杂志》62,第1期(1966)。1–7.https://doi.org/10.1037/h0023476.
Cologne, John B., and Dale L. Preston.“原子弹存活者的寿命”。Lancet356, no. 9226 (2000):303–7.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00)02506-X.
Coolen, P., S. Best, A. Lima, J. Sabel, and L. Paulozzi.“2004-2007年,华盛顿州医疗补助计划注册者中涉及处方阿片类药物的过量死亡”。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58, no.42 (2009):1171-75.
Courtwright, David T. “对鸦片和吗啡上瘾”。在《黑暗天堂》中。A History of Opiate Addiction in America, 35-60.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https://doi.org/10.2307/j.ctvk12rb0.7.
Courtwright, David T.The Age of Addiction:How Bad Habits Became Big Business.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9.https://doi.org/10.4159/9780674239241.
Crump, Casey, Kristina Sundquist, Jan Sundquist, and Marilyn A. Winkleby.“邻近地区的贫困和精神药物的处方。瑞典国家多层次研究”。*流行病学年鉴》*21, no.4 (2011):231–37.https://doi.org/10.1016/j.annepidem.2011.01.005.
崔长海、Antonio Noronha、Kenneth R. Warren、George F. Koob、Rajita Sinha、Mahesh Thakkar、John Matochik等人,“酒精依赖恢复的大脑途径”。Alcohol49, no.5 (2015):435–52.https://doi.org/10.1016/j.alcohol.2015.04.006.
Cypser, James R., Pat Tedesco, and Thomas E. Johnson."埃利根氏菌的荷尔蒙生成和衰老”。实验老年学41,第10期(2006)。935–39.https://doi.org/10.1016/j.exger.2006.09.004.
Douthat, Ross.Bad Religion:How We Became a Nation of Heretics.New York:Free Press, 2013.
Dunnington, Kent.成瘾和美德:超越疾病和选择的模式。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Academic, 2011.
Edlund, Mark J., Katherine M. Harris, Harold G. Koenig, Xiaotong Han, Greer Sullivan, Rhonda Mattox, and Lingqi Tang.“宗教信仰与药物使用障碍的风险降低。社会支持或心理健康状况是其影响的中介吗?"社会精神病学和精神病流行病学45(2010)。827–36.https://doi.org/10.1007/s00127-009-0124-3.
Eikelboom, Roelof, and Randelle Hewitt.“大鼠间歇性接触蔗糖溶液会导致消耗量的长期增加”。生理学与行为学》165(2016)。77–85.https://doi.org/10.1016/j.physbeh.2016.07.002.
El-Mallakh, Rif S., Yonglin Gao, and R. Jeannie Roberts.“迟发性焦虑症:长期使用抗抑郁药在诱发慢性抑郁症中的作用”。*医学假说》*第76期,第6期(2011年)。769–73.https://doi.org/10.1016/j.mehy.2011.01.020.
Epstein, Mark.Going on Being:在佛教和心理治疗的十字路口的生活。波士顿。智慧出版社,2009年。
Fava, Giovanni A., and Fiammetta Cosci.“理解和管理抗抑郁药物停药后的戒断综合症”。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iatry80, no. 6 (2019). https://doi.org/10.4088/JCP.19com12794。
Fiorino, Dennis F., Ariane Coury, and Anthony G. Phillips.“雄性大鼠库里奇效应期间,阿肯本核多巴胺外流的动态变化”。神经科学杂志》17,第12期(1997年)。4849–55.https://doi.org/10.1523/jneurosci.17-12-04849.1997.
Fisher, J. P., D. T. Hassan, and N. O’Connor.“关于疼痛的案例报告”。英国医学杂志310,第6971期(1995)。70.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2548478/pdf/bmj00574-0074.pdf。
Fogel, Robert William.The Fourth Great Awakening and the Future of Egalitarianism.芝加哥。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Francis, David R. “为什么高收入者工作时间更长”。国家经济研究局文摘,2020年。http://www.nber.org/digest/jul06/w11895.html。
Frank, Joseph W., Travis I. Lovejoy, William C. Becker, Benjamin J. Morasco, Christopher J. Koenig, Lilian Hoffecker, Hannah R. Dischinger, et al. “减少剂量或停止长期阿片类药物治疗的患者结果。系统回顾”。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167, no.3 (2017):181–91.https://doi.org/10.7326/M17-0598.
Franken, Ingmar H. A., Corien Zijlstra, and Peter Muris.“非药物诱导的奖励与失重症有关吗?在跳伞运动员中的研究”。神经精神药理学和生物精神病学进展》30,第2期(2006)。297–300.https://doi.org/10.1016/j.pnpbp.2005.10.011.
加斯帕罗,安妮,和杰西-纽曼。“口味的新科学:1000种香蕉口味”。华尔街日报》,2014年10月31日。
Ghertner, Robin, and Lincoln Groves.“阿片类药物危机和经济机会。地理和经济趋势”。ASPE研究简报来自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2018年。https://aspe.hhs.gov/system/files/pdf/259261/ASPEEconomicOpportunityOpioidCrisis.pdf。
Grant, Bridget F., S. Patricia Chou, Tulshi D. Saha, Roger P. Pickering, Bradley T. Kerridge, W. June Ruan, Boji Huang, et al. “2001-2002年至2012年美国12个月酒精使用、高风险饮酒和DSM-IV酒精使用障碍的流行率。来自全国酒精及相关疾病流行病学调查的结果”。JAMA精神病学74,第9期(2017年9月1日)。911–23.https://doi.org/10.1001/jamapsychiatry.2017.2161.
霍尔,韦恩。“1920-1933年美国国家禁酒令的政策教训是什么?"Addiction105, no. 7 (2010):1164-73。https://pubmed.ncbi.nlm.nih.gov/20331549/。
Hatcher, Alexandrea E., Sonia Mendoza, and Helena Hansen.“At the Expense of a Life:种族、阶级和丁丙诺啡在药物化 “护理 “中的意义。"物质使用和滥用53,第2(2018)。301–10.https://doi.org/10.1080/10826084.2017.1385633.
Helliwell, John F., Haifang Huang, and Shun Wang.“第二章:改变世界的幸福感”。2019年世界幸福报告》,2019年3月20日。
希波克拉底。箴言》。2020年7月8日访问。http://classics.mit.edu/Hippocrates/aphorisms.1.i.html。
Howie, Lajeana D., Patricia N. Pastor, and Susan L. Lukacs.“2011-2012年美国6-17岁儿童中因情绪或行为困难而开具的药物使用情况”。美国的医疗保健。发展与考虑5,第148期(2015年):25-35。
Hung, Lin W., Sophie Neuner, Jai S。Polepalli, Kevin T. Beier, Matthew Wright, Jessica J. Walsh, Eastman M. Lewis, et al. “腹侧被盖区的催产素对社会奖励的调控”。Science357, no. 6358 (2017):1406–11.https://doi.org/10.1126/science.aan4994.
赫胥黎,奥尔德斯。Brave New World Revisited.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4.
Iannaccone, Laurence R. “牺牲和污名。减少邪教、公社和其他集体中的搭便车”。政治经济学杂志》100,第2期(1992)。271-91.
Iannaccone, Laurence R. “为什么严格的教会很强大”。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99, no.5 (1994):1180–1211.https://doi.org/10.2307/2781147.
Iannelli, Eric J. “疯狂的物种”。泰晤士报文学副刊》,2017年9月22日。
Jonas, Bruce S., Qiuping Gu, and Juan R. Albertorio-Diaz.“青少年中的精神药物使用。美国,2005-2010年”。NCHS数据简报,第135期(2013年12月)。1-8.
Jorm, Anthony F., Scott B. Patten, Traolach S. Brugha, and Ramin Mojtabai.“提供更多的治疗是否降低了常见精神障碍的发病率?四个国家的证据回顾”。世界精神病学》16,第1期(2017)。90–99.https://doi.org/10.1002/wps.20388.
康德,伊曼纽尔。“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1785年),《剑桥哲学史文献》。 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
Katcher, Aaron H., Richard L. Solomon, Lucille H. Turner, and Vincent Lolordo.“心率和血压对有信号和无信号的冲击的反应。心脏交感神经切除术的影响”。比较和生理心理学杂志》68,第2期(1969)。163-74.
Kidd, Celeste, Holly Palmeri, and Richard N. Aslin.“理性的零食。幼儿在棉花糖任务上的决策受环境可靠性信念的调节”。认知》126,第1期(2013年)。109–14.https://doi.org/10.1016/j.cognition.2012.08.004.
克尼布斯,凯特。“一位超级马拉松运动员的传奇人物在旅途中携带的所有装备”。Gizmodo,2015年10月29日。https://gizmodo.com/all-the-gear-an-ultramarathon-legend-brings-with-him-on-1736088954。
Kohrman, Matthew, Quan Gan, Liu Wennan, and Robert N. Proctor, eds.有毒的熊猫。批判性历史视角下的中国卷烟制造。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18年。
Kolb, Brian, Grazyna Gorny, Yilin Li, Anne-Noël Samaha, and Terry E. Robinson.“安非他命或可卡因限制了后来的经验促进新皮层和阿肯色核的结构可塑性的能力”。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100,第18期(2003年)。10523–28.https://doi.org/10.1073/pnas.1834271100.
Koob, George F. “Hedonic Homeostatic Dysregulation as a Driver of Drug-Seeking Behavior”。今天的药物发现。疾病模型》5, no.4 (2008):207–15.https://doi.org/10.1016/j.ddmod.2009.04.002.
Kramer, Peter D.*Listening to Prozac.*New York:Viking Press, 1993.
Kreher, Jeffrey B., and Jennifer B. Schwartz.“过度训练综合症。实用指南”。运动健康4,第2期(2012年)。https://doi.org/10.1177/1941738111434406。
Leknes, Siri, and Irene Tracey.“疼痛和快乐的共同神经生物学”。Nature Reviews Neuroscience9, no.4 (2008):314–20.https://doi.org/10.1038/nrn2333.
Lembke, Anna.医学博士,毒贩:医生如何被骗,病人如何上钩,以及为什么如此难以停止。第1版。巴尔的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2016年。
Lembke, Anna.“是时候放弃精神病患者的自我治疗假说了”。美国药物和酒精滥用杂志38,第6期(2012)。524–29.https://doi.org/10.3109/00952990.2012.694532.
Lembke, Anna, and Amer Raheemullah.“成瘾与运动”。在《*生活方式精神病学》中。*在《生活方式精神病学:使用运动、饮食和正念来管理精神疾病》中,由Doug Noordsy编著。Washington, DC:美国精神病学出版社,2019年。
Lembke, Anna, and Niushen Zhang.“当代中国寻求治疗的海洛因使用者的定性研究”。Addiction Science & Clinical Practice10, no. 23 (2015). https://doi.org/10.1186/s13722-015-0044-3。
Levin, Edmund C. “在青少年寄宿机构中治疗发展性创伤障碍的挑战”。*美国精神分析和动态精神病学学会杂志》*37, no.3 (2009):519–38.https://doi.org/10.1521/jaap.2009.37.3.519.
Linnet, J., E. Peterson, D. J. Doudet, A. Gjedde, and A. Møller.“病态赌徒输钱时腹侧纹状体的多巴胺释放”。Acta Psychiatrica Scandinavica122, no.4 (2010):326–33.https://doi.org/10.1111/j.1600-0447.2010.01591.x.
刘庆庆、何海荣、杨进、冯晓杰、赵凡凡和柳俊。“1990年至2017年全球抑郁症负担的变化。来自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发现”。 精神病学研究杂志126(2020年6月):134-40。https://doi.org/10.1016/j.jpsychires.2019.08.002。
Liu, Xiang.“以痛制痛–针灸镇痛的基本神经机理”。*中国科学报》*46,第17期(2001)。1485–94.https://doi.org/10.1007/BF03187038.
Low, Yinghui, Collin F. Clarke, and Billy K. Huh.“阿片类药物诱导的痛觉减退症。流行病学、机制和管理回顾”。新加坡医学杂志53, no.5 (2012):357-60.
MacCoun, Robert.“毒品与法律。禁毒的心理学分析”。心理学公报113(1993年6月1日)。497–512.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13.3.497.
Maréchal, Michel André, Alain Cohn, Giuseppe Ugazio, and Christian C. Ruff.“用无创脑刺激提高人类的诚实度”。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第114期,第17期(2017年)。4360–64.https://doi.org/10.1073/pnas.1614912114.
Mattson, Mark P. “能量摄入和运动是大脑健康和易受伤害及疾病影响的决定因素”。细胞代谢》16,第6期(2012年)。706–22.https://doi.org/10.1016/j.cmet.2012.08.012.
Mattson, Mark P., and Ruiqian Wan.“间歇性禁食和热量限制对心血管和脑血管系统的有益影响”。营养生物化学杂志》16, no.3 (2005):129–37.https://doi.org/10.1016/j.jnutbio.2004.12.007.
McClure, Samuel M., David I. Laibson, George Loewenstein, and Jonathan D. Cohen.“独立的神经系统重视即时和延迟的货币奖励”。科学》306期,第。5695 (2004):503–7.https://doi.org/10.1126/science.1100907.
Meijer, Johanna H., and Yuri Robbers.“车轮在野外的运行”。皇家学会议事录B:生物科学》,2014年7月7日。https://doi.org/10.1098/rspb.2014.0210。
Meldrum, M. L. “疼痛管理的胶囊史”。JAMA290, no. 18 (2003):2470–75.https://doi.org/10.1001/jama.290.18.2470.
Mendis, Shanthi, Tim Armstrong, Douglas Bettcher, Francesco Branca, Jeremy Lauer, Cecile Mace, Shanthi Mendis, et al.2014年非传染性疾病全球状况报告。世界卫生组织,2014年。https://apps.who.int/iris/bitstream/handle/10665/148114/9789241564854_eng.pdf。
Minois, Nadège.“超重力对长寿和衰老的荷尔蒙效应”。Dose-Response4, no. 2 (2006).https://doi.org/10.2203/dose-response.05-008.minois.
Montagu, Kathleen A. “大鼠组织和不同动物大脑中的儿茶酚化合物”。自然180(1957)。244–45.https://doi.org/10.1038/180244a0.
国家马铃薯委员会。2016年马铃薯统计年鉴》。2020年4月18日访问。https://web.archive.org/web/20190707034920/https://www.nationalpotatocouncil.org/files/7014/6919/7938/NPCyearbook2016_-_FINAL.pdf。
Ng, Marie, Tom Fleming, Margaret Robinson, Blake Thomson, Nicholas Graetz, Christopher Margono, Erin C. Mullany, et al. “1980-2013年期间全球、区域和国家儿童和成人超重和肥胖的流行率。2013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系统分析”。Lancet384, no. 9945 (August 2014):766–81.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4)60460-8.
Ng, S. W., and B. M. Popkin.“时间使用和身体活动。A Shift Away from Movement across the Globe,"Obesity Reviews13, no. 8 (August 2012):659–80.https://doi.org/10.1111/j.1467-789X.2011.00982.x.
O’Dell, Laura E., Scott A. Chen, Ron T. Smith, Sheila E. Specio, Robert L. Balster, Neil E. Paterson, Athina Markou, et al. “延长尼古丁自我管理机会导致依赖。大鼠的昼夜节律措施、戒断措施和熄灭行为”。药理学和实验治疗学杂志》320,第1期(2007)。180–93.https://doi.org/10.1124/jpet.106.105270.
OECD.“经合组织2020年卫生统计”,2020年7月。http://www.oecd.org/els/health-systems/health-data.htm。
经合组织。“特别关注。衡量经合组织国家的休闲”。载于《2009年社会概览》。OECD社会指标。巴黎。经合组织出版社,2009年。https://doi.org/10.1787/soc_glance-2008-en。
Ohe, Christina G. von der, Corinna Darian-Smith, Craig C. Garner, and H. Craig Heller.“冬眠者中无处不在的、随温度变化的神经可塑性”。神经科学杂志》26, no.41 (2006):10590–98.https://doi.org/10.1523/JNEUROSCI.2874-06.2006.
Omura, Daniel T., Damon A. Clark, Aravinthan D. T. Samuel, and H. Robert Horvitz.“多巴胺信号对优雅动物的精确运动率是必不可少的。PLOS ONE7, no. 6 (2012).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038649.
Östlund, Magdalena Plecka, Olof Backman, Richard Marsk, Dag Stockeld, Jesper Lagergren, Finn Rasmussen, and Erik Näslund.“与限制性减肥手术相比,胃旁路手术后酒精依赖症的入院率增加”。JAMA Surgery148, no.4 (2013):374–77.https://doi.org/10.1001/jamasurg.2013.700.
Pascoli, Vincent, Marc Turiault, and Christian Lüscher.“可卡因诱发的突触电位的逆转可重置药物诱发的适应性行为”。*自然》*481 (2012)。71–75.https://doi.org/10.1038/nature10709.
Pedersen, B. K., and B. Saltin.“运动作为药物–在26种不同的慢性病中把运动作为治疗处方的证据”。Scandinavian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25, no.S3 (2015): 1-72.
Petry, Nancy M., Warren K. Bickel, and Martha Arnett.“海洛因成瘾者的时间视野缩短和对未来后果不敏感”。Addiction93, no.5 (1998):729–38.https://doi.org/10.1046/j.1360-0443.1998.9357298.x.
Piper, Brian J., Christy L. Ogden, Olapeju M. Simoyan, Daniel Y. Chung, James F. Caggiano, Stephanie D. Nichols, and Kenneth L. McCall.“2006年至2016年美国和地区处方兴奋剂的使用趋势”。PLOS ONE13,no.11(2018)。https://doi.org/10.1371/journal.pone.0206100。
Postman, Neil.Amusing Ourselves to Death:演艺事业时代的公共话语。New York:Penguin Books, 1986.
Pratt, Laura A., Debra J. Brody, and Quiping Gu.“12岁及以上人群抗抑郁药的使用。美国,2005-2008。"*NCHS数据简报第76号,*2011年10月。https://www.cdc.gov/nchs/products/databriefs/db76.htm。
“《古兰经》。24:31节。“2020年7月2日访问。http://corpus.quran.com/translation.jsp?chapter=24&verse=31。
Ramos, Dandara, Tânia Victor, Maria Lucia Seidl-de-Moura, and Martin Daly.“里约热内卢贫民窟青年与大学生的未来折扣”。青春期研究杂志》第23期(2013年)。95–102.https://doi.org/10.1111/j.1532-7795.2012.00796.x.
Rieff, Philip.治疗性的胜利。弗洛伊德之后信仰的使用。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66.
里奇,汉娜,和马克斯-罗瑟。“毒品使用”。我们的数据世界。2019年检索。https://ourworldindata.org/drug-use。
Robinson, Terry E., and Bryan Kolb.“与暴露于滥用药物有关的结构可塑性”。Neuropharmacology47, Suppl.1 (2004):33–46.https://doi.org/10.1016/j.neuropharm.2004.06.025.
Rogers, J. L., S. De Santis, and R. E. See.“延长甲基苯丙胺的自我给药时间会增强大鼠对药物需求的恢复,并损害其对新物体的识别”。精神药理学》第199期。4 (2008):615–24.https://doi.org/10.1007/s00213-008-1187-7.
Ruscio, Ayelet Meron, Lauren S. Hallion, Carmen C。W. Lim, Sergio Aguilar-Gaxiola, Ali Al-Hamzawi, Jordi Alonso, Laura Helena Andrade, et al. “全球DSM-5广泛性焦虑症流行病学的横向比较。"JAMA Psychiatry74, no.5 (2017):465–75.https://doi.org/10.1001/jamapsychiatry.2017.0056.
Saal, Daniel, Yan Dong, Antonello Bonci, and Robert C. Malenka.“滥用药物和压力在多巴胺神经元中触发了一个共同的突触适应”。神经元37, no.4 (2003):577–82.https://doi.org/10.1016/S0896-6273(03)00021-7.
萨特尔,萨利,和斯科特-O-利连菲尔德。“成瘾和大脑疾病的谬误”。*精神病学前沿》*4(2014年3月)。1–11.https://doi.org/10.3389/fpsyt.2013.00141.
Schelling, Thomas.“实践中的自我指挥,政策中的自我指挥,以及理性选择理论中的自我指挥”。*美国经济评论》*74,第2期(1984)。1-11。https://econpapers.repec.org/article/aeaaecrev/v_3a74_3ay_3a1984_3ai_3a2_3ap_3a1-11.htm。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psyt.2013.00141/full。
Schwarz, Alan.“报告发现,数以千计的幼儿被用于治疗A.D.H.D.,引发了人们的担忧。"纽约时报》,2014年5月16日。
Shanmugam, Victoria K., Kara S. Couch, Sean McNish, and Richard L. Amdur。“阿片类药物治疗与慢性伤口愈合率之间的关系”。伤口修复和再生25,第1期(2017)。120–30.https://doi.org/10.1111/wrr.12496.
Sharp, Mark J., and Thomas A. Melnik.“涉及阿片类镇痛剂的中毒死亡-纽约州,2003-2012”。Morbidity and Mortality Weekly Report64, no. 14 (2015):377-80.
Shahbandeh, M. “2014至2025年美国无麸质食品市场价值”。Statista,2019年11月20日。2020年7月2日访问。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884086/us-gluten-free-food-market-value/。
Sherwin, C. M. “自愿轮流跑。审查和新的解释”。动物行为学56,第1期(1998年)。11–27.https://doi.org/10.1006/anbe.1998.0836.
Shoda, Yuichi, Walter Mischel, and Philip K. Peake.“从学前的满足延迟预测青少年的认知和自我调节能力。识别诊断条件”。发展心理学26,第6期(1990)。978–86.https://doi.org/10.1037/0012-1649.26.6.978.
辛克莱尔,J.D. “关于使用纳曲酮和在酒精中毒治疗中使用不同方式的证据”。1 (2001)。2–10.https://doi.org/10.1093/alcalc/36.1.2.
Singh, Amit, and Sujita Kumar Kar.“电休克疗法如何发挥作用?了解神经生物学机制”。临床精神药理学和神经科学15, no.3 (2017):210–21.https://doi.org/10.9758/cpn.2017.15.3.210.
Sobell, L. C., J. A. Cunningham, and M. B. Sobell.“通过和不通过治疗从酒精问题中恢复。两个人口调查中的流行率”。美国公共卫生杂志86,第7期(1996年)。966-72.
Sobell, Mark B., and Linda C. Sobell.“25年后的控制性饮酒。大辩论有多重要?"Addiction90, no. 9 (1995):1149-53.
Solomon, Richard L., and John D. Corbit.“动机的对立过程理论”。*美国经济评论》*68,第6期(1978年)。12-24.
Spoelder, Marcia, Peter Hesseling, Annemarie M. Baars, José G. Lozeman-van’t Klooster, Marthe D. Rotte, Louk J. M. J. Vanderschuren, and Heidi M. B. Lesscher.“酒精摄入量的个体差异预测大鼠的强化、动机和强迫性酒精使用”。酒精中毒。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Research39, no. 12 (2015): 2427-37.https://doi.org/10.1111/acer.12891.
Sprenger, Christian, Ulrike Bingel, and Christian Büchel.“以痛治痛:异位有害条件刺激引起的内源性镇痛的脊柱上部机制”。Pain152, no. 2 (2011):428–39.https://doi.org/10.1016/j.pain.2010.11.018.
Šrámek, P., M.Šimečková, L. Janský, J.Šavlíková, and S. Vybíral.“人类对浸入不同温度的水的生理反应”。欧洲应用生理学杂志81(2000)。436–42.https://doi.org/10.1007/s004210050065.
Strang, John, Thomas Babor, Jonathan Caulkins, Benedikt Fischer, David Foxcroft, and Keith Humphreys.“毒品政策和公共利益。有效干预措施的证据”。Lancet379 (2012):71-83.
物质滥用和精神健康服务管理局,美国卫生和人类服务部。行为健康,美国,2012。HHS Publication No. (SMA) 13-4797, 2013.http://www.samhsa.gov/data/sites/default/files/2012-BHUS.pdf.
Sutou, Shizuyo.“来自原子弹的低剂量辐射延长了寿命,相对于未受辐射的个体而言,癌症死亡率降低了。"Genes and Environment40, no. 26 (2018).https://doi.org/10.1186/s41021-018-0114-3.
Sydenham, Thomas.“痛风和臌胀症的论文”。载于*《托马斯-西德纳姆医学博士的作品,关于急性和慢性疾病*》,254。伦敦,1783年。https://books.google.com/books?id=iSxsAAAA-MAAJ&printsec=frontcover&source=gbs_ge_summary_r&cad=0#v=onepage&q&f=false 2。
Synnott, Mark.“亚历克斯-霍诺德如何在没有绳索的情况下完成终极攀登”。国家地理杂志在线。2020年7月8日访问。https://www.nationalgeographic.com/magazine/2019/02/alex-honnold-made-ultimate-climb-el-capitan-without-rope。
辛诺特,马克。The Impossible Climb:亚历克斯-霍诺德,艾尔-卡皮坦,和攀登生活。New York:Dutton, 2018.
Taussig, Helen B. “来自闪电的’死亡’和重新生活的可能性”。American Scientist57, no.3 (1969):306-16.
Tomek, Seven E., Gabriela M. Stegmann, and M. Foster Olive.“海洛因对大鼠亲社会行为的影响”。Addiction Biology24, no.4 (2019): 676-84.https://doi.org/10.1111/adb.12633.
十二个步骤和十二个传统。纽约。酗酒者匿名世界服务组织,未注明日期。
Vasconcellos, Silvio José Lemos, Matheus Rizzatti, Thamires Pereira Barbosa, Bruna Sangoi Schmitz, Vanessa Cristina Nascimento Coelho, and Andrea Machado.“基于进化心理学的理解谎言。批判性评论”。心理学趋势》27,第1期(2019年)。141–53.https://doi.org/10.9788/TP2019.1-11.
Vengeliene, Valentina, Ainhoa Bilbao, and Rainer Spanagel.“研究复发行为的酒精剥夺效应模型。大鼠和小鼠之间的比较”。Alcohol48, no.3 (2014):313–20.https://doi.org/10.1016/j.alcohol.2014.03.002.
Volkow, N. D., J. S. Fowler, and G. J. Wang.“多巴胺在人类药物强化和成瘾中的作用。影像研究的结果”。行为药理学》13, no.5 (2002):355–66.https://doi.org/10.1097/00008877-200209000-00008.
Volkow, N. D., J. S. Fowler, G-J. Wang, and J. M. Swanson.Wang, and J. M. Swanson.“药物滥用和成瘾中的多巴胺。影像研究的结果和治疗意义”。分子精神病学》9,第6期(2004年6月)。557–69.https://doi.org/10.1038/sj.mp.4001507.
Watson, Gretchen LeFever, Andrea Powell Arcona, and David O. Antonuccio.“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多动症药物滥用危机”。伦理人类心理学和精神病学17,第1期(2015)。https://doi.org/10.1891/1559-4343.17.1.5。
Weisman, Aly, and Kristen Griffin.“吉米-基梅尔在这种激进的饮食方式下减掉了一吨的体重。"商业内幕》,2016年1月9日。
Wells, K. B., R. Sturm, C. D. Sherbourne, and L. S. Meredith.Caring for Depression.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惠特克,罗伯特。流行病的剖析。神奇的子弹、精神病学药物和美国精神疾病的惊人崛起。New York:Crown, 2010.
温尼科特,唐纳德-W. “在真我和假我方面的自我歪曲”。在*《成熟过程和促进环境》*中*。情感发展理论的研究*》,140-57。纽约。国际大学出版社,1960年。
Wu, Tim.“便利的暴政”。纽约时报》,2018年2月6日。
Younger, Jarred, Noorulain Noor, Rebecca McCue, and Sean Mackey.“用于治疗纤维肌痛的小剂量纳曲酮。小规模、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平衡、交叉试验的结果,评估每日疼痛水平”。关节炎和风湿病》第65期(2013年)。529–38.https://doi.org/10.1002/art.37734.
Zhou, Qun Yong, and Richard D. Palmiter.“多巴胺缺失的小鼠严重缺乏活动能力、自闭症和失语症。Cell83, no. 7 (1995):1197-1209。https://doi.org/10.1016/0092-8674(95)90145-0 。
鸣谢
我想感谢我的病人,他们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与我分享了他们的经验和思考。他们愿意不仅向我而且向看不见的、不知名的读者奉献自己,这是一种勇气和慷慨的行为。这就是我们的书。
我还要感谢那些同意接受本书采访的非我病人的人。他们对成瘾和康复的见解对我自己的见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我很幸运,身边有很多有思想、有创造力的人,他们的想法通过我们的对话进入了本书。我不可能把他们都列出来,但我要特别感谢肯特-邓宁顿、基思-汉弗莱斯、E-J-扬内利、罗伯-马伦卡、马修-普雷库佩克、约翰-鲁阿克和丹尼尔-萨尔。
还要感谢罗宾-科尔曼让我重新开始写作,感谢邦妮-索洛对这个项目的信任,感谢黛布-麦卡洛尔为我画画,感谢斯蒂芬-莫罗和汉娜-菲尼使它取得了成果。
最后,如果没有我心爱的丈夫的支持,Andrew,一切都不可能。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索引
本索引中的页码指的是本书的印刷版本。所提供的链接将带你到该印刷页的开头。你可能需要从该位置向前滚动以在你的电子阅读器上找到相应的参考资料。
注:斜体字的页码指的是插图。
节制
后的叮咬,87
在DOPAMINE框架内,76-81
和适度使用毒品的目标,87
复发的时期,57
稳态所需,77
的作用,在康复中,234
所需时间,78-79
违反禁欲的效果,87
接受,217
问责制
促进了真实的自传,186-92
和亲社会的羞耻感,219
针灸,154
阿德雷尔
多巴胺输出的影响,50
越来越高的处方率,39
效力的问题,130
上瘾的风险,129
上瘾
和对奖励的敏感性下降,56
的定义,16
对不能戒除的药物,88
运动的影响,150-51
遗传易感性,87
追求康复的动机,104
和恢复中的新突触途径,64
和光遗传学,64
贫困是风险因素,105
和复发,57
增长率,29
的风险因素,18-22
啮齿动物,对车轮运行的影响,161-65
和容忍(神经适应),53-58
易受影响,65
另见 戒断 ;特定的成瘾物质和行为
美国大学校园里的多动症药物滥用危机,(沃森),130
Aeschylus,189
年龄
和重置奖励途径所需的时间,79
和对消极后果的脆弱性,75
Aguiar, Mark,106-7
Ahmed, S. H.,101
酒精
节制,78-79
上瘾,20
和抑郁症,78-79
归因于疾病负担,29
和双硫仑作为自我结合的手段,97-98
访问对使用的影响,101
和纳曲酮作为自我结合的手段,96
和物理策略的自我约束,94-95
和禁酒令时代,19
和宗教参与,214
和减肥手术,100
戒断症状,79
匿名酗酒者协会
节制的重点,86
和俱乐部商品,219-22
批评,221
和 “醉汉”,185
自由骑手,221-22
诚实的强调,188
作为亲社会羞耻感的模型,215-24
和人、地、物(线索),58
强调的责任,187
支持性的团契,223-24
弥补,作出,218
安非他命
和延迟贴现现象,103
多巴胺输出的影响,50
自娱自乐到死(Postman),40
杏仁核,159
麻醉,38
动物王国的欺骗,172
南极洲,在附近游泳,166
抗抑郁药
对情感体验的影响,131
和情绪症状的发生率,129
使用的普遍性,38-39
耐受性/依赖性问题,130
焦虑
的作者,189-90
客户的经验,31-33 ,40-41 ,42-43 ,71-72 ,84-85
多巴胺禁食期间,84
在高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45
缺乏基本的自我护理被误认为是,41-44
和快乐-痛苦的平衡,65
症状的普遍性,129-30
戒断介导的焦虑,81
作为戒断症状,57
抗焦虑剂,129
细胞凋亡,149
公共卫生学校和项目协会(ASPPH),19
Ativan,42-43
日本的原子弹爆炸(1945年),149
注意力缺失症(ADD)
和安非他明用于治疗,50
客户的经验,32
药品的疗效问题,130
兴奋剂的处方,39
真实的自我,192
坏的宗教(Douthat),35
强迫性过度消费的障碍。见 自我约束
比彻,亨利-诺尔斯,65-66
比利时,44 岁
通过亲社会的耻辱感培养的归属感,217 ,223-24 ,234
狂看节目,44
戒酒后暴饮暴食,87
Bini, Lucino,155-56
指责,191
血压,29
蓝领工作,168-69
大脑
和现代世界的丰富,67
适应于稀缺性,67
杏仁核,159
药物永久改变的能力,62-63
以及对奖励和线索的编码记忆,62
保持平衡*(见* 大脑中的平衡状态 )。
海马体,67
学习对多巴胺发射的影响,63-64
和神经元生长,143-44
和恢复中的新突触途径,64
另见 大脑中的奖励途径
重温勇敢的新世界》(赫胥黎),40
Bretteville-Jensen, Anne Line,103
英国医学杂志,66
佛陀,152
丁丙诺啡(Suboxone),119-20 ,126-27 ,128-29 ,134
Calabrese, Edward J.,148
卡路里限制,149-50
“取消文化”,229
癌症,149
大麻
永久性地改变大脑的能力,63
客户的经验,71-72 ,107-9 ,123-24 ,125 ,231-32
日常使用,73
消耗的数据收集,73
和DOPAMINE框架,74-75
和医用大麻,114
和心态,81
消费者的目标,73-74
的效力,22
和自我约束,231-32
退出,76
卡尔森,阿尔维德,48
案例,安妮,30岁
自我约束的分类策略,110-18
客户的经验,110-11
妖魔化的神化,114-15
节食,112-13
的局限性,113
和克制的象征,116-17
因果关系,评估的能力受到影响,75
C. elegans,151
Cerletti, Ugo,155-56
布拉格查尔斯大学,142
儿童
违背承诺,193-94
和早期儿童创伤,36
与逆境隔绝,35-37
撒谎,171
精神科药物处方,133
巧克力,多巴胺的输出受到影响,50
自我约束的时间策略,101-9
关于,101
客户的经验,107-9
和延迟贴现现象,102-5
和闲暇时间和无聊,105-7
追踪消费的时间,102
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LDS教会),112
香烟和尼古丁
获取,20-21
和延迟贴现现象,103
多巴胺输出的影响,50
访问对使用的影响,101
和雅各布的性瘾经历,13
阶级平等,30
古典(巴甫洛夫)条件反射,58-62
可卡因
和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自我装订策略,101-2
多巴胺输出的影响,50
逆转由其引起的大脑变化,64
敏感化,62-63
色觉,53
强迫性过度消费
创造障碍*(见* 自我约束 )
和工作的劳累,169
的生态成本,30
对人类依恋的影响,184
互联网的促进作用,27
和闲暇时间和无聊,105-7
和自愿性的丧失,91-92
和节制毒品使用,88
贫困是风险因素,29-30
计算机,花在上面的时间,107
毒品消费的后果,74-75
消费/消费主义,沉迷于此,23-24
科尔比,约翰,52
反文化运动,114
大卫-考特莱特,20岁
渴望
在快乐之后,53
和丁丙诺啡,119
和大脑的快乐-痛苦平衡,2
交叉成瘾,79-80
线索
与毒品使用有关,58
依赖线索的学习,58-62
切割,成瘾,167
DOPAMINE框架下的数据收集,72-73
死亡
绝望的人,30
的风险因素,29
迪顿,安格斯,30岁
欺骗。见 谎言和欺骗
恶魔化的神化,114-15
延迟满足
违背诺言的影响,194
和物理策略的自我约束,116
和丰富与匮乏的心态,195-96
妖魔化的物质,神化,114-15
拒绝,177
去个性化,192
抑郁症
和酒精使用,78-79
客户的经验,40
越来越多的发生率,45
和快乐-痛苦的平衡,65
服用药物,132
脱实向虚,192
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SM-V),61
饮食是风险因素,29
节食,112-13
数字药物,23
披露色情,184-86
不舒服,不容忍,40
分散注意力
和多巴胺禁食,83-84
和避免疼痛,44
和个人设备,40-41
双硫仑作为自我结合的手段,97-98
狗,疼痛反应的研究,145-47
多巴胺
的功能,48-49
识别,48
另见 大脑中的奖励途径
多巴胺禁食,71-88
禁忌症,79-80
和同时存在的精神障碍,80-81
的步骤*(见* DOPAMINE框架 )
和退出,84
DOPAMINE框架,72-88
D代表数据,72-73
O代表目标,73-74
P代表问题,74-75
A代表节制,76-81
M代表正念,81-84
I代表洞察力,84-85
N为下一步行动,85-86
E代表实验,87-88
双重生活,12
Douthat, Ross,35
毒品和药物使用
与之相关的线索,58
和对奖励的敏感性下降,56
归因于疾病负担,29
和表观遗传学的变化,20
运动的影响,150-51
剂量过大,30
和快乐-痛苦的平衡,54
的效力,21-22
和宗教参与,214
“醉生梦死”,185
肯特郡邓宁顿,2
Duragesic芬太尼,18
Dutto, Vince,26-27
DXM,22
抑郁症,57
恐惧症导致的复发,57
东亚人,97
东欧,29
摇头丸,115
教育水平,29-30
电休克疗法(ECT),155-56
电子设备,个人,40-41
情感
精神药物的影响,131
忍受痛苦,83-84
同理心,217
内源性大麻素,150
内源性阿片肽(内啡肽),150
耐力型运动员,167
英国,129
娱乐,需求,40
表观遗传学变化,20
肾上腺素,150
爱泼斯坦,马克,192
平等,30
经验依赖的可塑性,62-63
经验,叙述的价值,177
DOPAMINE框架下的实验,87-88
接触疗法,156-59
极限运动,165-67
“假自我”,191-92
禁食,149-50
恐惧,对其容忍度增加,159-60
女性的谦逊,112
纤维肌痛,154-55
菲纽肯, 汤姆,67
食物
已处理,22
和减重手术,99-100
法国,44 岁
弗里德曼,丹尼尔,75
弗洛伊德,西格蒙德,36
对未来的信心,195-96
赌博
成瘾的分类策略,111
和损失的追逐,62
和纳曲酮作为自我结合的手段,96
在线,23
病理性的,61-62
胃肠结合,99
胃绕道,99
基因表达和表观遗传变化,20
德国,39
胶质细胞的产生,150
无麸质产品,113
目标
和多巴胺框架的下一步,85-86
“神在 “神学,35
Goethe, Johann Wolfgang von,53
继续存在(爱泼斯坦),192
有毒瘾的祖父母,20
古希腊人,141
致幻剂,114-15
幸福,34-35
哈奇,亚历山大,134
医疗保健,负担得起,30
Hebb, Donald,179
Hering, Ewald,53
英雄式疗法,153
海洛因
和延迟贴现现象,103
和奥施康定的发展,114
访问对使用的影响,101
和纳曲酮作为自我结合的手段,96-97
的起源,21
冬眠,143-44
海马体,67
希波克拉底,153
Hoff, Wim,142
大脑中的平衡状态
禁欲是必要的,77
和电休克疗法(ECT),156
作为多巴胺禁食的目标,88
无力实现,128
和疼痛引发快乐的能力,144-47
和快乐-痛苦的平衡,51-53
重新建立,在没有药物的情况下,58
诚实,171-205
推动的问责制,186-92
传染性,192-97
作为日常斗争,205
诚实的神经生物学机制,177-79
作为痛苦的,171
作为预防措施,197-204
的作用,在恢复中,172-75
和羞耻感的循环,217
荷尔蒙效应,科学,148-52
酒店房间,17-18
洪,林,184
Huxley, Aldous,40
氢可酮,21
海洛蒙,21
催眠剂,129
皮下注射器,21
Iannaccone, Laurence,219-21
埃里克-J-伊内利,107
冰岛,39 岁
漠不关心,184
在多巴胺禁食中获得的见解,84-85
间歇性禁食,149-50
互联网
和技术的成瘾潜力,23
和聊天室,26
和数字药物,23
和性虐待,26-27
“病毒性”(传染性)视频,27
诚实所促进的亲密的人际关系,182-86 ,227 ,234
作为戒断症状的易怒性,57
意大利,44 岁
日本
和原子弹爆炸(1945),149
幸福的分数,44
疼痛的发生率,45
朱雷克,斯科特,165-66
康德,伊曼纽尔,118
金梅尔,吉米,150
韩国,39
Kramer, Peter,131
kSafe,95
学习,多巴胺的发射增加,63-64
“休闲、奢侈品和青年男子的劳动供应”(阿吉亚尔),106-7
闲暇时间,越来越多的人,105-7
Levin, Ed,133
边缘资本主义,20
林内特,雅各布,61
倾听百忧解(克莱默),131
刘翔,154
肝脏疾病,30
追逐损失,62
路德,马丁,145
撒谎和欺骗
在动物界,172
成人的平均谎言,172
违背诺言,194-95
儿童的,171
客户的经验,172-75
的习惯,175
的神经生物学机制,178
和稀缺性心态,195-96
和教育儿童诚实,225-26
操纵性的自我表露,184-86
麦克卢尔, 塞缪尔,104
意义,感觉,196-97
医疗补助领取者,134
医疗实践,现代,38-39
药品
对情感体验的影响,131
和缺乏基本的自我照顾被误认为是精神疾病,41-44
作为社会控制的手段,133-34
和围绕疼痛的范式转变,38
开给儿童的,133
精神科药物,38-39
效力问题,129-30
上瘾的风险,129
另请参见具体药物
梅耶尔,约翰娜,164
Melencolia 1(Dürer),9
对快乐/痛苦的记忆,66-67
精神疾病
缺乏基本的自我护理被误认为是,41-44
症状的普遍性,129-30
作为成瘾的风险因素,20
道德形而上学,(康德),118
甲基苯丙胺
多巴胺输出的影响,50
访问对使用的影响,101
对学习能力的影响,64
佛祖倡导的中庸之道,152
DOPAMINE框架中的正念,81-84
Mischel, Walter,115
谦虚的衣服,112
单胺类神经递质,143
蒙塔古,凯思琳,48
情绪紊乱的症状,129-30
吗啡,21
死亡率风险,29
MXE,22
纳洛酮,153-55
纳曲酮作为自我结合的手段,96-97
国家卫生统计中心(CDC),133
全国健康访谈调查,133
自然资源,30
Netflix,狂看,44
神经适应(容忍),53-58
神经元
神经元生长,143-44
中国的新医院,96-97
新西兰,44 岁
尼古丁。见 香烟和尼古丁
Nietzsche, Friedrich,157
北美洲,45
NXIVM,223
DOPAMINE框架中的目标,73-74
Ohe, Christina G. von der,143
Opana,22
阿片类药物
永久性地改变大脑的能力,63
与之相关的成瘾风险,21
和丁丙诺啡,119
关于多巴胺禁食的警告,79
客户的经验,124-25
疫情,18-19
和纳曲酮作为自我结合的手段,96
剂量过大,39
快乐-痛苦平衡重置引起的,55
的效力,21
对穷人的规定,134
处方的普遍性,39
和手术后的恢复,38
和时间范围的缩减,103-4
和容忍(神经适应),55
并愿意帮助他人,184
另见 特定毒品,包括海洛因
对手过程理论,52-53
光遗传学,64
过度训练综合症,167
羟考酮,21
催产素,183-84
疼痛
容忍的能力,66
敏感性下降,145
和狗对电击的反应,145-47
丰富性对经验的影响,67
拥抱*(见* “痛苦的一面,按下”)。
情感,83-84
越来越多的物理发生率,45
和享乐主义设定点,145
对轻度的不容忍,40
纳曲酮的治疗,154-55
神经处理的,2
围绕范式转变,38-39
的认识,65-66
感受到的快乐,65
和对疼痛药物的耐受性,55
广泛流行,44-46
另见 快乐-痛苦的平衡
“痛苦的一面,按下了”
和对疼痛的成瘾,160-68
和多巴胺缺失状态,167
和运动,150-52
和暴露疗法,156-59
和极限运动,165-67
和稳态机制,143-44
和荷尔蒙效应,148-52
和增加对恐惧的容忍度,159-60
和间歇性禁食,149-50
作为对疼痛的治疗,153-60
和工作上瘾,168-69
亲子教育
让儿童远离逆境,35-37
和有毒瘾的父母,20
和亲社会的羞耻感,224-29
帕斯科利, 文森特,64
巴甫洛夫,伊万,58
巴甫洛夫(古典)条件反射,58-62
Paxil,32
五氯苯酚,22岁
以人、地、物为线索,58
哌克赛特,22
制药工业,128
自我约束的物理策略,93-101
客户的经验,93-94
双硫仑作为手段,97-98
kSafe设备,95
作为手段的纳曲酮,96-97
和斯坦福大学棉花糖实验,115-16
减肥手术,99-100
乐趣
预期性的,59
后的渴望,53
和依赖线索的学习,58-62
丰富性对经验的影响,67
长时间/重复接触的影响,66
无力享受,57
神经处理的,2
疼痛体验,65
疼痛的触发能力,144-48
和大脑中的奖励途径,51
和容忍(神经适应),53-58
另见 快乐-痛苦的平衡
快乐-痛苦的平衡,47-68
和丁丙诺啡,119
和依赖线索的学习,58-62
使用毒品的影响,54-58
和无法实现平衡的情况下,128
的个人起点,65
和赋予经验的意义,65-66
恢复的药物,127-35
阿片类药物的重置,55
说出真相的作用,179
的自我调节系统,50-53
和容忍(神经适应),53-58
参见 “痛苦的一面,压迫” 。
葡萄牙,39
邮递员,尼尔,40 岁
锅。参见 大麻
薯片,22
成瘾物质/体验的效力,21-22
贫困
和丰富与匮乏的心态,196-97
和精神药物处方率,133-34
祈祷,91
预防,以诚实为手段,197-204
普里斯尼茨,文森茨,141-42
DOPAMINE框架中的问题,74-75
禁酒令时代,19
承诺,打破/保持,194-95
西洛赛宾,114-15
迷幻药,114-15
精神疾病
和多巴胺禁食,80-81
和对成瘾的脆弱性,65
普格,刘易斯,166
古兰经》,112
种族平等,30
叙述我们的经验,其价值,177
恢复
禁欲的作用,234
和传染性的愈合,193
和创造新的突触途径,64
和哈利波特的意象,234
追求的动机,104
和亲社会的羞耻感,208
复发
禁欲期后,58
可靠性,195
宗教和宗教组织
和俱乐部商品,219-20
和女性的谦逊,112
现代新时代神学,35
羞耻感的体验,213-14
严格性,221
资源贫乏/丰富的环境,105
责任,个人,186-91
克制,象征性的,116-17
大脑中的奖励途径,49
和拒绝,177
和学习对多巴胺发射的影响,63-64
和测量药物/行为的成瘾潜力,49
催产素的作用,184
和快乐-痛苦的平衡,51
和前额叶皮层萎缩,105
重置所需时间,79
奖励
预测/反应的区别,62
奖励*(续*)
编码的记忆,62
和赌博障碍,62
即时与延迟,104-5
获得的动机,48-49
未能实现的,60-61
Rieff, Philip,34-35
成瘾的风险因素,18-22
劫匪,尤里,164
Rosenwasser, Alan,161-62
Ruff, Christian,177-79
谣言,231
跑步,成瘾,167
俄罗斯,29
稀缺性
的心态,194-97
精神分裂症,130
Schuckit, Marc,78
自我约束,89-118
归类的战略,110-18
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策略,101-9
客户的经验,89-91
并为选择药物制造障碍,91-92
和斯坦福大学的棉花糖实验,115-16
作为实现自由的手段,118
自我照顾,缺乏,41-44
自我伤害,成瘾,167
自查,219
敏感化,62-63
宁静(电影),135
Sertürner, Friedrich,21
性爱
多巴胺输出的影响,50
作为体育活动,152
性爱成瘾
和聊天室,26
和关系中的诚实,182-83
雅各的经历,10-13 ,16-18 ,24-26 ,27-29 ,89-91 ,110-11 ,117-18 ,182-83
性虐待,26-27
耻辱,207-29
和匿名酗酒者,215-24
和相互坦诚,227
亲社会的养育方式,224-29
和恢复,208
和宗教组织,213-14
羞愧-内疚的二分法,207-8
谢文,C. M.,163-64
缺点,理解,219
硅谷,168
跳伞,165
袖状胃切除术,99
智能手机
上瘾,88
作为成瘾性内容的传递装置,1
与之相关的物理/重复性运动,151-52
吸烟。见 香烟和尼古丁
社交媒体
和 “取消文化”,229
“假自我 “的转述,191-92
强化不确定性的方面,62
和匮乏的心态,196
所经历的耻辱,229
苏格拉底,147
所罗门,理查德,52
南非,45
西班牙,39
体育博彩,111
斯普格尔, 克里斯蒂安,153
兴奋剂
上瘾,129
对学习能力的影响,64
越来越高的处方率,39
自杀者,30 人
苏利文,艾迪,64 岁
手术,止痛药对恢复的影响,38
在南极洲附近游泳,166
瑞士,45 岁
托马斯-塞登纳姆,38 岁
注射器,皮下注射器,21
Taussig, Helen,147-48
时间跨度,缩减,103-4
牺牲和耻辱的理论(Iannaconne),220-21
时间限制。见 自我约束的时间顺序策略
烟草使用。见 香烟和尼古丁
耐受性(神经适应),53-58
经颅直接电流刺激(TDCS),178
治疗性的胜利,(里夫),34-35
推特,27
超级马拉松运动,165-66
不确定性,61-62
美国
由于成瘾而造成的疾病负担,29
情绪/焦虑症状的发生率,129
疼痛的发生率,45
罗切斯特大学,194
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134
安定剂,39
维柯丁,18岁
受害者的叙述,186-91
视频游戏
描写体育活动,151
花在休闲时间上的,107
在线,23
戒断症状,79
互联网上的 “病毒”(传染性)视频,27
自愿选择,91-92
脆弱性,表达,217
想,的时刻,2
沃森,格雷琴-勒弗,130
减肥手术,99-100
啮齿类动物的轮式运行,161-65
温尼科特, 唐纳德,191
撤回
对危及生命的警告,79
和焦虑症驱动的复发,57
从阅读习惯,181
的普遍症状,57
戒断介导的焦虑,81
伍德,亚历山大,21 岁
工作
上瘾,168-69
参加工作的人数减少,106
世界幸福报告》,44
第二次世界大战
日本的原子弹爆炸,149
受伤的士兵,65-66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X Y Z
关于作者
安娜-莱姆克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和成瘾医学教授,也是斯坦福成瘾医学双重诊断诊所的主任。她因在精神疾病方面的杰出研究、卓越的教学和临床治疗的创新而获得了许多奖项。作为一名临床学者,她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和《美国医学会杂志》等著名刊物上发表了一百多篇经同行评审的论文、书籍章节和评论文章。她是一本关于处方药流行的书的作者,《毒贩子,医学博士:医生如何被骗,病人如何上钩,以及为什么如此难以阻止》。她是几个州和国家成瘾组织的董事会成员,曾在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各个委员会作证,保持着活跃的演讲日程,并保持着繁荣的临床实践。

你的下一步是什么? 你的阅读清单?
获得个性化的图书精选和有关该作者的最新新闻。